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故事不是美國總統選舉或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的自負,而是我們對自然界的破壞,這使我們自己的未來面臨危險。可悲的是,這個故事令人沮喪且難以承受,因此通常不會成爲暢銷書的內容。
正如蘇尼爾•阿姆里斯(Sunil Amrith)在《燃燒的地球》(The Burning Earth)中提醒我們的那樣,這也不是一個新的故事。他的敘述始於1217年的英格蘭。在《大憲章》頒布兩年後,貴族們獲得了一份名爲「森林憲章」的檔案,這將有助於他們對土地、木材和野生動物的開發利用。對於富人來說,影響法律的自由與掠奪自然的自由是相輔相成的。從那時起,情況就一直如此。
耶魯(Yale)大學歷史學教授阿姆里斯回顧了許多人類貪婪的事件,包括西班牙、俄羅斯、中國、英國等國家的帝國主義;南非金礦的發展,其中非洲礦工的苦難幫助倫敦成爲金融中心;以及對現代環保人士的謀殺。我們面臨著全球危機,是因爲「我們無法想像與其他人類,更不用說其他物種的親屬關係」。我們未能理解自由具有「生態前提條件」。
《燃燒的地球》被宣傳爲一部「改變範式的全球調查,探討人類歷史如何重塑地球,反之亦然」。事實上,它涵蓋了牛津歷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在去年年初出版的《地球的轉變》中所涉及的一些內容。這兩本書都認爲,只有透過瞭解我們過去如何對待地球,我們才能理解我們的未來。
阿姆里斯確實更加重視亞洲歷史。他提到了自己在新加坡的童年,新加坡長期擔任總理的李光耀(Lee Kuan Yew)稱空調是「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發明」。
該書的一個論點是,特別是在化石燃料出現之後,人類錯誤地認爲他們可以擺脫自然的限制。這種表述在直覺上很有吸引力,但阿姆里斯提供的證據很少,證明人們確實是這樣想的。他只是簡單地陳述,到了1900年,殖民地行政官員相信「他們已經掌握了生命本身」,儘管在19世紀90年代有數百萬人死於與厄爾尼諾(El Niño)氣候現象相關的饑荒。《燃燒的地球》還引用了一份1952年的聯合國報告,其中提到「人類可以成爲環境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是在減少傳染病的背景下)。但這本書主要是一個接一個的破壞事件,只有很少關於思想的碎片。
他描述的許多活動並不是人類「逃離」自然,而是將其視爲一系列可利用的資源。這可能部分反映了人們對自己偉大性的不太相信,而更相信自己的無能。阿姆里斯引用了17世紀初維吉尼亞詹姆斯敦殖民地的領導人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話,他說到野生動物:「它們的領地如此廣闊,它們如此野性,而我們如此軟弱和無知,我們不能太過打擾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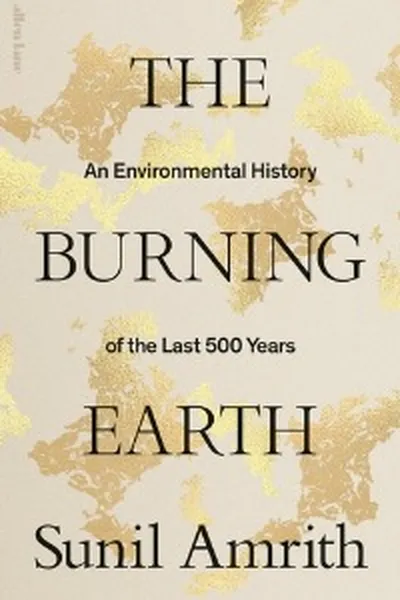
《燃燒的地球》揭示了一些鮮爲人知的事件,包括印度在1976-1977年對800萬人進行絕育手術,這種人口控制方式可能比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更加殘酷。書中提到了巴黎銀行家阿爾伯特•卡恩(Albert Kahn),他透過投資鑽石和金礦積累了一筆財富,並在1940年去世前委託拍攝了地球表面的照片檔案,以記錄「在時間還來得及的時候」。即使是像卡恩這樣富有、有權勢的人也無法拯救自然界,他只能記錄下來。與此同時,那些關注最近美國政治爭議中的「無子女貓奴」的人會對先驅環保主義者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遭到批評的情況感到好笑:「一個沒有孩子的老處女爲什麼如此關心遺傳學呢?」
弗蘭科潘的《地球的變革》有700多頁,而《燃燒的地球》大約有400頁。通常我會選擇較短的書,但在這裏,似乎被刪減的是分析和細微差別。《燃燒的地球》有可能將所有社會描繪成幾乎同樣蔑視窮人、自然世界和非人類動物的社會。中國的大躍進(Great Leap Forward)——甚至連普通的麻雀也被指責喫掉了太多糧食——被呈現爲人類貪婪的極端例子。
後一部分涉及蓬勃發展的環境意識,阿姆里斯將其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之後。他優雅地指出,環境政治的「悲劇」特徵在於「我們從意識覺醒到絕望地認爲可能爲時已晚的速度之快」。他在大學校園和年輕人的氣候罷工中看到了希望,這證明人們終於站出來對抗「過去兩個世紀的自我毀滅性愚蠢」。
反對破壞的聲音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令人遺憾的是,阿姆里斯沒有試圖解釋爲什麼這些聲音通常被淹沒。也許答案顯而易見:環境的捍衛者無法像破壞者那樣調動資源。如果是這樣,我們是否註定只能尋找新的開發領域,無論是深海海底還是外層空間,以滿足我們的貪婪?或者,我們是否最終會將無與倫比的智慧用於發展一種不同的人類繁榮模式?
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和伊隆•馬斯克等人的影響力。他們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故事,但他們是其中的插曲。
《燃燒的地球:過去500年的環境史》蘇尼爾•阿姆里斯著,Allen Lane出版社,30英鎊,4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