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FT共進午餐(二)


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等了幾分鐘,這裏應該是洪晃推薦的粵菜館所在之處,我們約好在這裏喫午餐。這時候,我的手機響了。「那兒就沒這家餐廳,是吧?」她笑道,聲音裏有一絲鬱悶,這家餐廳是她旗下雜誌——中國版Time Out《樂》——的城市生活指南編輯向她推薦的。我一直沒有搞明白,這家餐廳究竟是拆遷了,還是從來就不存在。畢竟,在當今的中國,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在轉瞬間發生。由於時間緊迫,我們選擇了一個簡單的辦法,約好在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St Regis Hotel)見面,就在馬路對面的使館區。
「中國的奧普拉」?過譽還是低估?
洪晃有時被稱作中國的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這種描述對她既是一種過譽,也是一種低估。她在自己辦的城市喫喝玩樂指南雜誌上,有一個讀者來信專欄;還有一個網路部落格,提供有些大膽挑逗的建議——至少按中國標準衡量是這樣;品種不斷增加的雜誌;以及一檔電視節目——所有這些都精明地利用了她的張揚個性。
但她既不具備美國脫口秀節目主持人的影響力,也沒有那麼高的收入。洪晃之所以脫穎而出,是出於其它原因:她的直言不諱——在中國,公共場合的嚴格自律適用於多數話題——和政治出身。
洪晃的母親曾擔任毛澤東和來訪美國政要的翻譯,有一小段時間,還當過毛澤東的英語教師。她的繼父曾擔任中國外交部長。上世紀70年代中期,當普通中國人還不可能出國旅行的時候,洪晃已經前往美國就讀高中,後來畢業於紐約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獲得政治學學位。在中國,這種政治關係可以帶來特權,同時,正如她後來發現的,也會帶來那麼一點危險。
中國真是個兒童的天堂!
近幾個月,45歲的洪晃還領養了一個嬰兒,這讓我們倆人在步入北京國際俱樂部時不禁在想:中國真是個兒童的天堂!在北京,如果你帶著孩子去餐館或酒店,迎接你的不會是西方國家侍者那種冰冷的「鐵板」面孔。「中國的好處是相當隨便,」她表示。「沒那麼多必須遵守的禮儀,儘管他們正在表面上創造這些東西。」
我提醒她,爲中國滿懷抱負的雅皮士一族提供禮儀方面的指導,如今是她自己辦的那些雜誌的主題之一。是的,她笑道。「否則你怎麼去賣所有那些奢侈品呢?你在中國只需要筷子。有了這兩根棍子,就可以喫飯。可你如何去賣那些餐具和黃油刀呢?
落座之後,我請她解釋一下中國奢侈品消費呈爆炸式成長這種矛盾的現象——在這個國家,炫耀財富可能招致懷疑和嫉妒,更不用說,在不時出現的反腐敗運動中,還會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關注。
「中國人希望向一些人展示(自己的財富),而向另外一些人隱瞞財富。他們希望向稅務機構隱瞞財富,但絕對希望展示給其它所有的人,」她表示。
「中國人非常看重面子」
「這是中國人的一個方面,非常看重面子。在任何事情上我們都希望有面子。我們希望人們真正認可我們的成就。但從本質上說,中國人都想玩點陰謀。他們不願亮出底牌,而總是希望隱瞞一些東西。」
洪晃自己幾乎毫無保留,這種個性爲她贏得了人們所熟知的媒體標籤:「越界」。「中國人覺得我越界,但我並不認爲自己越界。我認爲在西方沒人會覺得我越界,」她表示。「我受的是這種美國教育,因此有些事我會想當然,比如說,爲什麼就因爲我是女人,就不能談論性的問題。我從沒想到在中國這會引發衆怒。」但你現在肯定認識到了吧?「沒錯,」她微笑著說。「我在學著呢。」
我們兩個都不覺得菜單很「越界」。她點了海南雞飯,我要的是川味麻辣雞胸——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屬於常見的中式食物,更別說在中國國內了。
中國教條:處處爲他人考慮,唯獨自己除外
洪晃的坦率往往會讓她的聽衆(多數是女性)分爲兩派。有些人鄙視她,但她說,多數人還是覺得她讓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因爲他們長期以來所受的教育一直是「處處要爲他人考慮,唯獨排除自己」。這不會適用於像她這樣有著堅強母親的人吧?洪晃覺得,事實上正是由於她長期不在母親身邊,才讓她變得那麼獨立,而且缺乏某些中國人傳統的緘默。這正是讓她母親擔心的地方,她仍住在北京。
「她知道我口無遮攔,」洪晃表示。「我記得,在我的書(《我的非正常生活》(My Abnormal Life as a Publisher))出版後,我第一次接受電視採訪,他們拍攝的一段內容涉及我的男朋友,或者說是伴侶,或隨便你怎麼稱呼。主持人問道:『你們結婚了嗎?』我們說:『沒有。』我媽媽簡直嚇壞了。她的意思是,你不懂,你不能到媒體上去說,你和一個男人住在一起。但說實話,我從未想到有什麼問題。」
她母親總會看到事情的「負面」,這是在毛時代一次又一次可怕政治運動中養成的本能。毛去世後,上世紀70年代末她一度遭到軟禁,但挺了過來。洪晃從未見過毛澤東。她表示,當毛澤東放棄學英語時,她很高興。「對我媽媽來說,那是一個相當艱鉅的任務——嘗試教一位80歲的獨裁者說英語。」
中國政治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這個角度而言,她認爲中國政治發生了很大變化,儘管依然是一黨制。「我們從毛澤東這種帝王式人物的時代,走到了今天,人們已習慣於每五年有一次政府換屆。這不是一場政變;不是一位領袖從天而降,宣佈改朝換代。那曾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每次改朝換代,人們都會看到流血事件或是陰謀。」
我驚奇地發現,即使是洪晃,對於西方人對中國的描述也持尖銳的批評態度。她抱怨稱,直到現在,在海外的時候,還有人問她是如何從中國脫身的。「哦,」她回答時故意裝傻,「你申請一本護照,排好長好長時間的隊申請美國簽證,然後買張機票。」
洪晃表示,她的雜誌以生活方式爲核心內容,因此不太受中國審查制度的影響。她表示:「你的確必須和(審查人員)有所協商,就像我們當初創辦一個同性戀欄目時那樣。我們不得不改變對同性戀的成見。」她明確表示,我們不應對「外在改變」抱有過高期望。在她看來,中國沒有這種DNA,或者更準確地說,中華文明沒有這種DNA。「很多(限制)源自於文化因素。中國人沒有冒險精神。要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非常困難。」
如今,洪晃不是從政治層面識別這些趨勢,而是從自己爲旗下媒體所做的市場研究。她發現,在很多方面,人們並不保守。她說,當你對人羣分類後就會發現,年齡越大的人,就越認爲政府應對他們負責任;越年輕的人,則越不關心這些。「很多富人不在乎政府。他們擔心的是窮人綁架他們的孩子。四、五年前,他們的擔心來自於政策方面,如稅收。我可以把自己的錢帶出國嗎?現在這是犯罪。這是一個財富範疇的問題。」
法制挺管用
喫到一半的時候,從鄰桌走過來一位法國媒體高階主管,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他是來確認下週的約會。原來,他的公司剛剛挖走了洪晃手下的一位編輯,卻沒有意識到合同裏有一條非競爭條款。他離開後,洪晃承認,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式的法制正好在中國派上用場。「很簡單。只須花錢買斷她的合同。」
不過,讓她擔心的並非編輯人員的流失,而是消費者特徵變化的速度。「人們改變得如此迅速,當你剛剛完成一項研究——可能需要8個月,然後對結果進行整理分析,然後出版的時候,人們已經轉而關注下一件事了。」
名人市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過去,名人受到禮遇,直到讀者發現了「小報」的神奇效果。
「現在你可以告訴人們,他們是如何離婚、如何鬧緋聞的,還有關於訴訟和私生子的報導,」她表示。「6年前,這些你都不能報導,因爲它們被認爲是負面的東西——當時國家還覺得自己是名人們的主人。」
「現在的情況則好像是國家說了:『我們必須來一些可以取悅大衆、緩和大衆情緒的彈藥——一種令人感覺良好的因素。那就拿他們開刀吧!』」
媒體新概念
洪晃表示,向讀者提供服務——我估計其中包括讓名人們名聲掃地——在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中國媒體自出現以來,從不對讀者負責。他們先是對政府負責,後來偉大的商業化時代來了,人們爭相投身其中,對廣告商負責。」
「媒體工作者終於將迎來激動人心的時代。繼景觀、建築和住宅等發生實質變化之後,我認爲將出現文化方面的變化。現在我們正進入一個有意思的階段——改變人們的思想。」
這看上去像是一個奇特的奧威爾式(Orwellian)結尾,但在此之後,我們倆都不知道該如何讓談話繼續下去。於是我們買單離去。
譯者/牛薇
1份海南雞飯
1份川味麻辣雞胸
1瓶Perrier礦泉水
1杯可口可樂
2杯咖啡
總計:352.5元人民幣

米蘭,秋冬時裝展開場,時尚界人士濟濟一堂。即使上午10點看到lamé,或者正午時分看到施華洛世奇(Swarovski)水晶,也沒有人會感到驚奇。在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就更是如此。在這座有著貂皮紋理外觀、奉行賓至如歸的酒店,名流雲集,諸如美國版《Vogue》主編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法國版《Vogue》主編卡琳•洛菲德(Carine Roitfeld)和《名利場》(Vanity Fair)主編邁克爾•羅伯茲(Michael Roberts)等時尚界名人均住在這家酒店。可即使在這兒,在這座酒店富麗堂皇的中心區,「高跟鞋之帝」、已是滿頭銀髮的花花公子馬諾洛•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的登場也足以吸引目光。
「弗瑞德曼女士!」我正在服務檯,準備打電話到伯拉尼克的房間,跟他說我到了,這時66歲的伯拉尼克突然出現在我身邊,他喘著氣,用一隻手扇著風。「哦,非常抱歉我來晚了,可我在樓梯上遇到了漢密斯•鮑爾斯(Hamish Bowles,系歐洲版《Vogue》編輯主任),然後我們」——他的手微微壓了壓——「真難脫身,不過,來,來,我們坐下來。那張桌子好嗎?我們去那兒,請!」他用手勢引著我過去,然後拉出一張椅子。
潮流觀察者和「獵酷者」說,我們即將進入新的時尚時代:經過IT品牌和IT包之後,2009年將是IT鞋品的時代。如果真是如此,如果在經濟危機時期人們不再把錢花在衣服上,而花在可以改變服裝風格的配件上,如果鞋是各類配件中最容易達到這種效果的,那麼,有個人似乎應該比別人知道得更多,此人就是馬諾洛。(在公開談話中,他總是被稱作馬諾洛,他的鞋是「馬諾洛」,儘管他總是本著嚴格的個人禮儀規範,對任何人都採用正式稱呼。)
在克里斯蒂安•婁伯丁(Christian Louboutin)之前,在周仰傑(Jimmy Choo)、魯伯特•桑德森(Rupert Sanderson)和尼古拉斯•柯克伍德(Nicholas Kirkwood)之前,就有了馬諾洛。他是細跟鞋的發明者,他設計的鞋就如裝飾品,優雅、性感——那樣愛撫著足部曲線——無需標識,人們就能夠認出它們;它們創造了自己的風格。美劇《慾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極力渲染女人對鞋子的著迷,而馬諾洛是她們原始慾望中「必須擁有之物」。坐在他身邊用餐,我覺得自己成了衆人的注目焦點。
問題是,我們之間的談話總是飄忽不定。「鞋有這麼重要嗎?」他問道。「真的?如果我是女人,我會一個月都穿著同樣的東西,只換帽子和手套。大概也會換換鞋子;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真的,一個人裝束有沒有改變,要看珠寶。我真的喜歡手套。我也鍾——愛帽子。如今的鞋子太——多了。我總是告訴孩子們,」——伯拉尼克是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的榮譽教授,「孩子們」是指他的學生——「『不要做鞋子!要做帽子!'那些鞋子如此奇怪,如此庸俗。我討厭如今到處氾濫的厚底鞋;它們就想抓住人們的注意力。土死了!我從來沒做過厚底鞋。噢,做過,在上世紀70年代,不過那是段糟糕的經歷。」
馬諾洛似乎不怎麼想談論鞋子、女人與鞋子的關係,或者男人與女人的鞋子的關係。他對此不感興趣。整個午餐變成了問答遊戲,每當我提出一個問題,他的答覆總是忽高忽低地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飄走。這或許令人惱火,只是他的言談如此富有魅力。馬諾洛不但可以說是鞋界的巨人,也是迴避話題的天才。或者他只是厭倦了這類問題(唉,又是鞋子!),只是礙於禮貌而不願承認。
畢竟,他從1971年離開迦納利羣島的家後就開始從事這一行。他在迦納利羣島長大,他父親是捷克人,母親是西班牙人,雙親經營著一座香蕉園。他在日內瓦大學(University of Geneva)唸完書後前往英國,認識了攝影師埃裏克•波曼(Boman),後者把他帶到紐約,並介紹給當時美國版《Vogue》主編黛安娜•弗裏蘭(Diana Vreeland)。弗裏蘭告訴他,「去做鞋吧」。伯拉尼克想當舞臺佈景師,但他從未想過要對傳奇式(並且獨裁)的時尚界女王說不。或許是爲了彌補放棄早年戲劇夢的遺憾,從此他就把自己扮演成一個角色:整個世界是他的舞臺,而說話是一種表演藝術;每句話都自有其高峯和低谷。
因此,某些特別的詞語就被髮成顫音,並且拉長了念,於是,「鍾愛」(adore)變成「鍾——愛」(adddddore),「討厭」(detest)變成「討——厭」(detessssst)。伯拉尼克講話時,常常向前傾著身子,一副密謀的架式;也有時會連續三次揚起眉毛,以示強調——他自己知道這種姿勢很搞笑——然後臉上浮現微微的笑容。他還喜歡保持一致性,或者說喜歡呆在熟悉的地方。比如說,30年來他一來米蘭就必定住在四季酒店,而且住在同一個房間。去紐約則住聖瑞吉酒店(St Regis)。
「我喜歡去老地方,認得那裏的人。傳統!我喜歡傳統的地方,」伯拉尼克表示。他與四季酒店餐廳裏的侍者握手。所有侍者不僅認識他,還熟知他的飲食注意事項:他對醋酸過敏,不能飲用開胃酒,也不能沾醋。他喜歡白豆湯(「妙極了」),雖然菜單上沒有,他也想點這道湯。在與女侍者簡短交談後,他點了蔬菜湯,然後我們重新回到鞋子的話題。
「我討厭那種空想時期,你產生一個想法,可3秒鐘之後就把它拋到腦後,」他瞪大了眼睛,說道。「最近幾年簡直是噩夢!有夢想是一回事,可這太過了!去年我在洛杉磯,因爲他們要頒給我一個獎項,這樣他們就可以朝你吐唾沫,把你踩在腳下。叫什麼來著?大道風尚明星?」他說的是「羅迪歐大道風尚獎」(Rodeo Drive Walk of Style),授予時尚界傑出人物,獎牌會嵌在比佛利山(Beverly Hills)的一條人行道上。「沒錯,大道風尚獎。他們問我,想讓誰給我頒獎?科洛•塞維尼(Chloë Sevigny)怎樣?我說,『不,我不讓她頒。'那麼劉玉玲呢?哦,她棒極了!我喜——歡東方女孩。你喜不喜歡東方女孩?而且她當時穿著(紀梵希(Givenchy)設計師)卡爾多•蒂希(Riccardo Tisci)的作品,這是我喜愛的設計師——我們剛纔在談什麼?」
伯拉尼克講起話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常常會自己停下話題,自我反省地說道:「說多了,說多了!」他只有在提到令人不快的事情時,纔會停止這種自由聯想,比如提到伊夫•聖洛朗(Yves Saint Laurent)的葬禮時(「我再也不去參加葬禮了,太悲痛了。我就是完全無法接受死亡。的確,人固有一死,可我就是接受不了。」) 有朋友(如卡爾•拉格菲爾德(Karl Lagerfeld))過來時,他也會停下話頭,這時他會從椅子上探出身子,愉快地與人握手,並把我介紹給來人。
整個午餐期間,伯拉尼克只喝了三、四勺湯,碰都沒碰面包。在他舀第二勺湯之前,我就已經喫完了整盤沙拉。「我喫很多巧克力,」在我表示擔憂時,他悄悄地說道,「我喜——歡巧克力。」唯一把他難住的問題,其實是最基本的問題:「爲什麼要設計鞋?」
「我不知道,」他聳聳肩,說道,「我現在習慣了它們。」他瞥了我一眼,想看看能否避開這個問題。「這個漂亮的東西是什麼?」他突然說道,一手抓住我用來標識筆記本頁碼的斷橡皮筋,這玩意兒看來就像用錯了地方的書籤。「我喜歡這個!」
我抬了抬眉毛,提醒他,我們正在談論鞋子。「鞋子?」伯拉尼克嘆息了一聲,「我想……它們有自己的生命吧,」他大膽而言,「它們是獨立的,是你必須穿的。但我不怎麼思考這個。」
有時你會感覺伯拉尼克因爲太忙於想像自己的生活,以致沒有時間去「檢查」它。伯拉尼克閒不下來,不是在閱讀,就是在看電視,要不就在畫圖。在他位於英格蘭西南部喬治亞州風光優美的巴斯市的家裏,他收藏了大量的書籍和DVD(比利•懷爾德(Billy Wilder)的所有影片,恩斯特•劉別謙(Ernst Lubitsch)的所有影片),還有他設計的所有鞋款——大約有1.15萬雙,就收在仿喬治亞風格的壁櫥裏面,以及隔壁的房子裏。他買那所房子就爲了存放這些藏品。「這是鞋子的陵園,」他高興地說道,「不管我點了多少Diptyque的蠟燭,還是有皮革的味道。但我現在有一筆抵押貸款,爲了這第二所房子,我必須抵押貸款。抵押貸款讓我煩惱,因此我就去找我的——你們怎麼叫的,發抵押貸款的人,嗯嗯……」
銀行家?
「沒錯!我去找銀行家,他們說,『可是伯拉尼克先生你沒有問題,你沒有負債,'我說,'可我有抵押貸款,'他們告訴我,我沒問題。可我還是擔心……你的房子沒問題吧?這場危機就是這麼艱難。我想到在工廠裏爲我製作鞋子的工人,我擔心,很擔心。訂單在減少,但我們不能讓他們失業。我並不真的在乎鞋好不好賣,你知道,我不在乎。我並不怨天尤人,只是我對這些人負有責任。嗯,情況很好,他們現在很好。我們在杜拜開了一家專賣店,經營情況相當不錯,在愛爾蘭的Brown Thomas也開了一家。可多數時候,我最喜歡的鞋往往不是賣得最好的。」
他清楚什麼樣的鞋好賣,因爲他在全球各地有200個銷售點,而且每雙鞋都是他親手設計的。他最喜愛的鞋包括:1973年爲奧西•克拉克(Ossie Clark)設計的一款,以櫻花和仿麂皮的綠葉環繞腿部;有著巨大紐扣的鞋(「出自上世紀80年代我的紐扣時期」);以珊瑚和馬皮製成的鞋,2003年曾在倫敦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展出;以及本季新品「Toubid」——踝部繫帶的高跟涼鞋,特點在剪出層次感的足弓部分。他的顧客最喜歡的鞋款則往往是宮廷式樣的,他認爲這種款式「非常傳統」,尤其是「玫瑰紅那種愚蠢的顏色的。是安全的鞋款!」
他設計各種各樣的鞋跟,但表示他最喜歡3釐米的中高跟(也喜歡5釐米的)。目前他對平底鞋興趣十足,因爲「平底鞋走起來難度最大,優雅動人——它們讓你走起來就像馴鹿。女人們真正懂得如何把平底鞋走得好看,最近的也是在上世紀50年代。從電影中就可以看到。」
「我花了十年,才真正懂得如何製作出一雙合適的鞋,我從來沒有製作出完美的鞋,」他一邊說道,一邊揮手錶示不要咖啡和甜點,「我已經接近了,但從來沒有。我必須繼續努力。哦,有這麼多要做。我原來以爲,隨著時光流逝,我會變得越來越厭倦,可我只是變得越來越焦慮。你知道嗎,我不再看新聞了?我不願喪失樂觀態度……」他的話題再一次遠離產品,越來越遠。他用順滑、有如緞子般、綴著金屬片似的話語,掩蓋(受盡腳趾囊腫折磨、佈滿老繭的)的現實。這些話翻來覆去,而餐廳裏已漸漸變得空蕩下來,他陪我走到門口,嘴裏仍說個不停——直到下一場時裝秀。
譯者/岱嵩
義大利米蘭四季酒店La Veranda餐廳
義大利乾酪蘆筍色拉 26.50歐元
蔬菜湯 20.00歐元
氣泡水 7.50歐元
純水 7.50歐元
總計:61.50歐元

與全球最炙手可熱的時尚攝影師馬里奧•特斯蒂諾(Mario Testino)共進午餐,時間當然不會在午間。「我在這兒呆一天,」特斯蒂諾說。「明天要去紐約,週四去洛杉磯,週六去米蘭。我會在洛杉磯做什麼?我可不能談這個。前兩天我在卡普里。那之前在威尼斯呆了兩天,再之前的一週在巴黎。」
祕魯攝影師的生活日程
特斯蒂諾已經過了產生時差反應的階段。他穿一件範思哲(Versace)紫色襯衣,一條艾克妮(Acne)白色牛仔褲——這身裝束很適合參加法國南部的沙灘派對。他很高,有一點被曬黑,不算瘦,但身材還不錯。他說自己在45歲前一直是個「狂熱的派對分子」,經常光顧夜店,但到了45歲忽然意識到,自己「看上去像是俱樂部門衛」。不過,就目前54歲的年齡而言,他看起來頗顯年輕。
時間已近傍晚,我們的午餐被安排在這位祕魯攝影師位於霍蘭德公園(Holland Park)的倫敦辦公室。我們來到一個偌大的、幾乎是空蕩蕩的房間,白牆木地板,一端有一把椅子、一把長椅和一張咖啡桌——都是上世紀60年代的丹麥傢俱。不大的桌子上放著一份郊遊午餐:橄欖、花生、火腿、麪包、調味醬,以及一碗生菜色拉。
特斯蒂諾並不餓,又或者並非如此。他把一粒橄欖送進嘴裏。他的生活是攝影、派對、豪華飯店和飛行的週而復始。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有機會品嚐各式小食。他告訴我,他的最愛是洛杉磯的日本餐廳。他擔心自己的體重。「我的問題,」他說,「是我喜愛食物。」
他也鍾情於祕魯美食,當我告訴他自己對此所知不多時,他變得興奮起來。特斯蒂諾總是處於興奮狀態,這是他的天賦之一,也是他之所以在時尚和名人圈如此成功的一大原因。他總是不顧一切地保持樂觀。他的攝影作品使女性看起來像是她們自己的完美版本。他似乎賦予了她們一點點本不存在的東西。特斯蒂諾使黛安娜公主顯露出天真爛漫的少女特質;他賦予珍妮弗•安妮斯頓(Jennifer Aniston)一種前衛的性感。「她當時剛剛與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分手,」他表示,「她就像個可憐的孩子,而我對她說,『我將讓你性感至極。」
他又往嘴裏送了一粒橄欖,接著言歸正傳地告訴我,祕魯美食是「我所知道的最不爲人知的祕密。除了義大利,那裏是你能喫到最棒食物的地方。」他告訴我,他最喜愛的洛杉磯餐廳的廚師就曾在祕魯呆過一段時間。「那裏有很多海鮮。你知道塞維切(ceviche)嗎?那就是祕魯菜,是用檸檬汁醃製的魚,輔以辣椒和生洋蔥。還有tiradito,也是用檸檬汁醃製的魚,但不加洋蔥。」
他看看桌子。不,他不想喝酒,他說。一會兒他要去參加一個時尚酒會。一會兒?其實差不多就是現在。實際上,他需要在半小時後趕往別處,又或許是40分鐘以後。他的生活由分佈在各大陸的助手安排,並被劃分成若干微小片段——這裏一小時,那裏幾小時。在搭飛機前,他需要知道下一場拍攝必須產生多少照片。通常是一天五張。
「我是個工作狂,我想,」他說。他的動力是什麼?「我認爲是工作本身激勵著我。我喜歡工作。」當我問他大部分時間呆在哪裏時,他表示:「上帝,我每天也這麼問自己。」他的主要居住地是倫敦和洛杉磯。「我一直試圖抽更多時間去南美,」他說,但他「尚未找到一個可行的辦法——就工作而言。」
不過,他最近出了一部關於里約熱內盧的書,書名非常搶眼,叫《MaRio de Janeiro Testino》,書裏滿是派對和狂歡的精彩照片。「這是我經歷過的最難以置信的事情,」他一邊說一邊向我展示此書。「人們半裸著身體,流著汗,那麼性感和吵鬧。」
他總是提前做打算,總是在謀劃。在利馬上學時,他最拿手的科目是數學。事實上,在學校裏他有點像個局外人,不是那種受人歡迎的男孩。正因如此,他了解人的弱點,我認爲這一點恰恰構成了他創造作品的力量。他告訴我:「剛開始拍照時,我並沒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現在想起來,它是件人性化的事情——就好比,你看到某人需要幫助,於是就過去幫忙,或者你看到某人情緒不高,就試圖讓他們振作起來。」
明星拍攝祕訣
例如今年早些時候,他爲真人秀明星傑西卡•辛普森(Jessica Simpson)拍攝了一組照片,他知道該如何讓她顯得迷人。「當時人們批評她發福了,這一點觸動了我,」他說。於是,他使她看上去像一尊雕像——這是褒義的說法——就像是某個多年受人敬仰的人物的照片。他賦予了她高雅的氣質。
類似的,他給梅格•瑞恩(Meg Ryan)拍攝的美麗照片攝於10年前。她當時快40歲了,她可能在擔心她最好的作品都已成過去,也可能在考慮自己是否已失去了一點點讓她成名的聰明但漂亮的氣質。特斯蒂諾做了什麼?他讓她看上去清新如少女一般,她趴在地上,踢著腿,臉上充滿光彩。梅格•瑞恩看上去就像是一個柏拉圖式的完美人物。
「我對梅格的回憶確實有趣,」他說道,「在我給他拍攝的照片裏,我無法認出她來。我什麼都試過了,但還是無法認出她。她看到我很爲難。」他表示,是瑞恩自己建議把光打在她的臉上。
在他給朱莉婭•羅伯茲(Julia Roberts)拍攝的照片上,羅伯茲手裏捧著一個似乎是松鼠玩偶的東西。最終,照片讓她看上去非常有趣,至少很獨特。接著是給凱特•摩斯(Kate Moss)拍攝的照片。多年來,他讓她的面孔看上去至少像10個不同的人,每張照片都一樣的吸引人。她的照片給人的感覺依次是聰明、機智、藝術、天真,一點也不像小報上描繪的那種社交動物。
特斯蒂諾解釋道:「作爲一位攝影師,你要麼拍你自己,要麼拍你的拍攝對象,要麼爲你所供職的雜誌拍照,要麼爲你正試圖與其廣告進行交流的公司拍照。你要麼讓照片看上去和你一樣,要麼你讓照片符合客戶的意圖。如果我爲巴寶莉(Burberry)工作,我會試著讓它看上去像一個巴寶莉女孩,一個巴寶莉時刻。如果我爲範思哲工作,那麼我可能會要求相反的效果。我要讓它變成範思哲。」
他拍攝的女性似乎比男性要多。事實上,與他作品中那些貌若女神的女性相比,他塑造的男性有時顯得有點鬼鬼祟祟、精神失常。他拍攝的波諾(Bono)與納奧米•坎貝爾(Naomi Campbell)的合影,看上去就像一個精神病患者摟著一位公主。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看上去像個在酒吧唱歌的醉漢。查爾斯、威廉和哈利王子則在合影裏神經兮兮地齜著牙笑。對了,女演員克里斯汀•鄧斯特(Kirsten Dunst)看上去卻像天使,而超模吉賽爾•邦辰(Gisele Bündchen)顯得如此美豔,她或許並不完全屬於這個世界。
「女人對我們來說很陌生,因爲我們不是女人,」 特斯蒂諾以男人對男人的語氣告訴我。他補充道:「女人受到的保護和非議、贏得的眼球與讚賞都比男人多得多。女性遠比男性令人著迷。」
他又喫了一粒橄欖。這些橄欖在辣椒油裏泡過,其中一些還塞著小辣椒。我喫了點威爾特郡火腿。
特斯蒂諾認爲,我們之所以更尊敬女人,或許是因爲我們與母親的關係。「女人遠比男人樂於嘗試不同事物。我發現男人會對自己形成一種看法,然後就拘泥於這種看法,這方面女人要強得多。女人會說,『好啊,讓我們試試看!'這或許是因爲女人最終會成爲母親……她們更能接受各種可能性。」
從酒店服務生到大牌攝影師
或許吧。中學畢業後,特斯蒂諾在利馬大學(University of Lima)攻讀法律和經濟學,此後移居美國,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學習國際關係。1976年,他再度改變方向,遷居英國當起了服務生。他就是從那時開始攝影的,還抱著自己的作品集不厭其煩地往返於光鮮亮麗的雜誌編輯部。
特斯蒂諾表示,他在藝術創作上的突破發生於上世紀90年代。當時有更多的女性進入職場,她們因而把自己看作實幹者,而非那些只知道用午餐、品雞尾酒和辦茶會的閒人。他更近距離地與她們接觸,以創造出不那麼故作姿態的女性形象——「把女人真實的一面展現出來,」他說,「而不是把她們變成某種虛假的東西。」
他向我講述了1995年第一次爲麥當娜拍照的經歷。當時她來到他居住近20年的好萊塢酒店夏特蒙特(Chateau Marmont),她的頭髮全部向後梳著,紮成一束馬尾。他當時想,她這樣子看上去就很不錯,沒必要把她重新包裝一番。
談起爲黛安娜拍照,他說當時用手機與她通話的感覺很奇怪。「我會轉過身去,幾乎就像別人可以聽到一樣。」儘管如此,在1997年夏季他爲《名利場》(Vanity Fair)雜誌拍攝的那組著名照片中,他還是成功刻畫了黛安娜的形象,使其不同於自她成爲全球偶像以來其他任何人爲她打造的形象。他說自己之所以可以做到這一點,是因爲他把她想像成那個遇到查爾斯王子前的「普通女孩」。他完全正確。當我們欣賞那些照片時,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個黛安娜:她已神奇地化身爲普通女孩。幾周後她逝世了。
特斯蒂諾一天到晚與名人打交道,但他自己並不算是名人,他也很看中自己的私隱。當我問他有沒有在談戀愛時,他就這個問題思考片刻,然後拒絕回答。「我從來不喜歡談論自己,」他說。
到了起身離開的時候了。身邊的人在做準備,車子已經訂好,有人正取來一件短外套。特斯蒂諾還在就一個他再熟悉不過的話題滔滔不絕:時尚界對骨感女孩的癡迷。他說,模特兒都是少男少女。那個年齡段的人都瘦得皮包骨。「這很正常!我16歲那年也很瘦。設計師之所以聘用那些骨感女孩……是因爲衣服穿在瘦人身上就是更好看。原因很簡單,衣服動起來纔好看。」
再來一粒橄欖?一根胡蘿蔔?不了,他喫飽了。「一旦人們喜歡上我們,或者任何有點肥胖的人,」他一邊抓住襯衫袖口扣緊,一邊繼續說道,「那麼衣服就統統動不起來了,它們會緊貼你的脂肪。正因如此,很難以這類人爲題材製作時裝大片。」
接著,短外套送來了,他也已經離開,去和那些身著華服的女人談話,當然還有更多的小食在等著他。
譯者/章晴、梁豔裳
馬里奧•特斯蒂諾工作室
霍蘭德公園,倫敦
福特納姆&梅森(FORTNUM & MASON)野餐籃(兩人份)
混合鮮橄欖
Carnevale花生
手切威爾特郡火腿
豬肉醬配硬皮面包
水煮鮭魚數份
雞柳條撒莫澤雷勒乾酪和西紅柿派大塊,配芹菜、胡蘿蔔和櫻桃番茄色拉
鮮草莓和薄荷
紙託蛋糕兩個
維歐尼(Viognier)葡萄酒一瓶
Blenheim瓶裝水兩瓶
總計85英鎊

與馬克•雅可布(Marc Jacobs)共進午餐的那天,我早到了十分鐘,他則遲了十分鐘。這通常本不值一提,如果不是因爲雅可布——這位同名時裝品牌馬克•雅可布的擁有者,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簡稱LV)的創意總監,《時代》週刊最具影響力100人的入選者,演員索菲亞•科波拉(Sofia Coppola)與辣妹維多利亞(Victoria Beckham)的好友——與時間有著一言難盡、頗具個人象徵意味的關係。
現年47歲的雅可布,多年來以在紐約時裝週不斷上演糟糕無比的「遲到秀」聞名。他在1997年加入法國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後,同樣的事情又在巴黎發生。2007年,他紐約時裝週的演出更是延誤了兩個多小時,致使若干時尚主編離席。因此,在下一季的時裝週中,馬克•雅可布品牌時裝秀(在經歷了短期的戒毒戒酒治療後)準時準點地開場,而LV的時裝秀甚至提前了幾分鐘,導致幾位毫無覺察的主編錯過了整場秀。(在時裝業,晚30分鐘開始被視爲「準時」;事實上在指定的時間開始纔是聞所未聞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雅可布對待日程安排的態度就像他對待生命中每件事情的態度一樣,是極端的。就像他常說的那樣(在我以前對他的採訪中,也對我說過),他這人不管做什麼事,都容易上癮。
我坐在紐約莫薩(Mercer)酒店的大堂裏時,12點整,他的助理打電話過來,告知我雅可布正在路上——幾分鐘後,他到了,露齒微笑。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正常。
「這是怎麼啦?」當我蹣跚著走向酒店大堂我們的座位時,他指著我右腳的石膏問。莫薩酒店是那種不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極簡時尚之所,卻也因而受到名流喜愛。朗萬(Lanvin)設計師阿爾伯•艾爾巴茨(Alber Elbaz)一直以此酒店爲家,做同樣選擇的還有好萊塢男星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
我告訴雅可布我的腳跟腱撕裂了,他同情地做了個苦臉,並說起自己肩旋肌受了傷,近幾周內就要做手術,因此他最近「完全沒法健身」。幾年前,雅可布做了舉世聞名的轉型,從戴眼鏡、留長髮的神經質男,變身爲從身體到頭髮(就此而言,還有體毛)都精雕細琢的美男子,並從此對他每天兩小時的健身房運動狂熱入迷。
我問他不能健身的話是否改做了些什麼,因爲我以爲他已把對健身的執著轉移到了旁的事情上。「嗯,」他想了一分鐘,然後聳聳肩。「什麼都不做,真的。」
這回答很讓人意外,一如今天雅可布的打扮,他穿著牛仔褲加白色襯衫,而不是蘇格蘭方格「短裙褲」——蘇格蘭短裙和短褲的雜交品種,自兩年前「一時衝動」購買了這類服裝,他就一直不能自拔地穿成那樣在每個公衆場合露面。
「嗨,」我問,「你的蘇格蘭短裙呢?」
「我就是不想再穿了。」
考慮再三後,我斗膽問道:「你在大量收購藝術品嗎?」
這麼問並非毫無邏輯的閒聊。歸功於同包括史蒂芬•斯普勞斯(Stephen Sprouse)、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和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在內的衆藝術家在飾品設計上的通力合作,雅可布幾乎以一人之力讓LV這個奢侈品牌保持了與藝術界最大限度的聯繫。無論是路易威登公司和雅可布本人,都將品牌藝術化的特徵闡釋得淋漓盡致:路易威登在倫敦的最新旗艦店已經開幕,展出了村上隆與吉爾伯特和喬治(Gilbert & George)的作品,同時展出的還有雅可布私人所藏的埃德•拉斯查(Ed Ruscha)、伊麗莎白•佩頓(Elizabeth Peyton)、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以及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作品。過去,雅可布曾因斥資於自己的收藏愛好而陷入債務。我想,也許,他現在正以盡情揮金來取代其「舉重養生法」。
「事實上,我已經很久沒有買什麼了,」我倆並排坐在軟長椅上,他這麼回答道,「前幾天我在佳士得拍賣行買了一件埃斯沃茲•凱利(Ellsworth Kelly)1962年的小作品,不過僅此而已。其實對我來說,買這件東西也是難以解釋的事。」「爲什麼?」我問。
「那件作品只是一個帶黃色弧線的白色方塊。我通常喜歡更具象的作品,而對這類抽象作品我會去欣賞和讚美,但不會想據爲己有。但這次我就是喜歡它……它令我很快樂。」
事實證明,馬克•雅可布正在進入黃澄澄的成熟期。這並不止於其對畫作的態度。例如,我之前曾猜想我們在默薩見面是因爲雅可布住在這裏;在擔任LV的工作後,他把自己的大本營遷到巴黎,而他本人的品牌總部仍然設在紐約。雅可布說,他的確曾有九年,基本住在這個酒店,不過已於兩年前搬出,現在紐約的切爾西區(Chelsea)租了一個地方。同時,他在紐約西區的一個新住宅項目裏買了幢聯排別墅,目前正在裝修,小區由建築師羅伯特•斯特恩(Robert A.M. Stern)設計。
「我喜歡有一個家,」他說,「我喜歡在巴黎我的房屋裏擺滿我熱愛的物件。而且,我意識到我能在紐約和巴黎之間找到一個平衡。以往,我常認爲自己必須在巴黎做LV品牌的工作,在這裏做馬克•雅可布品牌的,我那時總是亂亂糟糟、匆匆忙忙。但是現在,我知道不管我人在哪裏,都能兼顧到兩個品牌,於是我就在紐約住幾個星期,然後再返回巴黎,如此循環。」
不管怎樣,雅可布仍是個典型的曼哈頓設計師。他小時候和祖母生活在上西區,還是十幾歲的少年時,就是夜總會Studio 54的常客。他畢業於Parsons設計學院,並於1988年成爲Perry Ellis的女裝設計師,但在1992年設計了衆所周知的「Grunge」系列後被解僱。如今,他是西區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上名副其實的王者,在那裏他擁有五間專賣店,囊括了他的主線產品,副線Marc by Marc Jacobs,以及童裝Little Marc Jacobs。他目前正在籌建第六家店,這將是一家書店。
因此,他對飯店熟悉到能點一份並沒列入菜單的烤三明治,那是客房服務清單裏的。我要了茴香沙拉。他要的飲料是加冰無檸檬的健怡可樂,我的則是加檸檬無冰。他喜歡這個點法。
「啊哈,我們這不就平衡了嗎?!」他說。
他說,過些時日他將先去巴黎,再前往倫敦參加新店開業,隨後回紐約接受肩部手術。他說,他非常想看到LV在倫敦邦德街的新店,因爲這號稱是有史以來最奢華的一家旗艦店,店中安裝了巨大的玻璃樓梯、一間藝術書店,並設有藝術陳列區。
「你還不知道這家店長得是什麼樣子?」我問。
「還真不知道」,他咧嘴笑了起來,「我的工作是創造產品。好玩的是,我剛剛在畫商拉里•加戈西安(Larry Gagosian)爲理查德•普林斯舉辦的宴會上,碰到了這家店的建築師彼得•馬利諾(Peter Marino)。人家問我,是不是我向LV推薦的他,我只能照實回答,這跟我本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常常在社交場合見面,都爲LV工作,但我們並沒有在一起合作。」
在這個時代,時尚品牌的創意總監往往不僅僅是其產品本身的專家,還需要是一位可以看到「遠大前景」的美學獨裁者,發現雅可布竟然對LV的零售生意不聞不問,這自然讓我非常驚訝。「我畢竟不能把所有事都做完,況且我也不是全才。」他的烤三明治20分鐘還沒到,而他現在依然表現得很耐心。
「假如你也曾經凡事操心,就知道這有多讓人鬱悶了,如果說到品牌的時裝秀或者新鞋設計,我或許不是控制狂,但我對最後的成果有決定權。我有時還要做些超出我專業的事情。我覺得,我應該做的是爲公司指出某種方向,隨後,我就應抽身而出,由其他人對此加以解讀。」
不過雅可布確實會負責產品廣告創意。過去他曾在LV的廣告中起用詹妮弗•洛佩茲和麥當娜這些女星,不過在這個秋冬的廣告中,他將使用的是幾位均已成爲人母的模特兒,廣告硬照「在更衣室裏拍攝,看起來非常美妙。這就是我在本季想要表達的理念:不花哨,不過分追求時尚,只想表達高雅與優美;這是那些不盲目跟風的人會喜歡的衣服。」
其結果便是,在今年3月LV發佈的新品中最後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場「上帝創造女人」式的盛宴:豐胸、蜂腰、大擺裙。雅可布獨特的時尚天賦,讓他把拇指伸向空中,感知時代潮流,並將之賦形於服飾——不論是1990年代的「邋遢」開司米保暖內衣(當時推動了反炫耀性消費的思潮),還是去年的1980年代「新浪潮」時裝展(昭示了近來興起的對於非金融恐慌年代的懷舊情緒)。因此,似乎接下來符合邏輯的提問只能是:他是否認爲「美及其平易可及性」將是下一個後經濟衰退期的流行大趨勢。
「哦,我不曉得耶,」他輕鬆地回答說,「我自己是這樣感覺的。但你也知道,作爲設計師,製作好了衣服,將新品推出,隨後它們就有了自己的存在意義。很久以前我就明白了,人們看完了我的時裝秀,來到後臺後,會跟我講述他們的觀感,我其實大可不必糾正他們的說法,因爲至關緊要的是他們自己的感受。一旦時裝擺進店裏,設計師本人的理念已經無足輕重;一件大衣,不會因爲其靈感來源自世紀之交的英格蘭,就因此成爲件更好的大衣。」
喫了半份三明治,雅可布看起來心滿意足,想去外面抽根菸。有一陣子他煙不離手,不過如今,在抽菸這件事上他也沒那麼執迷了。他上過一段時間MySpace,這會兒也不再上任何社群網站——「Facebook上一堆假冒我的人開的頁面,結果現在總是有人跟我說,『你爲什麼刪除我?我們原來在Facebook上聊得多歡哪。'我只能告訴他們,『那真的不是我!'」不過,對於社群網站,他並無詆譭之意,甚至還將自己設計的一隻手袋以著名時尚博主BryanBoy的名字來命名。
網上關於他的謠言滿天飛——要是按網上的訊息說,他已經跟自己的男友、公關洛倫佐•瑪通(Lorenzo Martone)結了幾次婚,也離了幾次婚。雅可布說雖然很希望結婚,但事實上他目前未婚,並且表示維基百科上關於他的詞條,其中有半數資訊都不屬實。
「這些謠言,有時候會令我心緒不佳。」晃著手中的菸捲,他向我坦承。「但我儘量不受影響;我也不想凡事帶有戒心。」一邊說著,他一邊咬著手指甲,我讓他別再咬了,他低頭看了看手,表示他確實該做個美甲了,不過表情並不那麼擔心。他看起來對於這一切特別……冷靜,特別就事論事。回到桌前,點了咖啡後,我不由自主跟他說,「你現在似乎很解脫。」
「噢,不,」他說,「我還是跟以前一樣痛苦,一星期看一次心理醫生,情緒依舊起起落落。在一場時裝秀前,我會徹夜不眠,心裏想著,『假如觀衆討厭這場秀該怎麼辦?如果我的職業生涯完結、無家可歸怎麼辦?'我會反覆推想最可怕的情形。一次,我一直坐在這張沙發上」——他指了指房間對面的那張沙發——「(藝術家)約翰•柯林(John Currin)問我,『你在幹什麼?'我回答說,『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後他會談起他已經重畫了16次的微笑。但在如此悲觀的情況下,我仍然還有清醒的認識,我明白所有這些反應,都是人性使然。我覺得也正因此,現在我特別迷戀黃顏色。這是積極的象徵,是樂觀的選擇。」
看了看錶,我這才發現,我們聊的時間,已經比預定的時間多了40分鐘。不過雅可布看起來並不介意,他繼續闡述:「我想說,我們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起點,但這樣說顯得太傻。你知道,在時尚界,一切瞬息萬變。」
(本文選自《FT睿》雜誌2010年7月號), 譯/李瑋
1. 茴香沙拉 $7
2. 烤馬蘇裏拉乳酪和燻火腿三明治 $12
3. 低因卡布奇諾 $5
4. 義大利濃咖啡 $4
5. 健怡可樂 $7 ×2
總計$47.68 (含服務費)
莫薩酒店:紐約蘇豪區莫薩街147號

菲比•菲羅(Phoebe Philo),37歲的時尚品牌Céline創意總監,作爲一年前神奇般改變時尚潮流、一掃時尚界陳年累積浮華之風的扛鼎人物,其真人之纖弱實在令人驚歎。作爲2010年英國年度設計師的候選人,她同時也是今秋巴黎女裝秀上最受歡迎作品系列之一背後的設計師。
菲羅中等身材,條縷狀棕發,顴骨突出;一件黑色皮夾克、男式襯衫和一條黑色寬鬆褲子包裹著她瘦弱的骨架,使她看起來彷彿弱不禁風。但是,她卻選擇了倫敦市克勒肯韋爾區的聖約翰餐廳(St John)。這是一家以菜單中囊括各種「包羅萬象的」雜碎和內臟而著稱的餐廳,因此,顯然她有食肉、愛好高蛋白質食物的一面。
「這家餐廳是我一個朋友經營的,」來到這家簡約樸實的白色餐廳時菲羅說。她坐在用紙覆蓋的桌子旁表示:「它有著我喜歡的直率。它非常的直截了當。」比如,在菜單上有一道菜叫「帶豆莢豌豆」,那就是未加工的、帶著豆莢的豌豆,就像你在市場上買到的那樣。或者,像菲羅說的那樣,可能「就是採摘自花園」的那種。她點了其中的一些,並加上一些新鮮檸檬汁——在美國榨的那種,由檸檬果汁、水和糖混合而成的;她還點了一份蔬菜沙拉,一些醃製的青花魚和一份烤牛肉三明治,因爲她「非常想要一些白麪包」。我則點了檸檬水,一些花椰菜和扁豆,還有一份蔬菜沙拉和一份乳酪片。見我如此點菜,菲羅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是素食主義者嗎?」她說。
我聳了聳肩。「我很抱歉,」她抽動著嘴角說。因爲說實在的,我們都知道我的飲食習慣不是現在的談話重點。「這裏的食物不錯,」菲羅說,此刻我們都打量著房間的四周。菲羅接著說:「但我對這裏的裝飾不是很鐘意。」
這顯然是正確的——不僅是對這家餐廳而言,事實上對我們的談話也是如此。菲羅說話簡潔明晰,正如她無名指上的金環(一粗一細),她說話時很認真,從不誇張或如演講一般激情四溢,她語調柔和,並且很少用形容詞。她不以喋喋不休的話語來保持談話的連續,對長時間的中斷泰然自若。她考慮問題非常透徹,這既體現在某款襯衫的設計上,也體現在她選擇討論該款襯衫的地點,以及她最初作出開始設計該款襯衫的決定上。
看起來有點像是書讀得太多而顯得偏執,但我不這麼認爲。我認爲菲羅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畢竟,她已爲她的自我意識贏得了認可。
菲羅在法國出生,父母都是英國人(她的母親是一位平面設計師,父親是測量師),作爲家裏的三個孩子之一,她在倫敦長大,就讀於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Central S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在爲Chloé效力五年並取得顯赫成功後,四年前菲羅功成身退。1997年,菲羅在藝術學院的朋友史黛拉•麥卡托尼(Stella McCartney)被任命爲這家法國時裝公司的創意總監,後者也將菲羅帶進了公司。
2001年史黛拉離開Chloé,去開創與其本人同名的時尚品牌,菲羅接任Chloé創意總監。幾年後,菲羅將Chloé品牌轉變成確立時代精神的機器:讓一代女性相信,她們非常、非常希望穿上成人版童裝的組合:粗木鞋跟,蕾絲花邊的娃娃式束腰外衣,以及鄉土氣息的裙子(並且願意爲此花很多錢)。
此外,在她擔綱Chloé品牌設計的時間裏,菲羅還卓有成效地樹立了「It」手袋之風,使得以Paddington、Edith等特色名稱的手袋銷量翻了一番還多。2004年她與藝術品經銷商麥克斯•威格拉姆(Max Wigram)結婚,當年就有了第一個孩子瑪雅。此時菲羅認爲她已無法在倫敦的家庭和巴黎的工作間取得平衡,因爲這需要她在歐洲之星列車上不斷往返兩地。所以,儘管她贏得了當年英國年度時裝設計師大獎,她還是辭掉了工作「以便有更多的時間與家人相處」。這又是一個如同獵殺涅墨亞雄獅(Nemean lion)的驚世之舉,令時尚界大喫一驚:拋棄所有的成功?留在家裏帶孩子?她怎麼做得出這樣的選擇?
「這相當容易,」她一邊說,一邊快速剝開豌豆。
她離開時尚界兩年,生下另一個孩子馬洛(Marlow,男孩),之後她決定「重新出山」,並且要能自己做主。2008年9月,她成爲奢侈品集團路易威登(LVMH)旗下公司Céline的創意總監。
Céline的何種特質讓她下定了復出的決心?這家公司在1996年被路易威登以4.12億歐元收購,這些年來一直不停地更換設計師,始終未能確立其自身的風格——1997年至2004年由邁克•柯爾斯(Michael Kors)擔任創意總監,然後是羅伯託•麥尼切蒂(Roberto Menichetti)任職一年,接下來是麥尼切蒂的前任助手伊萬娜•奧馬澤(Ivana Omazic)。一般來說,那是一個註定要失敗的品牌。沒有人對它有任何的期望,因爲大多數人都不會想到這個品牌。
「當時Céline對我來說確實沒有什麼分量,」菲羅邊說邊把豌豆推向一邊,以便給剛上的三個盤子騰出空間,然後叉了一些生菜。她沒有把缺乏個性看成是一個問題,反而認爲這是一種資產。
「當我考慮是否去Céline工作時,我並沒有太多考慮公司的過去。」她說。「也有其它公司向我發出復出邀請,但它們要麼不合適,要麼不允許我留在倫敦,而後者對我來說是沒有商量餘地的。不過爲Céline工作就不存在這個問題,而且我爲這個品牌不再代表任何內涵而高興。沒錯,賭注是有點高,因爲每個人都在關注我,同時因爲經濟形勢不佳,競爭更加激烈,但我認爲,Céline過去是什麼、怎麼樣和我毫無關係。我在任期間,它將會是我打造的結果。」
這種觀點堪稱時尚界的「離經叛道」,因爲這個行業的一大信條就是,在打理一個歷史久遠的品牌——例如迪奧(Dior)或紀梵希(Givenchy),或是1945年由賽琳•威皮安娜(Céline Vipiana)創立的Céline時,品牌的「DNA」、其內涵、該品牌的當代產品是否真正保留了這種「DNA」等,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前提。對於一個設計師而言,要拒絕這個前提,就如同要砍掉九頭蛇的腦袋一樣艱難。
「我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去思考『這是Céline嗎?』這樣的問題,」菲羅聳聳肩,一邊喫完她的青花魚,一邊說出這句明顯有所保留的話。我能感受到,她認爲——但不會言明——那種賣弄大道理的做法實際上很愚蠢。不論是魚還是服裝,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其出身,而是最終產品的好壞。她花了六個月時間敲定了一份令自己滿意的合同,這份合同能讓她既掌控自己的生活,也能掌控其工作成果。路易威登在倫敦爲她建立了一個工作室(Céline之前的總部設在巴黎,它之前所有的設計師——一個美國人、一個義大利人和一個克羅埃西亞人,都不得不搬遷至更接近總部的地方,未能享受菲羅的待遇)。公司關閉了大量店鋪,並銷燬了所有的舊品庫存,因此沒有了任何關於過去的實體提示。同時,公司也賦予了她確立品牌審美觀的權力。
「對於時裝,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麼、不想要做什麼,」菲羅說。「我想要一些讓人感覺誠實的東西,那種我的穿衣風格和生活方式綜合起來的感覺。我認爲它得相當簡單和真實。」
於是駝色套裝系列出現了:高腰身,剪裁完美的下襬和A字形的帆布超短裙,並且常常以黑色皮革裝飾;以及超大尺碼、潔淨挺括的白襯衫。這些設計和以前的產品截然不同——既不同於菲羅之前在Chloé的設計,也不同於豹紋斑點或是施華洛世奇裝飾盛行時代任何其他設計師的設計,並在時尚界再度掀起對她的瘋狂崇拜,並且又一次證明這樣一點:作爲一個設計師,菲羅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明白像她那樣的女性想要穿什麼。(她穿的也是自己設計的衣服,她穿的男士襯衫來自2011年春季預展系列。她表示,現在她衣櫥的「半壁江山」都屬於Céline。)
她的第二組設計以她獨創的編織爲特色,保持了與第一組相同的風格;第三組也一樣,爲了向巴黎致敬,在這個系列中菲羅放鬆了她嚴格的廓形剪裁要求,選用了隨性的蠶絲褲,並且用黑色系帶的連身褲裝取代了晚禮服。在她的首個廣告宣傳活動中,模特兒的臉孔從下巴和脖子向上被模糊化處理,並且最令人喫驚的是,這些模特兒沒有經過任何粉飾和化妝,意圖「讓產品成爲明星。這不關乎生活方式。這隻關乎服裝——要提高它們的聲望。這就是目標,沒有任何掩飾。」她從來沒有請過明星充當品牌的「形象大使」,她甚至不喜歡用「品牌」這個詞,而寧願用「公司」。
「我認爲這是一種很過時的做法。對於我來說非常重要的是,在Céline要一步一個臺階的前進,我們沒有很龐大的戰略規劃。我深刻意識到我是一個人,有人的侷限,並且我必須尊重這一點。」
顯然,她的侷限也包括她的胃口。當她的三明治上來時——兩大片面包,中間夾著一小片烤牛肉——她看著它,嘆了口氣說:「不知道都喫了這些會怎樣。」然後她對三明治進行解構,按自己的意思重新設計,更具流線型,更規範 ,於是只有一片面包裹住牛肉。
「時間是我最奢侈的享受,」她說。「找時間做些時裝之外的事情,我認爲這對於一個設計師來說非常重要。」每天她送孩子們上學,大約上午十點到辦公室,再回到家哄孩子們睡覺。「從未感到輕鬆過,」她說。
不工作的時候,她花很多時間在牀上讀新聞,看報紙。她看的是紙質報紙。她並不花很多時間掛在網上,不像很多時尚界同行那樣依賴虛擬世界,不論是公事還是私事。她甚至不上Facebook。「我想不到有什麼比那更糟糕了,」她說。「相比之下我寧願在街上裸奔。我不用網路,也不喜歡和朋友透過網路溝通。我只是不希望和並非家人或朋友的人有太多的接觸 。」
「我一直想做一些在一天工作結束時可以帶回家東西的事。」她邊說邊謝絕了咖啡和甜點。「我在學校最快樂的記憶與藝術有關。從事時尚業只是這段記憶的延伸。我是說,我喜歡那種把創意變成女性穿著的想法。」
正如對Céline的改造一樣,這番話聽起來也近乎神話一般。
..................................................
從「It」手袋到駝色大衣——
菲比•菲羅經典作品一覽
作者:尼古拉•柯平(Nicola Copping)
Chloé Paddington手袋
菲羅任職於Chloé時,曾多次引領時尚界潮流,但影響力最爲強勁的作品當數「It「手袋。Chloé Paddington手袋2005年3月上市,售價爲750英鎊,它實際上是一個小挎包。菲羅以堅硬黃銅釦和一把粗短掛鎖相組合,構成其標誌性的螺旋形。該款手袋的流行導致大街上出現了許多仿製品,待購購買的顧客排成長長的隊伍。
Chloé娃娃裝
菲羅在Chloé時的審美觀念很簡單:漂亮、女性化且容易穿著。但是,她的每一款作品都有一種諷喻的味道。以流行的、被多次模仿的娃娃裝爲例:它出現在2006年春季T臺秀上,蓬鬆的袖子,高腰線剪裁,以柔滑的蠶絲製成,它十分的少女化,除非你配上粗跟耐磨的鞋子。這款服裝教會了成年女性如何穿出少女的味道。
Chloé疊跟高跟鞋
在紡錘型的細高跟鞋風靡多年後,菲羅抓住一個機會異軍突起,以鞋跟較爲粗笨的鞋品與其輕快飄逸的罩衫裙交相呼應。堆疊的木製鞋跟和楔形鞋跟出現在涼鞋、繫帶靴以及及膝的棕色皮靴上,爲Chloé的粉絲和世界各地的女性提供她們急需的舒適性和行路穩定性。
Céline皮革T恤
在菲羅來到Céline之前,皮革和T恤通常是相互不沾邊的兩個詞。但在菲羅爲這家法國公司舉辦的第一次時裝秀2010年春季時裝秀上,皮革和T恤結合到了一起:方方正正,平滑光潔,以黑色和橄欖綠色先後出現。就耐用性和實用性而言,再沒有比種組合這更有說服力了。瓦利斯(Wallis)、瑪莎百貨(Marks & Spencer)和多蘿西•帕金斯(Dorothy Pekins)很快跟進推出自己的廉價款式(Céline的售價達1978英鎊)。皮革終於被歸入主流。
Céline駝色大衣
沒有什麼衣服能比駝色大衣讓女人的衣櫃顯得更加底氣十足了—— 菲羅很清楚這一點。更重要的是——她比別人先知道這一點。在她的首款Céline系列中,駝色比比皆是,接下來在她的2010年秋季預展目錄上,駝色再次出現:一件縱線剪裁的鑲羊毛駝色大衣,售價2442英鎊。在幾周後的2010年秋季時裝秀上,駝色大衣已是無處不在。菲羅知道女人想要什麼,甚至在她們的想法出現前就已知道,這種能力已經成爲她最傑出的資產。
譯者/李慧
帶豆莢豌豆 4英鎊
花椰菜和小扁豆 6英鎊
醃製青花魚 7.1英鎊
乳酪片 9英鎊
牛肉三明治 6.5英鎊
鮮檸檬水X3 5.1英鎊
瓶裝蘇打水 3英鎊
蔬菜沙拉X2 9英鎊
總計(包括服務費)49.7英鎊

與現年43歲的Jimmy Choo創辦人兼CEO塔瑪拉•梅隆共進午餐前,四季酒店(Four Seasons)的餐廳領班把我們領錯了包間,或者準確地說,把我領到了其它包間。其中有兩個包間:一個叫Grill Room ,另一個叫Pool Room,前一個包間面積小、木質裝修,靠近酒吧;後者面積大得多,位於酒店後面,圍著一口汩汩的大噴泉而建。時尚圈的人一般喜歡Grill Room包間;而銀行家與大公司老總則比較青睞Pool Room包間。比方說,梅隆的叔叔(她前夫的叔叔,梅隆家族的族長)傑伊•梅隆(Jay Mellon)喜歡Pool Room包間(他倆只要一起喫飯,傑伊就準會帶她上這兒來),這就是爲何餐廳領班自認爲我們約好會面的地點是在Pool Room包間的原因所在。
但是,任何讀過小報與broadsheet(一種大幅尺寸版面的報刊)的人都知道:說到塔瑪拉•梅隆時,啥事都不能僅憑想當然。所以我在Pool Room包間裏喝著聖沛黎洛礦泉水(Pellegrino)坐了足足有5分鐘後,纔有一位滿面羞愧的服務員找到我,把我帶到Grill Room包間,一路上還不停地向我道歉。
找到梅隆時,她正躺在沿牆的長條形軟座上,小鳥依人地偎依在銀行家奈特•羅斯柴爾德(Nat Rothschild)的懷裏,身穿豹紋緊身絲裙,腳穿周仰傑黑色短靴,這雙靴子相當眼熟,記得自己曾在YouTube網路影片中見過它們,當時放在她位於第五大道(Fifth Avenue)寬敞公寓房裏可以進出換裝的衣櫃中,衣櫃裏還有她那幾百雙各種款式的周仰傑履鞋。(她從華納CEO小埃德加•布朗夫曼(Edgar Bronfman Jr)手中以2000萬美元購得該套公寓房,在Real Estalker的部落格中對此有詳細介紹)。
換句話說,看著她在紐約住宅區的高檔餐館與國際級大腕共進餐,你可能覺得她的模樣活象個花瓶妻子——實際上,如今她既非人妻(2003年她沸沸揚揚地與馬修•梅隆(Mathew Mellon)離婚,還有鬧得不可開交的法律官司,她指控馬修僱用駭客侵入其電腦,但如今兩人又成了朋友),也非任何人的玩偶。相反,如今倒是她正忙於不斷「網羅」自己的玩偶。
去年剛入秋時,因對英國時尚業作出的傑出貢獻,她在倫敦被女王授予官佐勳章(OBE)。如今Jimmy Choo在全球32個國家開了115家門店,總估值接近5億英鎊。再後來,就在我倆會面前一週,她同配飾界的大姐大安雅•希德瑪芝(Anya Hindmarch)、傑西博的安東尼•班福德爵士(Sir Anthony Bamford)等許多名人一起,被大衛•卡梅倫首相(David Cameron)任命爲新的全球貿易特使。
與羅斯柴爾德(他另有自己宴請的客人)告別,我倆到自己的桌子坐定後,她承認說, 「這事我沒想到。」但又不算太驚訝,她繼續說,因爲和希德瑪芝以及安東尼爵士不一樣的是,她並沒有深度介入保守黨的政治圈(雖然她2006年就結識了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當時他倆一起出席了面向英國企業的一個會議)而是因爲,「哎,你知道我當時的情況嘛。」
我說,該不會是指這件事吧——在Google上搜索「塔瑪拉•梅隆」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刊登在去年早先出版的Interview雜誌上她的一張側影照,旁邊就是由泰利•理查森(Terry Richardson)爲她專門拍的一張裸照,照片中的梅隆躺在沙發上,頭往後仰著,嘴裏抽著煙,手裏抱著一隻貓遮住了她的私處?
「沒錯!」她笑著說,把點菜的事忘得一乾二淨。「我不相信《每日郵報》(Daily Mail)會利用這事(我擔任貿易特使)作爲重印那張照片的『契機』——尤其是由於該照片的版權還在泰利手中,況且(我覺得)他永遠都不會出售它,所以我認爲不會有啥問題。但《每日郵報》未經許可直接就把照片登出來了!現在泰利已經要求他們撤下照片,如今照片已經從Interview的網頁上刪掉了,但還有人在互相傳。」
於是我就問她:你當時真沒想過照片會流傳出去嗎?狗仔隊(paparazzi)偷拍到了她在度假時上身一絲不掛地與前男友克利斯汀•史萊特(Christian Slater)在一起曬太陽浴的照片,她默許衆多報紙予以刊登,難道這樣的梅隆真那麼幼稚嗎?
「總有那麼一小撮別有用心的Interview雜誌讀者,」她聳聳肩說。「這完全是個特例,我真的不知道這一切。」她明顯看出我不信她的解釋,但睜大藍色的雙眼,翻轉著看著自己,並堅持說她確實沒那麼玩世不恭。我這纔有點相信她說的話。
再說,卡梅倫首相與他的手下也似乎並不在意——至少他們迄今爲止還沒找她談及此事——整件事一經媒體刊載後,周仰傑公司現在的控股股東TowerBrook私募投資公司也未發表任何意見。「很顯然,整件事算是風平浪靜地過去了,」她笑著說,似乎連她自己都覺得不太相信。畢竟正常情況下,如果一家全球性公司的「C級別僱員」(指企業最高階主管理層,譯者注)的裸照遭曝光,隨之而來的強烈抗議不僅會涉及其行爲得體與否的問題,而且可能因此作出靠不住的判斷,並隨後要求其離職。不管怎麼說,我是會這麼想的。不過,與餐廳領班一樣,我判斷錯誤。(我沒想到的還有,)這時梅隆突然大聲叫道:」我們還沒點菜呢!」
我們坐到這張桌子已經20分鐘了,服務員也一直在不遠的地方等著。我想她也許壓根就不餓。「我想要金槍魚生牛肉片(tuna carpaccio)以及多佛鰨魚(Dover Sole),」她說,這是道垂涎已久的主菜(但與預想地一樣,她沒要酒,只要了健怡可樂(Diet Coke);畢竟這是在紐約,她保持清醒狀態已經「大約15年」了)。我自己點了金槍魚,還要了份湯,就爲陪著她。梅隆骨質身材,但也飯局不斷:就在我們會面後的第二天,那天適逢感恩節,她約好與退休的時裝大師華倫天奴•格拉瓦尼(Valentino Garavani)共進午餐,晚上又約定與前夫一家人共進感恩節晚餐。
她已經成功被梅隆家族接納;這就是她緣何於2008年從倫敦移居紐約的其中一個原因:如此一來,她8歲的女兒阿拉明塔(Araminta)能進一步培養與她父親及整個家族的感情。雖然梅隆與她父親湯米•葉爾戴(Tommy Yeardye)感情很好,她父親是維達•沙宣(Vidal Sassoon)的合夥創辦人,是她最早的贊助人,給了她15萬美元幫她成立了周仰傑公司,但她說她母親安(Ann)是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自從她父親於2004年去世後,她就再也沒和母親及兩個弟弟說過話。
此外,生活在紐約還能讓梅隆設法擺脫狗仔隊的糾纏,況且美國還是周仰傑公司最大的市場。
「我從一開始就明白我們的產品得要進入美國市場,因爲這裏有充足的購買力,」 她說,這時她要的金槍魚端上來了。「不把美國算在內,你就不能算是全球性公司,再說我本人一直想要實現全球化經營。正常情況下,英國品牌得需20年時間才能飄洋過海打開美國市場,但我們在美國經營不到3年就開了三家門店,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原因就在於我們爲參加奧斯卡頒獎晚會的女星們定製系列鞋履產品。」如今透過這每年一次約定俗成的贊助,梅隆成功地於奧斯卡頒獎晚會前一週在半島酒店(Peninsula Hotel)開設專賣店,提供手工染色鞋履去搭配明星們的禮服,Jimmy Choo是第一家成功利用奧斯卡紅地毯宣傳魔力的品牌。
「但我們做到這一點,完全是因爲那時父親出資幫了我。你能想像得到遊說銀行家時的情形:我要用你的出資,免費給那些女明星提供鞋履,行嗎?他們肯定會這樣告訴我,『你腦子有病,』然後就一口拒絕。但父親與維達•沙宣一起合夥干時,有一次在日本,他讓沙宣當衆爲他理髮,沙宣理解了我父親的苦心,於是同意向我出資。」
梅隆說,父親教會了她「要相信直覺。我認爲那是最大的力量源泉。教育程度太高的人往往不願意冒險。」梅隆沒有上過大學,所以不存在想不到這一說。她詳細解釋道:「投資者會事後統計你的銷量,再製訂出未來成長的計劃,但他們選不中哪些產品能賺錢。我卻能做到,而且我的工作就是讓他們明白。」
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佐證。2001年,她做出全盤買下Jimmy Choo的決定後,當時圈內一位大名鼎鼎的製鞋商(他認爲應該爲少數精英女性設計新款女鞋)與梅隆的理念(她的想法是在癡迷時尚的潮人引領下佔領全球市場)相左,於是梅隆與她父親開始尋求圈外的投資。他們出售了51% 的股權給私募資本公司Phoenix Equity Partners,對方持股到2004年後,把股權賣給了獅王資本(Lion Capital),獅王持股了三年後,又把股權賣給了TowerBrook(梅隆持有Jimmy Choo公司17%股份)。這使得Jimmy Choo並不僅僅在英國、而是成爲全球時尚界與私募資本合作成功的典範:雖然私募資本與時尚業在2000千禧年前後打得火熱,但很少有基金能夠做到把時尚界難以預測的週期與自己慣常的持股期(通常3至5年)步調一致。比如說,瑞士鞋業製造商巴利(Bally)於1999年遭收購後,又進行了艱難的品牌重組之路,即便如此,全球私募資本公司TPG一直持有它的股權長達9年。
「關鍵是業績,」梅隆現在說。「你只要掙錢,這些股東就高興。所以即使私募資本的掌舵者可能不明白你所做的事——再說我所做的事他們就壓根不懂——但他們會慢慢信任你。」
然而,她承認(這時她要的多佛鰨魚端上來了)這一切讓人筋疲力盡。「正當你剛剛熟悉這一屆董事會,他們卻決定要賣掉公司,於是你又得從頭開始。」比如說,你得重新向新董事解釋諸如「髮型與化妝品」如何重要這樣的事,她說,「但他們就是雲裏霧裏。」你得耐心向他們一點點解釋對創新低估或自以爲是所導致的嚴重後果。
「我當時太年輕,每一次出售股權時,沒有真正理解私募資本的本質,」她繼續說。「現在回想起來,我真希望自己有傢俬募公司,(真要是那樣的話),只需直接接洽銀行,讓它們借給我要的錢就行了。」
但如今的現狀是:「即便我想買下整個公司,我也無能爲力,」雖說她如今身家約1.02億英鎊,而且真得想全買下來。相反,在(通常私募資本持股)三年期快結束時入股的TowerBrook,如今正對Jimmy Choo進行「戰略估值」,然後再決定下一步的舉措:是把Jimmy Choo賣給另一傢俬募資本公司,抑或將它上市,還是繼續持有。梅隆不願就公司的未來預設任何圖景,雖然她的確說過:自她2008年擔任露華濃(Revlon)董事以來,曾親眼目睹了公司上市所要經歷的艱難險阻。不管情況如何,她希望股東們能致力於公司的長遠發展戰略,她目前正在就此進行運籌帷幄。
「我認爲樹立一款奢侈品牌需要30年,」她說著,喫了一半的魚,然後又要了咖啡,「所以說我們的創業只是過了半程,我還任重道遠。我認爲我們能把Jimmy Choo打造成生活時尚品牌——公司與高階零售連鎖品牌H&M的合作就清楚表明了一點:消費者喜歡我們推出的任何產品,包括男裝、女裝以及珠寶類。這些我全想做。」
她事實上說到做到:旗下某款香水預定明年推出,然後是男鞋,再之後是童裝、手錶、珠寶、家居用品等等。也許在打造品牌的下一個階段,爲保險起見,她自己會充當香水的「代言人」,會在廣告宣傳中親自披掛上陣(當然是穿衣服的):頭往後仰,香脖露出來。當然這不會是她籌劃的唯一一次自我推介。
因爲我們走出餐館時,梅隆提及她想要出書,是她的自傳。「關於我的事有這麼多的不實之詞,我覺得我應該原原本本把它寫出來,」她說。於是我問她:是全部嗎?毫無保留的事實真相?
「當然是全部囉,」她笑著說。然後又提到她結識的一位導演曾說:若她真想把自己的事情告白於天下,他倒有興趣把它拍成電影。
我問她:誰呀?
也許你猜測會是蓋•裏奇(Guy Ritchie)或者馬修•沃恩(Matthew Vaughn)。告訴你吧:這人是皮特•摩根(Peter Morgan),他是高品味的漫談類電影《福斯特對話尼克松》(Frost/Nixon)及《女王》(The Queen)的編劇
價目表:
三杯蘇打水/純淨水:13.5美元
蔬菜色拉(Crudités):10美元
2份金槍魚生牛肉片:50美元
清燉肉湯(Consommé):16美元
多佛鰨魚:65美元
咖啡:6美元
熱牛奶咖啡:6美元
總計(包括稅及小費):181.29美元

就在我與化妝品界的教父及慈善家倫納德•勞德(Leonard Lauder)相約共進午餐前的幾周,他曾給我發過這樣一封電子郵件:「問題是:在何處見面?若是談論權力話題,採訪地點就在四季酒店(the Four Seasons);若是談論媒體話題,採訪地點就在邁克爾餐館(Michael』s);若是探討藝術界話題,地點就選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我回復:您定。於是他選中了四季酒店。然而就在我們午餐會前一天,他的祕書打電話給我,「您能跟勞德先生說幾句話嗎?」她問。電話中他一上來就說:「我們約好今天一起共進午餐。」我說,沒錯,是在四季餐廳,我正與你祕書敲定此事呢。
「稍等一下!」他說。「聽我說咱這次午餐會去哪兒。我昨天去了四季酒店,那個地方死氣沉沉!我們應該找個熱鬧點的地方。咱們去邁克爾餐館吧,那兒動感十足。」就依你,我說,並提前幾分鐘趕到了邁克爾餐館,原因是作採訪時,我喜歡先行趕到會談地。但沒想到勞德先生已經捷足先登了,他坐在靠凸窗的那張主桌旁,沐浴在陽光裏,身穿藍色泡泡沙西服,扎著領帶,還配著渦紋花呢裝飾方巾(pocket square),他坐那兒能縱覽整個餐廳。「我先到了!」他高興地激將我。「我可不想讓馬克•雅可布(Marc Jacobs)那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
「馬克•雅可布那樣的事」 是指我曾邀這位LV設計師參加與《金融時報》共進午餐訪談會,當時採訪首先從他遲到說起。換言之,甚至就在我們坐定開喫之前,勞德就以實際行動表明:首先,他很在意我心情快樂與否,即便他是採訪對象;其次,他能在短時間內在任何地方訂上自己中意的餐桌;再有就是這個地方他已事先踩過點了。
這表明了他一貫的策略:「我會竭盡全力於我有利的方向做事,我知道你知道我會以身作則,你也心知肚明,但今天咱倆不談這問題,因爲咱倆都要聰明許多」,這一點讓人印象深刻。他設法同時做到奉承與操控——仔細一想,覺得這很準確地指出了化妝品界高階主管成功所需的能力素質(或者就此而言,所有高階主管皆是如此)。例外情況是:77歲的勞德已不是化妝品界的高階主管了。
「我已經退休了!」他笑著說,揮手示意提麪包籃的服務員走開,於是當服務員走到我跟前時,勞德說,「不,不!她也啥都不需要。」
事實上,我說我需要。
「真的嗎?」他看上去有點喫驚,然後開始自責起來:「你很苗條,所以我自以爲你不需要。」他要了份不加橄欖的尼斯沙拉(Salade Niçoise),又要了一個空盤子,還要了點調味品,然後湊近我跟前說:「每天早晨,我喝一杯無脂酸奶,若桃子上市時,就喫一個切成片的桃子,還有薄薄一塊全麥麪包。早餐就只喫這些東西,我可不想長胖,還想保持好體型。」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胃,停了一會兒接著說:「你覺得我是A型血的人嗎?」
實際上,要我說:若是倫納德•勞德退休,那我就該是核物理學家了。
「哎,現在我是公司的名譽主席,」勞德說。「公司薪酬委員會的負責人迪克•帕森斯(Dick Parsons,時代華納(Time Warner)前CEO)對我說,『您不能再領正常的薪酬了,我們該怎麼辦?』所以我們對此進行了討論,他對我說,『按天給您津貼如何?』我說,『行啊』。然後他又說,『但我們得上有封頂。』我說,『可以』,我上了6個月班,這就是我今年按日領津貼的最高上限,所以嘛現在我屬於免費上班,」他笑著說。
「當然,我是公司最大股東,因此嘛,我也算爲自己打工。但是我經常說我上班就得有報酬。爲什麼我老提這樣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呢?」但當我正要說時,他已經接著往下說了:「因爲這是我從商以來最快意的時刻。如今的公司是跨種族、多品牌、跨空間、跨國經營!現在真的是其樂無窮!」
勞德肯定清楚。1958年他從母親艾絲黛(Estée)手中接過公司(創辦於1946年)起,一直在從事化妝品行業,雖說自他出生後,他一直非正式地涉足此行業(除了兩年在海軍服役外)。他親眼看到公司年銷售額從1958年的80萬美元飈升至如今的50億美元,從只在一國發展到如今在全球140個國家開設門店,旗下品牌從一個發展爲29個,併成功使公司上市,還把它發展成爲全球化妝品五大巨擘之一(位列聯合利華(Unilever)與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這樣的大衆市場公司之後)。他已將公司交由兒子威廉(William)掌舵,威廉如今是公司的董事長。巧的是,威廉也在邁克爾餐廳,他走過來向父親打招呼,並與之商討送自己女兒到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事。
經營化妝品讓勞德成了富翁——去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倫納德•勞德位列第212名,公佈的淨資產達42億美元。他在紐約第五大道(Fifth Avenue)有一套專門收集藝術品的複式公寓,在弗羅裏達、瑞士以及紐約州北部均有豪宅。他與他弟弟隆納(Ronald)共同出資在母校賓州大學商學院成立了勞德學院(Lauder Institute),賓州大學快成勞德家族成員共同的母校了(威廉曾就讀於此,隆納的女兒、現雅詩蘭黛副總裁兼創意總監艾琳(Aerin)也曾就讀於此)。勞德與妻子伊芙琳還在紐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幫助設立了伊芙琳•勞德乳腺癌研究中心(Evelyn H Lauder Breast Center at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2008年,他與隆納一起成立了老齡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ging),幫助研製治療阿爾茨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即老年性癡呆)的臨牀新藥。
由於沒有正式頭銜,當我問他該如何定位自己目前在公司的角色時,他告訴我,「道德核心人物。」鑑於目前世人對大公司的普遍評價(越來越把它們看作是一羣唯利是圖的強盜資本家),我覺得這算是個蠻有趣的稱呼。
「我不覺得公司執行家長制有啥不妥,」勞德說。「我們公司的家長制氛圍很濃。我們有非常不錯的健康計劃——我們對員工體貼入微。」我們點的沙拉端上來後,勞德開始把他點的帕爾馬乾酪(Paternalistic Parmesan)夾到所要的空盤子中,我就問他說這話什麼意思。
「我們有位高級銷售代表患了癌症,她的醫生告訴她將不久於人世。她給我打電話,哭得很傷心,我馬上叫我認識的一位醫生給她看病,並讓祕書用專車接她去看醫生,如今她活得好好的,」他說,正色看著我。「只有手下員工想讓你成功,你方能成功,」他說。
勞德描述自己目前另一個角色是「首席教官」( chief teaching officer),他清楚地意識到要把自己一生積累的真知灼見向員工傳授。他如今仍在公司做的一件事就是舉辦各種各樣的員工培訓班。比方說,他舉辦的一個培訓班,透過研究卡卡圈坊(Krispy Kreme)、星巴克(Starbucks)以及家得寶(Home Depot)等經典案例來探討「怎麼與其它公司處好關係,怎樣會交惡」,勞德說,他在培訓班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從紙袋裏取出香奈兒五號香水(Chanel No 5)、倩碧 (Clinique)、樂之餅乾、納貝斯科(nabisco)與可樂,然後問培訓員工這些產品共性的東西是什麼。他問我,停了一會兒就說,「告訴你吧,它們不胡搗鼓自己的標識和色碼。」
在課上,他總結了十條承諾以及諸多禁忌。他喜歡做標牌。其中一個寫道,「就直截了當拒絕。」這指的是零售合夥人可能想讓推銷雅詩蘭黛的銷售員做勞德不允許做的事。勞德反覆灌輸他的員工:對奢侈品牌來說,最最重要的是控制式分銷。「上週五,我召集倩碧高級銷售總管開了個會,我談了很多關於能力的問題,」他說。「能力就是俘獲消費羣的擁有者:品牌或零售商。如果員工擔心會得罪重要的合夥人,我就舉起另一標牌:『一切歸咎於倫納德』。」
勞德是個演技高手——他所說的話中,就象雜耍老手一樣顯得遊刃有餘,這讓我想起了鮑伯•霍普(Bob Hope)以及其他表演高手,多年來他們已經習慣了觀衆欣賞他們露一手,似乎他們一直在臺上表演似的——但這個角色他已習以爲常。早期瞭解他的人老說他「靦腆」。談及他年輕時的樣子,他說:「過了50年,我才意識到自己年輕時是多麼帥。」
他湊到我跟前說:「你知道嗎?我當海軍時,腰圍是34英寸,現在也就是35、36英寸的樣子。」他說當兵的經歷讓他脫胎換骨:「讓我明白該如何當好頭。」
從海軍退役後,勞德立下了宏願:要把他母親創辦的公司發展成爲化妝品界的通用公司(General Motors)。「剛開始,在美國本土市場銷售化妝品不費吹灰之力,我們把產品賣給有抱負的女性。上世紀60年代,美國郊區每天都有新商場開張,它們就是我們的客戶。但我萌生了另一個想法:我要進軍國際市場。」
他選中了英國,大家都說他瘋了——都說「英國人沒錢,不會花這麼高價格買化妝品的」,但1953年,他曾在倫敦呆過,看到「絲毫沒有復興的跡象,一切死氣沉沉,」1957年他隨美國海軍再次來倫敦時,「我看到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所以我知道勸我的那些人都錯了。我心裏想,『腦子裏有好點子時,千萬不要因爲別人的勸而打退堂鼓』。」
1989年,他以同樣的銳意進取精神進軍前蘇聯市場——「有人對我說,『你怎麼能把化妝品賣給共黨呢?』再往後到了1993年,我進軍中國市場。公司上市是1995年,動因主要是考慮到家族因素」——他說有些家族成員需要更多流動性資金——但他話語之間,略帶一絲遺憾。他的個人生活如今很安逸,但公司生意卻越來越難做。
「我做的最痛苦決定就是放棄權力,」他說。「我花了很長時間才適應。2000年,我從CEO位子上退下來,請弗雷德•連翰墨(Fred Langhammer)執掌公司(目前的CEO是傅懿德(Fabrizio Freda))。有時我倆商討(或爭論)時,他會以儘可能委婉的口氣提醒我,『倫納德,您已不再是CEO。』在此情況下,我知道自己是對的,對方是錯的,但我還得按對方的意思辦。這樣的問題以前也發生在我母親身上,她爲了讓別人(也讓我)照她的意思辦,也頗費心思,但有時你得接受這樣的現狀:對方也許與你行事方式大不一樣,但那並不意味著對方做得糟糕。」
說到這兒,他又點了冰牛奶咖啡(cappuccino),我則點了薄荷茶。「我每天喝三杯咖啡,因爲我的老年癡呆症基金會主席曾看到一份芬蘭人的研究報告,說成年人每天喝三到四杯咖啡會有助於防止得老年癡呆症,」勞德說。「我們是否再來點餅乾?」他問我,隨後要了些。但端上來後,他卻壓根沒喫。
「這就是我思考的公司未來發展方向,」他轉而說。「美國國內的力量對比已經從大企業轉至消費者手中。名人的時代已漸行漸遠,對富人以及名人的敬畏感也正在消失。社會上層出不窮的是精明的購物者,以及足不出戶的觀念,界定得很寬泛。」他又要了一杯咖啡。「我的觀念要比其他人超前10至20年。但我現在對此只得保持緘默。」
他嘆了口氣。不管他做什麼,不管他多麼苦口婆心地說教,也不管他對自己的飲食如何挑剔,他也「不能保證30年後,公司還會是現在的樣子。30年後,我能保證的是公司會不同於現在。」
這時,他突然叫道還有其它約會,他得馬上走。我準備買單。他喫驚地看著我。「今天可喫了好多喔!」他說——雖然我早就給他同行的手下人打過招呼今天由我買單。我知道這是玩笑話,這一點他也心知肚明,所以即便他起身準備離開,我還在等他給我使眼色。
範妮莎•弗瑞德曼是《金融時報》時裝編輯。
邁克爾餐廳地址:紐約市西55大街24號
科布沙拉(Cobb salad):36美元
尼斯沙拉:36美元
兩份餅乾:3美元
薄荷茶:6.5美元
2份冰牛奶咖啡:19美元
瓶裝Panna礦泉水:9美元
總計(包括小費):144.22美元

每年春季時裝秀,即1月份舉行的男裝秀與3月份在米蘭舉行的女裝系列秀期間,多梅尼科•多爾切(Domenico Dolce)與斯特凡諾•加巴納(Stefano Gabbana)就不再外出喫午飯。
這個做法可不是由於義大利當前經濟緊縮計劃的現狀(或許你有疑問的話)——多爾切與加巴納事實上在米蘭有自己的餐館,名字就叫「Gold」。但在異常忙碌的時裝季中,兩位珠聯璧合的設計師把西西里寡婦的喪服變成了風靡一時的高階時裝並硬是說服斯嘉麗•約翰森(Scarlett Johansson)及凱莉•米洛(Kylie Minogue)等名人穿著用緊身衣與黑色飾帶打造的所謂潮服。他們9點鐘從街對面某大樓裏各自的公寓房(多爾切住六層,加巴納則住七層)上班後,就很少再走出辦公室。
換言之,你若想採訪他們,徑直去找他們就是了,並不如想像中那樣麻煩。當我邀他們共進午餐時,加巴納解釋道,「辦公室就好比是我們的牢籠,但卻是不錯的牢籠。」「是絕好的牢籠,」加巴納補充說。他說得並不拐彎抹角。
來到總服務檯(極其規範,高桌子後面坐著一位女士)後,我很快被人引到更爲私密的接待區域。這兒的搭配讓人大跌眼鏡:深色勃艮第天鵝絨靠背長椅、豹紋式的牆以及各種風格的大幅畫作。其中一幅油畫畫的是他們兩位與三隻拉布拉多犬(深褐色、金黃色以及黑色),還有義大利流行藝術畫家朱佩塞•維尼齊來諾(Giuseppe Veneziano)的畫作:古典風格的大幅聖母像,頭形則是麥當娜(Madonna Ciccone),還有在腳邊嬉戲的兩個男童天使(是多爾切與加巴納的頭形)。說實話,看後讓人覺得有點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即便丹特•費雷蒂(Dante Ferretti)多努力,也無法制作出比這更出色的電影場景。多爾切與加巴納他們這麼設計,他倆也是這麼生活的。
「範妮莎!」加巴納走進來,站在我左邊,棕褐色的臉上帶著笑容,身穿巧妙撕扯風格的杜嘉班納(Dolce & Gabbana)藍色牛仔褲,系在細條紋馬甲上的錶鏈上的各種怪異鑰匙噹啷直響。「範妮莎!」多爾切緊隨其後走進來:他的身材更短、頭髮謝頂,黑框眼鏡擱在頭頂,身穿灰色毛衣與牛仔褲。
多爾切(53歲)與加巴納(49歲)初識於1980年,當時他倆均爲米蘭某時裝工作室的員工,並於1982年成立杜嘉班納公司。創業伊始,他們的理想就是把世人對義大利甜蜜生活(Dolce Vita)的浪漫懷舊情調——索菲亞•羅蘭(Sophia Loren)、意大利麪食以及西西里島——融入設計中,並以滿腔熱情(而無譏諷之意)把它詮釋成現代審美風格的服飾(2009年的一則廣告片拍的是麥當娜在廚房裏烹製意大利麪條)。服裝製作可能複雜多變,但其魅力直截了當。與其它義大利品牌一樣,這些服裝至少從表面上看直涉性愛風格。但正如過去古姿是開了享樂主義性愛風格之先河,範思哲引領了大膽性愛之風格,而杜嘉班納則是圍繞歡快性愛之主題:「哇塞,看看我的乳溝,簡直難以置信」之類的性愛風格。
這兩位設計師在事業上搭檔已經有30年了,保持私密關係長達23年,但2005年兩人關係破裂。他們知道世人挖空心思想搞明白兩人之間的關係,有人說其中一位是男裝裁剪師,另一位則是女裝裁剪師;有人說一位是構思者,另一位是經銷商。多爾切說:「本人每週有三個早上去練普拉提(Pilates),前不久我在普拉提更衣室時,一位教練走進來(這的確讓人不爽,因爲我更衣時不願與教練交談),他問我,『你們倆到底是怎麼合作的:你是裁剪師,而對方要重要得多?抑或(這我知道)你是貝爾泰利(Patrizio Bertelli),而對方是繆西婭•普拉達(Miuccia Prada)?
「貝爾泰利與普拉達?哈哈!」加巴納輕蔑地說道。教練說的是另一家義大利知名奢侈品公司普拉達有關設計與經營的分工,妻子繆西婭•普拉達是設計師,而其丈夫、公司主席特里齊奧•貝爾泰利則負責具體經營。
相反,正如多爾切所解釋的:「我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然,他倆在一起生活到了如此地步,成了一對不分彼此的搭檔,可以和勞萊與哈代(Laurel and Hardy)、霍普與克勞斯比(Hope and Crosby)以及《天生冤家》中的奧斯卡與菲力克斯(Oscar and Felix from The Odd Couple)相媲美;多爾切更喜歡安靜、更務實;而加巴納則很健談。加巴納說多爾切是「西西里人——來到北方後看到了『新事物』,總是向前看」;而他自己則是米蘭人,「所以嘛,本人鍾情傳統的東西,很難捨棄過去。」加巴納說話時不僅是手動,而且胳膊動,甚至不時地肩膀兒一塊動。多爾切若是要用啥小道具來闡述或者強調自己的話,那就是他的眼鏡了。
看著他們一唱一和,活像看一場演出,但自己再抱怨似乎顯得不禮貌。對於熟悉他們所設計的服飾的人來說,看到這場景後,感覺似曾相識。雖說他們設計的系列服裝都是可捋式緊身衣與水晶飾件,但杜嘉班納的業務實際上靠的是成衣、白襯衣以及女衫褲套裝。雖說利潤可觀,但材質看上去並不特別。所以,與其說是時裝秀,不如說是這兩個男人的秀。
我們漫步走向餐廳(位於寬敞的大廳對面,一頭掛著一盞巨大的威尼斯樹形燈)時,還繼續著先前的話題。我提及自己剛從巴黎時裝秀過來,對它感到很失望。
「如今大家都認爲時尚就是手提包,」多爾切哀傷地說道。
「但光改手提包的款式是無法改變整個時尚風格的,」加巴納說。「只有改變服飾的風格,方能改變整個時尚的風格。」
多爾切說:「在歷史上,古埃及的克婁巴特拉女王(Cleopatra)改了手提包的款式了嗎?」
加巴納說:「應該是服飾要與時俱進。過上10年,誰還會記得手提包的風格?只會記得服裝的風格。」
多爾切說:「整個時裝體系扼殺了時裝本身。」
我們步入另一個房間時,健談的加巴納停了一會兒,房間裏同樣掛著巨型樹形燈(只是這盞鍍了金),牆上貼著同樣狂野風格的虎紋壁紙。加巴納的狗也該喫午飯了。他閃進另一個房間,回來時拿了三隻狗碗(放在牆角)。加巴納喜歡拉布拉多狗。自從義大利時尚主編與部落格大名人安娜•戴洛•羅素(Anna Dello Russo)把一隻拉布拉多犬作爲聖誕禮物送給他後,他養了這些狗已有17年了。「它們是最棒的狗,」他說。「對人極其友善。」
這時,一位服務員過來遞給加巴納一張紙,他看了一下後,神情誇張地遞給我。「這是你的菜單,」他說道。不巧的是,菜單是用義大利文寫的,本人只能胡亂猜,所以他詳細給我解釋:「我正戒酒,所以我喫啥,你也只能喫啥。有次我在紐約時,麥當娜給了我這個戒酒療法,如今我每年戒酒兩次,每次十天,只喫蔬菜與蛋白質。」
「我沒有戒酒,」多爾切說。「我喜歡做飯,我會燒西西里菜:上週末,我爲15位客人做了一頓肉醬麵與燒烤。我做飯洗碗一肩挑,做好後,整個廚房乾乾淨淨。」
穿白色外套的服務員給我們端上來一大碗湯,是加了海帶與小麥片(bulgar)的胡蘿蔔湯。由於本人是客人,所以服務員先給我端。我提到了此事,因爲擔心事後會成爲是非之事。「我們理應如此,」多爾切說。
「嘿嘿,」加巴納笑道。
「想喫乳酪嗎?」多爾切問道,把放在銀碗裏切好的奶製品遞給我。加巴納則看了他一眼。
這是他倆在現在的公司總部喫的最後幾餐了,他們馬上就要搬到緊臨Metropol老劇院的新大樓裏,他們幾年前買下了這幢傳統風格、四周全是玻璃幕牆的大樓,並把它改造得適於舉辦時裝展。全部裝修歷時三年,只是在義大利金融危機爆發伊始停了一陣子工。他倆說總體上同意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政府目前爲解決本國財政困難所採取的措施,儘管他倆目前正就逃稅指控接受法庭審訊(「我們清楚自己沒做啥不當之事,」加巴納說。「但這種事就是耗時」),並受到了一項新生效法律的影響,即任何公司不可接受超過1000歐元的現金。「結果我們在銷售上損失慘重,」加巴納說。「顧客到店裏來購物,想用現金支付,我們告訴對方,『不行,只能用信用卡,』結果對方沒購物就走了。」
「然而,制訂這項法律是對的,」多爾切說。「想想所有的美甲師,他們收受現金,並不付相應的稅。你看,有一位美甲師我行我素,沒啥關係,但所有的人都這麼做……」
「這是創業以來我們行事方式改變最大的一次,」加巴納說。「我們也懂得啥事都得適時。」
「以前,我們做啥事都追求立竿見影:希望快快快,」多爾切附和道,並又喝了一些湯。「我們過去像部機器,唉,如今我們還像機器,但現在我這部機器有耐心等待。」
多爾切自己設計了這幢新大樓(建築是他的老本行),但加巴納還沒有進去看過。「他不讓我進去瞧,」他說,並朝多爾切擺擺手。屆時他們會和現在一樣,共用一間辦公室。
「大約三、四年前,我就想,『整天見到你,我都審美疲勞了!』」加巴納說。「我指的就是類似這樣的對話:他說,『本人喜歡黃色。』但我卻喜歡藍色。然後他又說,『這件襯衣讓我膩煩,』當然緊接著我得說,『是我錯了嗎?』然後他又說——」
「不,這不是你的錯,」多爾切笑著說。
「所以我說過希望自己的辦公室與他分開,但最終的結果還是倆人共用一間大辦公室。」
這時服務員端來了清蒸魚、海帶、甘藍與茴香。我喫了一點——通常情況下我午飯只喫一道菜,但本人學會了若是在別人家做客,就得客隨主便,況且這兒是義大利,喫可是馬虎不得的大事——但當服務員轉到他們跟前時,他們卻擺擺手表示不需要。
「我湯喝多了,」多爾切說。
「我也是,」加巴納說。「湯喝得我撐肚子。」我看了看自己盤子裏的菜,自我感覺有點傻傻的。就我還在喫個不停,這在時尚界顯得相當怪異。然而,這意味著他倆可以繼續對答,同時無需擔心喫的東西從嘴巴里掉出來,或許是他們別有用心。不管屬於哪一種情況,他們始終很主動地掌控著整個場面。
「最糟糕的時候就是我倆關係破裂、卻還在一起工作那陣子,」加巴納說。「我們考慮過散夥,但做不到。事實情況是一切完全照舊。但是,No Sex.」
「對,No Sex。」多爾切附和道。
「沒有他我無法工作,」加巴納說。「也許將來有朝一日會有多爾切服裝系列與加巴納服裝系列——」
「不可能,永遠不可能,」多爾切說。「這就是我的宿命。」
「永遠不要說不可能,」加巴納責備道。
談及首次公開招股發行之事時,倆人也是這麼說的。時裝界慣常的思維是:爲了具備全球競爭力,義大利家族經營企業不是轉投大集團懷抱(寶格麗(Bulgari)剛被路易維登集團(LVMH)併購)、公開上市(如菲拉格慕(Ferragamo))、就是引入私人股權投資(如蒙口(Moncler))。外界都覺得杜嘉班納(2011年的年收入爲11億歐元)無論採取何種方式,都是搶手的香餑餑。「當被問及是否打算上市時,我們就想,『爲啥要上市呢?』」加巴納說。「差不多有六個月,各大銀行不厭其煩爭相找我們談。」
「但我們不需要錢,」多爾切說。「將來我們若想擴張,可能會改變主意,但目前我們不想上市。我們的確需要稍微擴張,我們有很多計劃。」
雖說他們在去年九月停止銷售了更容易買到的杜嘉班納新款服裝系列,但告訴我此舉並非出於經濟原因,而是爲了防止與自己的主打系列造成混亂。除了在聖保羅與紐約開設門店外,未來兩年,他們打算在中國開設30家門店。他們還把自己打造成了小型出版公司,與Rizzoli以及Taschen等出版公司聯袂出版咖啡茶几上擺設用的圖書。他們的夢想是成爲「香奈兒那樣的龐大集團,但也許我們等不到實現這個夢想的那一天了,」加巴納說。
「屆時卡爾•拉格菲爾德(Karl Lagerfeld)加盟進來,給我們設計服裝!」多爾切說。
服務員又來了,這次端來(帶玻璃穹頂蓋子)的盤子裏堆著滿滿的西西里小甜點。「哇!」多爾西喃喃道。「我愛喫蛋糕。」
「甜食好比毒品,我若是咬上一口,就想把它全喫完,」加巴納說。「我一次能喫完一整塊義大利水果蛋糕。」
然而,他倆誰也沒動甜點。喝完咖啡後,他倆登著彎曲的寬樓梯徑直去自己的工作室了,我則有專人送到戶外,外面陽光明媚。我心裏還在唸叨玻璃穹頂蓋下的那些甜點。然而事實情況卻是:無論多爾切與加巴納如何裝苦相以及唉聲嘆氣,表明自己多麼喜歡喫甜點,無論他倆聲稱自己如何嘴饞,卻還是完全能自控。畢竟,誰都不會喫掉自己的道具,對吧?
範妮莎•弗瑞德曼是英國《金融時報》時尚版主編
譯者:常和
杜嘉班納公司總部
米蘭市Via San Damiano7號,郵編:20122
胡蘿蔔與小麥片湯
清蒸比目魚、炒茴香
甘藍與海帶
西西里糕點及混合漿果
瓶裝水
咖啡
均爲免費

每年八月,紐約就成了一座空城,城裏的上流人士不是趕赴漢普頓斯(Hamptons)的私人海灘、就是到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起伏無垠的原野度假。可謂只見其名在門上,難見其人在家中————當然時尚界人士除外,因爲每年9月6日開幕的紐約時裝週(New York Fashion Week)就在眼前了。
「哦,我每年8月回紐約,」設計師卡羅琳娜•海萊拉(Carolina Herrera)笑著說。她旗下公司年銷售額已達十幾億美元,她專爲那些東奔西走的達官貴人設計服裝,其中就包括新任駐日大使卡羅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肯尼迪又是瑪莎文雅島(Martha's Vineyard)的夏日度假常客。「這就是幹這一行的代價,但我真的喜歡這行,想去哪裏就去哪裏,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
我倆在聖安布魯斯餐廳(Sant Ambroeus)見面時,當然並無條條框框的限制。聖安布魯斯是家意式餐館,位於紐約曼哈頓西村(West Village)的名流居住區。此處綠樹成蔭,遍佈紅磚砌就的褐沙石豪華房屋以及盛開著白花的梨樹。事實上,如今這兒幾乎空無一人,以至於我不禁納悶爲何選在這裏見面。整天與名流打交道的設計師卡羅琳娜•海萊拉,自己的辦公室位於紐約時裝區的黃金地段,卻捨近求遠到市中心來赴約,這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難道是想增加影響力?知名設計師似乎總想增加影響力。或是實地打探開設新店的理想地段?抑或她與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一樣,喜歡清靜獨處?(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1979年曾完全參照庇隆夫人(Evita)的模樣,給海萊拉創作了一幅絲網印刷作品,自此以後,她盡人皆知。)
「我女兒帕特里夏(Patricia)就住在附近,」當我問海萊拉爲何選此處見面時,她這樣說。「我倆常來這兒,我希望你也能喜歡,我覺得這兒有家的溫馨感。」
海萊拉夫人成立自己的時尚帝國,憑藉的就是這樣的理念:希望與人分享其光鮮亮麗的生活方式————生活闊綽、富有教養、國際視野、謹慎持重,而她就是這一切的化身。卡羅琳娜•海萊拉更爲人所知的稱謂是海萊拉夫人,這既是出於對其實際年齡的尊重(她已73歲),也是因爲她身上特有的那種老派優雅舉止的需要。
她赴約時,上身穿著抽象風格的米色及黑色大麗花圖樣點綴的綠色短上衣(選自自己設計的秋冬季服裝系列),再配以得體的圍巾、黑色短裙以及雙耳大珠母墜掛件,顯得再合適不過了;金色短髮往後梳理,顯得氣度不凡。事實上,她的時尚形象總是那麼完美無缺(這就是爲何她多次榮獲國際最佳著裝獎(International Best Dressed List)的原因)。1980年成功榮登名人堂,並於2011年被《名利場》雜誌(Vanity Fair)評爲有史以來最會著裝的女性。她本人又是自己時裝的最佳模特兒,明快風格的白色襯衣配塔夫綢料蓬蓬裙已成時尚經典,讓好幾代人對定製襯裙連衣裙以及套裙念念不忘,讓心儀者欲罷不能。這種始終如一精心打造出的形象光彩照人,在我這時尚主編面前,都顯得咄咄逼人,其他女性的強烈共鳴也就不難理解了,她們大多都說「我希望裝扮成她的模樣。」她則因此而掙得盆滿鉢滿。
. . .
實際上,她本人並不願意這樣形容自己。海萊拉喜歡這樣答覆我這樣的詢問者:「我只是製作服裝,感興趣的只是美的東西以及讓女性更靚麗。」 這樣的回答似乎顯得滴水不漏,尤其是透過說自己「只是製作服裝」。 出生於加拉加斯的海萊拉也已成爲一系列現代時尚元素的象徵。她不僅展示了女性創業能力(她創業時已41歲,在謝里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看來,海萊拉在服裝界出類拔萃之前,在這一行早已「成績斐然」),展現了拉美新興時尚市場與日俱增的影響力,而且標誌着專爲名流設計服裝的社交型設計師的崛起。但冷靜斟酌後,發現她的這個回答也是個性十足。換個說法也能說明她的性格:儘管她曾多次獲邀擔任電視真人秀節目《天橋驕子》(Project Runway)的評委,但一直拒絕參加。
「那些改編自真實故事的電視節目,」她說,並朝爲我倒蘇打水的服務員微微搖搖頭,然後又低聲說道,「給我倒靜水」——「諸如《暴徒狂妻》(Mob wives),內容全是講自己:誰希望這麼個活法?瞧瞧大家一天到晚關注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以及其體重這類花邊新聞。我敢肯定這是她有意爲之,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被健康減肥諮詢機構慧儷輕體(Weight Watchers)相中。」她翻了翻白眼,然後問道:「您說啥話題最無聊?」還沒等我開口,她就脫口而出,「我對你說:那就是聊自己!」
採訪的開場白就如此調侃自己,似乎有些犯忌。但海萊拉受過良好教育,因爲她這樣回答道,「人的一生就是成家立業、生兒育女,接受良好教育以及謹言慎行」。抑或她後來的說法, 「我被認爲是品牌代言人,但我覺得自己是凡人一個。」點完菜(她要了意大利麪,本人則點了三文魚塔塔、北韓薊沙拉)後,我決定轉向政治話題————今年四月以微弱優勢當選委內瑞拉總統的馬杜洛(Nicolas Maduro),我覺得這個話題似乎不偏不倚,於是問她投票了沒有?
「我當然投票了,」海萊拉說。「我每次都參加。但我就在紐約投票。我投票支援恩裏克•卡普里萊斯(Henrique Capriles)。委內瑞拉需要變革。若一切順利,我會說選誰都沒問題,但如今經濟出現了大問題,反對黨候選人卡普里萊斯年輕有爲、理念又新,不選他選誰?」她經常回加拉加斯,最近一次回國是11月參加自己孫子的婚禮。但她也說:「我設法不談論政治,因爲我女兒和外孫女目前仍生活在委內瑞拉。委內瑞拉是個美麗的國家,但時刻有危險,我不希望出啥不測。」這讓我引出的政治話題「半路夭折」。
生活在加拉加斯的是她的大女兒梅塞德斯(Mercedes)。海萊拉和她現任丈夫、《名利場》雜誌專稿編輯雷納爾多•海萊拉(Reinaldo Herrera)育有兩女,帕特里夏和小卡羅琳娜。另外兩個女兒——梅塞德斯與安娜•路易莎(Ana Louisa)是自己與首任丈夫、地主吉列爾莫(Guillermo Behrens-Tello)所生(他倆結婚時,海萊拉年僅18歲,她24歲離異)。小卡羅琳娜目前供職於海萊拉名下的香水公司,而帕特里夏則專司成衣業。「女承母業益處多多,」海萊拉說。「有啥問題,她們隨時就會告訴我,」勿庸置疑,她的兩個女兒對品牌推廣居功至偉,使她設計出的服裝更符合年輕人的審美情趣。
孩提時代,海萊拉全家就常去歐美遊歷。她有貴族血統,父親是空軍軍官,曾一度擔任過加拉加斯地區的總督。她與雷納爾多的交際圈遍佈全球。 有一天,她與閨蜜、時任美國《Vogue》雜誌主編的黛安娜•弗裏蘭(Diana Vreeland)交談時,提到自己正考慮成立紡織品牌。弗裏蘭卻說「這個想法毫無新意,要是我的話,就進軍時裝界。」海萊拉對此仍記憶猶新。當時,她的全部服裝專業知識僅限於自己離異後,在加拉加斯的璞琪(Emilio Pucci)專賣店打工六個月。但閨蜜的忠言深深地打動了她,不久之後,她在某雞尾酒會上遇見拉美最大的雜誌出版公司老闆德阿馬斯(Armando de Armas),對方願意出資充當其合夥人。
1981年,她在紐約成立了同名時裝公司,從此以後公司總部始終留駐紐約。海萊拉說她自認爲仍是委內瑞拉人,但卻自視是美國設計師。「紐約是世界之都,」她說。「若在這裏能創業成功,在天下就暢通無阻了。」
我對她說,哎,這不就是辛納屈(Frank Sinatra)的歌詞嗎?此時我們點的菜端了上來。但紐約實際上並非舉足輕重的時尚重鎮。我問她:難道您沒有想過若在歐洲創業,不是更聲名顯赫嗎?「我不知道爲何有這種說法,」海萊拉回答道,「這種說法荒謬至極,我的意思是,所有歐洲設計師都希望開拓美國市場。所以爲何要捨近求遠呢?我實在無法接受這種想法。」她的首次個人時裝秀就在紐約的大都會俱樂部(Metropolitan Club)舉辦。
「我覺得當時的想法是推出一個系列後,一切順其自然就行了,」她說,並用手指著自己的意大利麪。「然後消費者購買,我們再接再厲。」她們於1986年推出了低價CH系列香水;1987年,西班牙香水及時裝家族企業蓓格(Puig)推出了她設計的香水。1995年,蓓格出資購入德阿馬斯名下擁有的公司股權,成爲海萊拉公司合夥人。「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她說。如今全球共有95家卡羅琳娜•海萊拉全資門店以及400個時裝銷售點。她專爲傑奎琳•奧納西斯(Jacqueline Onassis)以及小布什夫人勞拉(Laura Bush)設計服裝,也爲影片暮光之城四:破曉(上)(Breaking Dawn – Part 1, Twilight)設計了婚紗。
隨著巴西與墨西哥成爲日趨重要的奢侈品銷售市場以及自己在西班牙語世界聲名日隆,海萊拉對公司的飛速發展前景充滿了信心。去年,她在保加利亞、印尼、巴拿馬、巴拉圭以及烏茲別克等10個國家新開設了門店。今年五月,她作爲特邀明星嘉賓參加了新加坡時裝週(Singapore Fashion Week),以慶祝自己在該國開設的首家門店。
儘管她是時裝界首波交際型設計師的一分子——她們的培訓與資質主要在於穿個性時裝的能力以及對市場瞭如指掌(諸如此類的設計師還有德里貝斯(Jacqueline de Ribes)和瑪麗•麥克法頓(Mary McFadden))————但她是事業至今仍蓬勃發展的碩果僅存者,目前仍沒退休打算。
「我不會把海萊拉門店徹底改頭換面,從而讓自己品牌的擁躉者一頭霧水。」她說。「我秉承迷人魅力以及始終如一的理念。」儘管如此,她也理解進軍時裝界隨之而來的種種質疑,而這往往會付出相應代價。她說當初剛推出自己的品牌時,她對設計師朋友候司頓(Halston,已故)和盤托出自己的計劃時,對方說,「您難道瘋了嗎?」她對那些進軍時裝界、卻鬧得滿城風雨的非科班設計師(托里•伯奇(Tory Burch)、貝嫂維多利亞(Victoria Beckham)以及奧爾森姐妹(the Olsen twins))感同身受,她清楚這些人所面臨的種種艱難險阻。
. . .
「問題是如今人人都成了設計師,」她說。「成功的歌星與網球明星都搖身變成了設計師!人人都對時裝說得頭頭是道,都能品頭論足一番。甚至我的司機對此都略知一二。但真要獲得成功,必須要有獨到眼光,這至關重要————比院校的科班教育要重要得多。設計師對比例、紋理以及色彩要有獨到眼光。這就是爲何有人對維多利亞說三道四、說肯定另有高人爲她的設計捉刀之類的話時,我就氣不打一處來。不親歷爲之,就不能妄下定論。維多利亞有她自己的眼光,她言之有據,源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儘管她不可能操刀所有時裝草圖、親自裁剪所有面料,但從確定每個時裝季的主題到如何詮釋,她都深度參與其中。然而,她從不僞稱一切都是自己親歷親爲。」
沒錯,她告誡年輕一代的同行:「不要包辦一切,打點生意要另請高人。」我問她是否讀過謝里爾•桑德伯格的著作。她說自己沒讀過,但她說對此很感興趣。我問她是否覺得女效能擁有一切時,她答覆說「可以————但不能同時擁有。」
儘管如此,我說她同時把家庭和事業兼顧得井井有條。海萊拉則說,自己創業伊始,女兒上的是全日制學校,而當時時裝界本身發展還很緩慢,也容易操控。「如今還能兩頭兼顧嗎?」我問道。「我真不知道,也許做不到。」她說丈夫全力支援自己,但並非像新派男人那樣。當問她丈夫是否幫忙做家務時,她不禁笑了。
「哦,他不做,」她說,但隨後補充說自己也不願意他這樣:「我覺得女人做家務其樂無窮,女人天生就喜歡操持家務。」海萊拉老公的最大貢獻並非在精神上大力支援她,而是「把女兒帶走、他們仨一起度春假,可以讓我全身心工作!」她說。紐約的春假往往與秋冬季時裝週在時間上重合。
我問她做好這一切的訣竅是什麼,她回答道:「出色的員工。」與其說她感興趣的是當一位女權運動代言人,倒不如說她更是願意爲自己母國委內瑞拉大聲疾呼的政治活躍分子。但這並非說她不看重自己時尚代言人的角色。這時附近一位用餐者走過來問:「不好意思,您是設計師嗎?」海萊拉握著對方的手笑著說「是」。
「這種情況常發生嗎?」她的粉絲離開後,服務員過來清理餐桌,我問她。海萊拉承認這是常有的事。「我心情愉悅,」她說。「爲啥不呢?這表明我們做得好。」我倆都有意迴避甜食,轉而點了咖啡,咖啡端上來時,店方免費贈送了一小盤甜點。
也許她喜歡自己的擁躉,但很不喜歡時裝秀後臺那一套做法————記者搭訕時,要求他們就設計精髓發表高論;而他們獻飛吻時,各大時尚雜誌主編則恭維他們是「天才設計師」。「『您的設計靈感源自哪裏?』是普天下最糟糕透頂的問題,」海萊拉說。「那些恭維者,雷納爾多常對我這樣說:『他們還能說啥————我很不喜歡你的設計?』他們不得不恭維一番。但那意味著你不要相信這一套。」
該買單了,但服務員笑著說,「今天算免單。」很顯然,他頗爲自豪————餐廳對知名時尚設計師很大方。但他們顯然不知道我們《金融時報》採訪付餐費的規矩,我對此作了解釋。服務員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一名叫託德的經理走了過來,他與海萊拉握手,海萊拉則向他介紹了我。託德說傳訊部已說過這頓飯算餐廳請。我則回覆說:謝謝美意,但本人必須買單。
「她必須買單!她是報界從業人員,」海萊拉以責備的口氣說道。託德最終只得同意,隨後離開了我們。海萊拉笑著說:「問題在於:店方想免單!而通常買單時,食客一下子都去衛生間了。」她主要是想開個玩笑。但我倆都心知肚明:不管你有多謹言慎行,終有百密一疏的時候。
範妮莎•弗瑞德曼是《金融時報》時尚主編
-------------------------------------------
聖安布魯斯餐廳位於紐約西四大街259號
蘇打水:7.50美元
靜水:7.50美元
北韓薊沙拉:19美元
三文魚塔塔:19美元
Fusillone all』Arrabbiata:19美元
兩份瑪奇雅朵咖啡:4.5美元
卡布奇諾熱牛奶咖啡:5美元
總計(包括小費):104.73美元
譯者/常和

今年90歲高齡的凱萊•範德比爾特(Gloria Vanderbilt)這一生可謂跌宕起伏、絢麗多彩,在很多行當都是響噹噹的人物。她是藝術家、演員、家族繼承人、模特兒、社交名媛以及時尚設計師,共結過四次婚————先後嫁給電影經紀人兼製片人帕特•迪西科(Pat DiCicco)、交響樂指揮大師史託考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電影名導西德尼•呂美特(Sidney Lumet)以及著名作家懷亞特•庫珀(Wyatt Cooper),也曾與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以及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等名人傳出過緋聞。
似乎爲了與名聲形成鮮明反差,她每天的午餐千篇一律:只喫塗抹花生醬的果凍三明治,時不時會喫個蘋果。然而爲了我這次採訪,她同意打破生活常規,繞過街道拐角,從自己的工作室來到Ze Café餐廳。但算是某種補償,她首先要我先蒞臨其工作室,工作室爲曼哈頓中城(Midtown Manhattan)最東頭某地下公寓的一間白色小房間,就在她居住的公寓樓下。
我倆如此「交易」還算公道,她的公寓房是個套間,已有90年房齡,她生活的細枝末節,歷歷在目,房間裏東西塞得滿滿當當。
凱萊出生於1924年2月,是美國鐵路大王繼承人雷根納德•範德比爾特(Reginald Claypoole Vanderbilt)與第二任妻子歌莉亞•摩根的唯一孩子。1925年,父親雷根納德因酗酒撒手人寰,經過激烈的法律訴訟,年輕的寡母並未奪得女兒的監護權,小凱萊改由姑姑、紐約惠特尼藝術博物館(Whitney art museum)的創辦人格特魯德•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監管。
在隨後的歲月中,凱萊成爲諸多形象的化身,而每個人的詮釋各不相同:在我看來,她永遠是上世紀70年代那個首創高檔牛仔布料製作緊身牛仔褲(帶著獨特簽名與白天鵝標識)的設計師;而在作家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看來,她是名符其實的「天鵝」,凱萊早年作爲交際名媛時,曾與卡波特相識。她的各種形象版本均在自己寓所內有所體現(均有實物存證)。
「噢,很高興見到您,」她對我說,古銅色的頭髮梳理得溫婉優雅,經過化妝品打理的肌膚沒丁點皺紋,招牌式的爽朗笑容又讓肌膚緊繃感十足,正是這爽朗笑容,讓她一次次克服人生不幸,不斷實現燦爛輝煌。1978年,她的「至愛」、第四任丈夫、著名作家懷亞特•庫柏不幸死於手術檯,時年50歲;10年後,她與庫柏的大兒子卡特自殺身亡,時年只有23歲。然而,她的燦爛笑容流露出這樣的信念:只要永往直前,明天會更美好。
. . .
今天的凱萊下穿黑色寬鬆褲子,上穿拉鍊式羊絨運動衫,沒看見佩戴啥首飾。椅子上搭著一件藍色工作服,這是她工作時的行頭(她一直在準備自己的紐約個展,許多展牆需要策劃)。她不再創作拼貼畫,1969年,正是在紐約哈默畫廊(Hammer Gallery)舉辦自己的拼貼畫展後,才使其一舉成名。脫口秀主持人約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對此愛不釋手,於是把這些拼貼畫在自己主持的「今夜秀」節目中(The Tonight Show)展示出來,此舉開啓了凱萊紡織料設計師的時尚生涯。
她也不再製作「魔盒」(dream boxes),這種Plexiglas樹脂料盒子擺滿了洋娃娃拼組件以及其它自然藝術品。在拼貼畫創作之後,她又轉向了「魔盒」製作。「我喜歡不斷嘗試新事物,」她這樣說道,給人的感覺象是某種掩飾。1952年,她開始舉辦自己的藝術展,迄今已舉辦了好幾十場(她的畫作總共賣得4.5萬美元)。最近她的興趣又轉向了蠟筆畫創作,工作室(曾是第四任丈夫庫柏的辦公室)裏滿是創作用的畫布,此外還有洋娃娃,書籍以及她父親的半身塑像(「母親說是她親手製作了雕塑,但我依然存疑。」)
凱萊邊向四周比劃邊說道:「這些就是我2013年以來的作品。」畫架上正在創作一幅兩個軀體融爲一體的巨型畫;小幅的素描畫則堆了足足三英尺高,其中一幅畫上還寫著這樣的話,「我把便條放進罐子,而後扔進大海,這就是我找尋真愛的方式」;牆上則掛著一幅捲髮女士的全身肖像畫,旁邊的題款是「坐在海邊的JCO」。JCO就是美國女作家喬伊斯•卡洛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她恰好又是凱萊的閨蜜與創作模特兒。
「歐茨的美麗讓我神昏顛倒。她身材瘦削、秀髮驚豔、雙眼迷人,猶如天使下凡。她的肖像畫我畫了好幾百幅,但依然未畫出其神韻,」她對我說。
她的另一創作模特兒是法國著名演員與卡巴萊歌舞表演藝術家奧萊利婭•提瑞(Aurélia Thierrée),提瑞是「奧娜•卓別林(Oona Chaplin)的親孫女」。奧娜•卓別林與凱萊年輕時都是社交名媛,關係密切。(與凱萊交談,有點感覺象是與真實版的變色龍(Zelig)交流:每次一談及某位名人,哇塞,她總是滔滔不絕。)我問她畫畫時是否遭遇過所謂的創作瓶頸。「沒有,」她聳聳肩回答道。「我一創作,就不會停下來。我一次不會畫很多幅畫,每次只創作一幅,但是我畫的速度很快。」
多數畫一般花2-3天就能完成。她實在難以爲繼的那一次(儘管這種情況不多見)是畫小兒子安德森的肖像畫,安德森是CNN新聞主持人。那幅畫她已創作了很長時間:畫的只是兒子的素描畫,並用紅筆列出了1993年以來他到過的所有熱點地區————柬埔寨、盧安達等等。「看來我得重頭開始了,」她說。
「我好多年前畫過一幅安德森的肖像畫,當時他還是紐約道爾頓私立學校(Dalton)的學生,」她說,「我讓他把畫帶到學校去給同學看,結果他說自己顏面盡失。但如今我覺得他會很喜歡這幅畫。」
凱萊把我領進客衛,在每塊瓷磚上,分別畫着她的設計圖樣、閨蜜名字以及對自己有特殊意義的日期。緊接著又給我看了在另一個房間自己設計與安裝的壁爐。壁爐呈拱形狀,加入亮銀粉後把它刷成了綠松色,其藝術水準有點不敢恭維,但又萌態十足。「一有時間的話,我就會每半年把它重拾掇一番,」她對我說。
我問她:您是否總想藝術創作?「沒錯,從我孩提時代就有此夢想,但小時候沒法與人探討藝術,上了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的惠勒私立走讀學校(Wheeler school)後,我才夢想成真,因爲我在那兒碰見了一位出色的藝術老師。」
我問她爲此是否擔心過被人瞧不起,或是憂慮自身的名人身份會讓自己作品黯然失色。
「實話對你說,我還真去紐約藝術學生聯盟學校(Art Students League)學習過,」凱萊說,「但我認爲從雷內•布歇(René Bouché)與馬賽爾•韋爾特斯(Marcel Vertès)等大藝術家的造型藝術中受益匪淺,而且幸運的是我四任丈夫都非常支援我的事業————託考夫斯基支援我畫畫,呂美特支援我的演職生涯,庫柏則全天候地支援我。孩子,你會問我思念庫柏嗎?我無時不刻都在想,『親愛的,你爲何撒手人寰?否則你就能親眼目睹這一切,我也可以一一呈現給你看。』
「但安德森眼光異常獨到,他只要在,就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觀衆。他本可以成爲出色的藝術家,但他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此時建議一起步行至Ze Café餐廳喫午飯,似乎是最合適的時機了。凱萊挽著我的胳膊,我倆慢慢沿著街道拐角走到Ze Café餐廳,餐廳裏基本沒啥客人。服務員拿來菜單後,凱萊說:「你想點些啥,直接告訴我。我每次點菜,到頭來往往都是主隨客便,因爲這樣看起來更爲得體。」
我倆點了蘇打水以及當天店家特別推薦的湯————滴著香醋的蘿蔔湯。「我不喜歡太過骨感,」她對我說。「我努力想多喫點。」她晚餐通常喫義大利天使面————「再加些甘藍、一聽青豌豆、碎培根肉與胡蘿蔔絲、紅辣椒以及橄欖油,」對於甜食,她可能會選「清涼維普(Cool Whip,是人造生奶油)。它是冒牌貨,糟糕透頂,但它難以複製。」
她這輩子只有兩個時間段沒搞藝術創作:上世紀50年代(共當了七年演員,在莫爾納爾(Ferenc Molnár)執導的《天鵝》(The Swan)以及威廉•薩洛揚的《鼎盛年華》(William Saroyan』s The Time of Your Life)等作品中飾演角色)以及做時裝的時候。她說:「我當演員原因很複雜,並非勉爲其難,但我的願望一直是畫畫。做演員是截然不同的生活,需要依賴許多人的支援,而且不管自己演得多棒,感覺永無止境,所以我真得不適合做演員。」
我對她說:您似乎是社交名媛「下海」做設計師的第一人————是卡羅琳娜•海萊拉(Carolina Herrera)、托里•伯奇(Tory Burch)以及維多利亞•貝克漢姆(Victoria Beckham)等人的領路人。「本人從不自視爲時裝設計師,」她說。但也說自己從不懷疑識別好時裝的能力。「這完全關乎個人品味,有如何實現最佳搭配的第六感。我覺得這與教育程度毫無關係。」此外,她由於一直是《Vogue》的常客,所以感覺自己就屬於時尚圈。
不管怎麼說,她入設計行純屬偶然。在自己的拼貼畫基礎上,凱萊製作了織物面料(這就發生在她的作品亮相《今日秀》節目後),進而把它們做成圍巾及其它飾物。後來,梅真尼公司(Murjani)萌生了想法。梅真尼是位於紐約第七大道的一家制造企業,掌舵者是行銷天才沃倫•赫希(Warren Hirsch)。「梅真尼公司的倉庫裏放了很多牛仔布料,」凱萊說,「所以對方說:『爲啥不把自己名字印到牛仔褲上?』正是這讓本人大賺了一把。」她的同名牛仔褲於1977年12月面世,共售出了好幾百萬條。凱萊靠在電視上打廣告以及個人公開露面銷售自己的牛仔褲。1980年是銷售的巔峯時期,自己一下子就掙了1000萬美元。「靠自己能力掙的錢纔是唯一實實在在的錢,」她這樣說道。
但沒過多久,凱萊就發覺一直被自己的心理醫生克里斯•佐伊斯(Christ Zois)與律師兼朋友托馬斯•安德魯(Thomas Andrews,自己的全權委託人)矇騙。這兩人一直在中飽私囊銷售款,而且把她的商標名悄悄賣給佛羅里達的一家公司,並發現自己欠下了好幾百萬美元退繳稅(back tax)。她只得賣掉在英國南安普敦以及紐約的房產去還債,儘管她爲此起訴了那兩個巨騙,並且於1993年獲判150萬美元的賠償,但此時安德魯已經去世,多數賠償都無法追回。
「信任他們真是大錯特錯,」她說。「雖說糟糕程度還比不上自己17歲草率嫁人(那麼年輕嫁人真不應該),但還是危害巨大。另外,如果連自己的心理醫生都不能相信,那還能信任誰?」於是,她不再像牛仔褲簽名那樣署名自己的畫,也算是喫一塹,長一智。她不再草草在畫作上籤上自己的大名,而是在字母V上另外新增了非常形象化的字母G————但這看起來仍然是標識。
凱萊棄做時尚設計師後,就一直致力於藝術創作及出書。她迄今已寫了九本書(還不包括她的藝術與設計專著)。她的著作包括了前二次婚史(分別是1987年出版的《黑騎士》 (Black Knight)與《白騎士》(White Knight))、兒子卡特的往事回憶錄(出版於1997年的《一位母親的故事》(Mother』s Story))以及自己85歲時創作的情慾小說《欲罷不能》(Obsession, 2009)。儘管多數作品爲自傳體,但她說自己的本意絕非「澄清事實真相」。
點的湯端上來後,她繼續說道:「我覺得自己對『喪失』這個話題非常感興趣,並且想努力表達出來。我覺得父母雙亡者會感覺人生有所缺失,但他們又說不清、道不明,因爲自己從未真正擁有過。」
庫柏葬於紐約斯塔騰島(Staten Island)的摩拉維亞公墓(Moravian cemetery),這兒也是範德比爾德的先祖、鐵路大王範德比爾特的氣派陵墓所在地。「庫柏希望自己安息於此,因爲我和孩子們可以常去祭奠他。」她說。卡特的墓就緊挨著父親庫柏。凱萊最近剛與安德森一起去祭掃了墓園,而當時美國家庭電影頻道(HBO)正在拍攝一部反映整個範德比爾特家族的紀錄片。我問她生活再次被起底,自己是否感覺造化弄人?
「沒有!」她回答道。「我覺得此生已完全無憾。我從不拜讀關於自己的材料。孩提時代頻頻亮相是段痛苦經歷。我明白人生若要成就一番事業,自己頭腦就得保持清醒狀態,方法之一就是不去拜讀別人評論自己的材料。但這可能也是我唯一關注的東西。」
凱萊的作品往往用敘事性很強的標題:如「世界一片漆黑,人類將居於何處?」(Where Will We Live When the World Goes Dark)與「左撇子都是夢想家」(The Left Hand is the Dreamer,她最近在古董拍賣網站1stdibs上舉辦的紐約個展也是如此命名)。她醉心於在畫作與時裝印花的方寸之地中表達豐富內涵。
「我有一天與作家喬伊斯•歐茨共進午餐時,給對方講述自己寫過的一部名爲《夢想成真》(It Came True)的『短篇小說』,」她說。所謂『短篇小說』,就是用盡可能少的字講述一個簡短故事。
「當講到『男主人公說,寶貝,你會無比幸福』時,喬伊斯對我說,『何不取《真能夢想成真?》的標題?』
是啊,爲啥不這樣取呢?我一邊付賬,一邊問她。
「唉,那樣可能會讓整個故事更爲妙趣橫生,」凱萊坦承道。「但這樣一來就太過憤世嫉俗了。你知道,本人並非憤世嫉俗之輩。」
於是我追問:那您屬於哪種類型?「忠誠可靠!」她大聲說道,顯得興高采烈,所以很容易讓人覺得她一直在等待這種自吹自擂的機會。
我倆起身走回她的工作室,她則拐着我的胳膊肘。我問她:接下來你會做啥?「我會一直幹到凌晨三點身心疲憊爲止。」她對我說,然後走後樓梯回自己住的公寓,她喜歡在家裏看真人秀電視節目《茱迪法官》(Judge Judy)————當事人不在正規法庭、而是在節目中直抒胸中煩惱,她說「節目內容與自己的家庭背景並不相干。」儘管凱萊再三否認自己對別人的感想表現冷漠,但她並非沒意識到自己的實際形象。每晚10:30,她會準時入睡。第二天一早,她又會爬起來,開始一天的日常工作。
「這是唯一做好一切事情的方法,」她說,此時我倆已走到她家門口,於是她把手從我的胳膊肘抽出來,並與我握手告別。儘管午餐期間,我倆都感覺像是親密無間的朋友,但她這個舉動明白無誤地表明我倆該各奔東西了。
注:進行本次採訪時,範妮莎•弗瑞德曼還是《金融時報》時尚主編。
-------------------------------------------
Ze Café餐廳位於紐約第52東街398號(398 East 52nd St, New York),郵費:10022
2份當天店家推薦的蘿蔔湯:18美元
聖培露(San Pellegrino)蘇打水:7美元
總計(包括稅費及小費):33.22美元
譯者/常和

在我的職業生涯裏,我女兒從來沒有要求我向任何採訪過的人索取簽名。不管他們是總理、將軍還是商界領袖,全都受到了一視同仁的無視。但當我這個13歲的小孩聽到我將和佐拉(Zoella)會面時,她立刻陷入了一種欣喜若狂的狀態。「爸爸,你可千萬別忘記!」在我將去與這位24歲的時尚和美容博主共進午餐時,女兒堅決地發了這樣的簡訊給我。
在出發之前,她跟我講了她所知道的一切關於我午餐夥伴的資訊。她告訴我採訪的技巧,甚至對我可能問的問題提了建議————除了喜歡的音樂和食物。
正因如此,當我到達莫德羅會所(Modelo Lounge),一家有點荒涼的海邊咖啡館時,我覺得我已經做好了準備工作。我知道很多關於佐拉自身的事--她是一位在線大姐、心理諮詢阿姨、終極時尚專家以及吸引了數百萬狂熱、尚未變成憤青的年輕消費者的關鍵人物。不僅如此,我也對阿爾菲•德耶斯(Alfie Deyes)、PewDiePie、塔尼婭•伯爾(Tanya Burr)和YouTube影客(影片部落格)的「英國幫」(Brit crew)有著相當程度的瞭解。
如果你沒有在某年齡段的小孩子,這些名字對你來說可能毫無意義。但他們是青少年的小螢幕興奮劑,就像英國廣播公司(BBC)電視明星約翰•諾克斯(John Noakes)和湯姆•貝克(Tom Baker)在1970年代對童年時代的我來說一樣偉大。
沒錯,這些影片的內容與「藍色彼得」(Blue Peter)或「神祕博士」(Doctor Who)完全不同:作品談不上有什麼價值;主要題材是針對電玩、惡作劇和那些令所有青少年著迷的東西。但正是這些影片吸引了廣大的觀衆。成千上萬的兒童和年輕人每天聚精會神地觀看它們。
從這個羣體中脫穎而出最紅的明星也許就是佐拉她自己。她的影片主要是坐在牀上給出美容建議、做頭髮或者播放一個她的購物「戰利品」--她和她的朋友們炫耀她們剛買到的產品。
還有一個固定的播放時段稱爲「親密交談」(ChummyChatter),包含了佐拉和她的「閨蜜」路易絲交換關於友誼、身材形象、男孩和是否該上大學等關鍵問題方面的建議。你可以從一些最近播出的標題看到會受到父母們支援的常識。這些問題包括:「你爲何這麼瘦?」或者「邊界與說『不』」。
很難對行外人講清楚她對那些年齡從13歲到20歲年輕羣體的吸引力。但她的魅力是不可否認的。自從她在2009年推出她的YouTube影片後,佐拉的影片已經成功吸引了530萬的訂閱者--僅僅在1月就有230萬訂戶--透過一種全民擁護的神奇滲透力。
獎賞也如期而至的到來。去年,她榮登BBC1當代流行音樂電臺青少年獎(BBC Radio 1』s Teen Awards)的英國最佳影客(Best British Vlogger)寶座;而她在今年已經獲得Nickelodeon的兒童選擇獎(Kids』 Choice Award)。線下的職業生涯也正向她招手。她最近與企鵝(Penguin)出版社簽約了;她的第一部小說,《網上女孩》(Girl Online),也將在11月出版。
佐拉在現實生活中名叫佐伊•伊麗莎白•薩格(Zoe Elizabeth Sugg)。她是第一個承認她的成名之路是個意外的人。「很神奇,因爲我們從沒預料到這將會變成我們的工作,」她說,「當我們剛開始探索這些令人興奮的新事物時,沒有人知道這會成爲什麼樣子。」
......
佐拉的外形纖細精緻、容貌如洋娃娃般,染色的頭髮綁成了一個馬尾辮。爲了讓佐拉安心,她的經理瑪迪跟著一起來。但瑪迪同意躲到一個遠處的桌子玩她的筆記型電腦。
我們原來打算在外面喫午飯,但壞天氣迫使我們改變計劃。佐拉選擇了安靜的莫德羅會所(有著一股不祥的氣氛),裏面幾乎空無一人。幾位貌似商務人士的客人從他們的漢堡或牛排和薯片中抬起頭來看。我想知道他們是怎麼看待一個外觀凌亂的中年男子會見一個穿著優雅灰色襯衫裙、配著一條花格圍巾、身材嬌小的二十多歲女子這件事。他們認爲我是她的教父嗎? 或我在面試一位住家阿姨?
佐拉從去年開始就一直住在布賴頓市。她租了一個「絕佳的」面海閣樓公寓,在宜家傢俱「豪華」的佈置下與兩位天竺鼠同居。珀西和皮平經常在她的影片裏擔任重要角色,最近一次演出全是他們的入浴鏡頭。
她搬到這裏的主要原因是因爲她男朋友住在這。阿爾菲•德耶斯也有一個名爲「毫無意義」(Pointless)的人氣影客。他和他的朋友在上面做冒險行爲和鬼臉。事實上,布賴頓是個YouTube城市。這也是PewDiePie--一位拍攝自己和朋友們玩電玩,並吸引了大量觀衆的瑞典潮人和影片日記大師馬庫斯•巴特勒(Marcus Butler)的家鄉。 「我不知道這個地方有什麼魔力,」佐拉咯咯地笑著說,「它像是變成了宇宙的中心;我遇到的每個要搬家的人總說:『是的,我要到布賴頓。』」
她在威爾特郡美麗的拉考克(Lacock)小鎮長大。父親是房地產開發商,母親是美容師。當她在藝術、攝影和紡織方面以A級成績畢業於當地公立學校後,她曾考慮過上大學。但她後來拒絕了這個想法,部分是因爲她不確定她想學什麼,但主要是因爲焦慮感。佐拉從小爲極度害羞所困擾,至今仍偶爾會受到恐慌症的折磨。「我不想離開我的家人,離開我任何的慰藉。」
相反地,她在離家不遠的室內設計公司找到了一份學徒的工作,並開始了她的部落格。將寫部落格作爲一個愛好,她只是想記錄她對自己生活中一些異想天開的觀察而已。
佐拉說:」我從來沒有任何組織,從來沒想過它會走到哪一步。實際上它就像是我在網路上的小空間,只是讓我用來寫我喜歡、或我想其他人也會喜歡的東西。「
這種配方無疑地奏效了--靈感豐富的她尤其關注購物。讀了其他部落格描述他們購買服裝和化妝的分享,佐拉決定嘗試類似的事物。「我開始寫跟我媽媽去舊雜貨店的事,那裏能找到價格低於50便士的小化妝品。」
她很快地移向高檔市場,評論她在Top Shop、Superdrug和Primark裏看到的好東西。
我們中間停頓了一下,從吧檯點了午餐。佐拉毫不掩飾她對垃圾食品的偏愛,所以我在瀏覽菜單時做了最壞的打算。但莫德羅會所最引以爲傲的無麩質美食原來是無害的。佐拉點了一個夾滿哈羅米芝士與辣椒沾醬的三明治和冰鎮檸檬水,而我則點了雞肉和啤酒。
當我正大口咀嚼我的雞肉和佐拉正無精打采地啃著一個顯然不怎麼樣的三明治時,我們回到了故事內容。她愉快的樣子、奇特的舉止和對青少年偏好敏銳的鑑賞力很快地吸引了讀者。沒過多久,她日漸增加的關注者開始鼓勵她拍攝影片。她鼓起了勇氣,主要是她知道會有觀衆。「因爲已經有閱讀我部落格的人會直接轉到影片,我想至少有人會看。」
那時,多虧了經濟危機後的不景氣,她的室內設計職務被解僱了。但她初生的影客生涯幾乎被她焦急的父母耽誤了。「我爸爸真的很困惑。他總是叫我走出我的臥室去找一個正式的工作。」
我承認我在這一點是贊同她爸爸的。但事實上,拿著筆記型電腦坐在她的臥室裏對佐拉來說纔是最好的方式。或許她不是第一個嘗試影客的青少年,但她在一個幸運的時刻開始:正當谷歌(Google)在2006年收購YouTube,把貓從滑板上摔下來的有趣影片從線上平臺完全改造成更像是一個電視網。
谷歌想鼓勵「創造者」生產更專業和更有吸引力的內容。這將使美國網路巨擘能從每年花在電視廣告上約2500億美元的市場分到一杯羹。
谷歌託管和發佈創造者們的影片,並共享他們45%廣告的收入。儘管谷歌沒有具體的透露,投行分析師認爲廣告銷售去年爲公司帶來了約50億美元的收入。
關鍵是要鼓勵透過內容去吸引遠不可及的消費者,比如那些正值青春時期和二十歲出頭、不固守傳統電視的羣體。(佐拉本身幾乎不怎麼看電視。她說:「在我這一代,至少我知道的人,看YouTube和電視的比例是70:30。」)如同所述,當前的YouTube用戶潮正準備大舉登場了。
佐拉將她的重點放在13歲到20歲的市場,也是這場變革的最佳目標羣體。儘管她告訴我她的觀衆年齡層其實更加廣泛,讓我大喫一驚。「我的觀衆百分之九是男性,其中我認爲大多數是45歲到50歲。」注意到了我的眉毛快速上升,她補充道,「我總告訴自己這隻像是我爸在看。」
......
佐拉和其他「英國幫」的成員可能相對是明星新秀,但是他們對自己特許經銷權的價值有著高度敏銳性。離她第一次兌現從谷歌收到的60英鎊支票以來,只有短短几年。但現在佐拉是YouTube「時尚行動」(Style Haul)廣播網的一員。該節目針對「千禧年的女性」(約13歲至30歲之間)推廣時尚與美容相關的話題,併爲其影片創造者與「名牌和利潤豐厚的交易」牽線。
她也在「社會人才」機構管理她日益複雜的事務。Gleam Futures這個組織似乎代表了英國所有的YouTube畫面。「就像是幫忙整理,」 她接著補充道,「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會筋疲力盡。」
主要的影客成員間關係都很緊密,他們常常互相出現在彼此的頻道。這種交叉推廣有助於集合觀衆。佐拉的羣組包括她的男朋友、她的弟弟喬(他的部落格現在有2百萬的訂閱者;她堅持說這是在她開始之後纔有的)、馬庫斯•巴特勒,還有路易絲(Louise,又名Sprinkle of Glitter)和塔尼婭•伯爾,一位在她諾威奇家臥室裏給與建議的化妝師,她的化妝產品線最近也在佐拉的影片裏受到推薦。「我們都想互相幫助,這樣我們就可以集合我們所有的頻道,」佐拉說,「這纔是社群媒體的真諦:共享。」
我告訴佐拉她在廣告世界被稱爲「群眾外包領域(crowd-sourced people)的冠軍」。她笑著說:「好酷。我還沒有聽說過這個。」但她也承認,知名品牌正排隊等著兌現她的受歡迎程度。「他們知道YouTube用戶總是有方法能連接觀衆,而即使他們已經有了世界上所有的錢也做不到這點。」一個她影響範圍廣大的例子是和聯合利華(Unilever)的簽約,推銷他們的護膚品給年輕用戶們。
廣告商聲稱願意每月支付2萬英鎊在知名的YouTube頻道上掛橫幅廣告; 而在影片裏每次提及他們的產品, 可以賺到4000英鎊(成本大致與在推特上大喊相同)。佐拉不喜歡提到她賺了多少錢。但基於最成功影客教主的定價來算,現在她單是來自廣告的收入就可以達到每年數十萬英鎊。
當然,這個機會也帶來了衝突。我們在處理午餐殘渣時討論到了這些。我斥責佐拉沒有喫完她的三明治,而她承諾她會打包回家。(事實上當我們離開時,它仍被拋棄在桌上。)
佐拉對她的追隨者像神一樣的掌握在本質上是有著一個影客作家和觀衆之間信任、甚至親密的關係。我追問她,當她從廣告商那兒拿錢並推薦他們的產品時,如何維持這份關係?
她說基本上是一個判斷的問題。她在挑選「合作伙伴」時會考慮她所尊敬的公司或認爲好用的產品。「不管多大筆的錢都不能吸引我去推銷我不相信的東西,」她聲明,「我建立了這個信任我意見的社羣,它對我的價值遠遠超過一張大額支票。」
她聲稱拒絕了90%的交易邀約。有些產品比如酒類,直接被拒絕了。她的焦慮意味著她從未是個嗜酒的人--「我討厭失去自制力」, 因此幾年前她放棄了喝酒。而對化妝品和衣服,她經營著一個簡單的經驗法則。她說:「如果是個我不會穿或不喜歡的東西,我就不會考慮。」她支援的產品都在網址上的描述框裏向用戶披露。
隨著午餐接近尾聲,我們談論到佐拉創造的線下職業機會。
她對她的書感到興奮。裏面涉及到的主題對她來說很重要,例如焦慮、線上人際關係和網路欺凌。談論她的焦慮實際上對她自己很有幫助。「做在我舒適區之外的事和督促我自己對我有好處。」 佐拉對其它想法和建議保持開放;但是她還挺想擁有自己品牌系列的家庭用品。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對自己新得到的名聲有著隨遇而安的態度。"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任何的一切會發生;所以我只會隨它去,並好好把握它,"她說,"誰知道五年的時間裏會發生什麼事。」
當我們起身離開時,我想起了我的承諾。佐拉介意傳個訊息給她的一位年輕粉絲嗎?她同意在我的蘋果手機錄下一段問候(簽名早就落伍了),然後我就心滿意足地離開了。
但當我在回家的火車上檢視記錄時,我發現我在關鍵的拍攝時刻把拇指蓋住了麥克風。微笑的表情、獨特的揮手,卻聽不到佐拉訊息的任何一個詞。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社評撰稿人
譯者/Cindy P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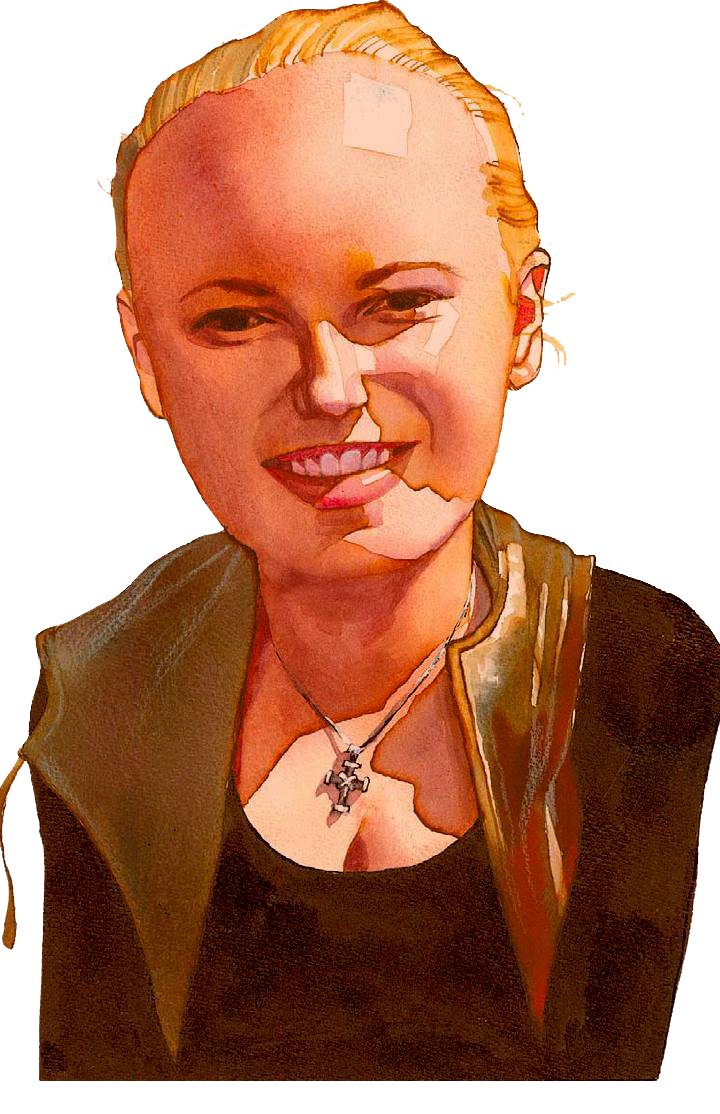
我等的採訪對象是當今世界女子網壇排名第一的卡洛琳•沃茲尼亞奇(Caroline Wozniacki),也是今年溫布爾登公開賽(Wimbledon)賽會一號種子,本人有點擔心的是自己可能認不出她來——雖說前天我曾短暫見過她,當時她剛剛奪得e-Boks索尼愛立信公開賽(e-Boks Sony Ericsson Open)桂冠。她身材高挑、一頭金髮、長相俏麗。然而,在我們約定會面的哥本哈根諾頓咖啡屋(Café Norden in Copenhagen)周圍卻是美女如雲,這叫我如何是好?
現在的時間是上午11點,沃茲尼亞奇原先與我約好於12時在奢華的維克多咖啡屋(Café Victor)一起用午餐,但現在她卻早午餐一起喫了。雖說她是當今世界網壇頭號選手,但給我的感覺卻是:她若走在英國的大街上,幾乎不會有人會留意她。雖說如今正是女子組賽事,諸位在一大堆姑娘中挑出塞爾維亞的揚科維奇(Jelena Jankovic)與俄羅斯的薩芬娜(Dinara Safina)有啥困難嗎?在沃茲尼亞奇之前,都曾登上過世界第一的寶座。看到身材高挑的金髮姑娘,就能確定是沃茲尼亞奇嗎?我覺得肯定行不通。
哈!她來了。實際上,她的氣質與衆不同。她大步流星地徑直朝我起來,來到我面前與我握手。近距離仔細一瞧,她的皮膚潔淨無暇、亮白牙齒,下穿牛仔褲、上穿訓練服、頭戴萊卡(Lycra)伸縮帽。初看外表,她可算是本人見過的身體最棒的運動員。
我問沃茲尼亞奇這麼快就升至世界第一是如何做到的,要知道,一年前她還是世界排名第四。她今年只有20歲,雖說獲得的總獎金已經接近1000萬美元,但還未奪得過大滿貫冠軍。她2009年曾闖進美網(US Open)決賽,但與冠軍失之交臂。在澳網(Australian Open),她給人的印象是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現冷淡呆板,還說記者們應該問些有意思的問題。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她還自己採訪起自己來——真是匪夷所思。雖說從頭到尾一直面帶微笑,但她的自問自答依然乏善可陳。也許她只是一部打網球的機器,在網球場上如魚得水,但毫無自己的生活。也許她會與前世界第一伊凡諾維奇(Ana Ivanovic)一樣曇花一現後就匆匆謝幕,也許她最終會成爲真正偉大的網球選手。
沃茲尼亞奇是一個人來赴約的,身旁並沒任何隨從。她喜歡坐到咖啡屋外面,諾頓咖啡屋適合高消費羣體,這在全歐洲比比皆是——咖啡屋店面不起眼,但賓客如雲,都坐在屋外喫著稀奇古怪的三明治,喝著盛在高腳杯中的熱巧克力。咖啡屋並不奢華,但氣氛輕鬆、讓人愉悅。行走在哥本哈根最主要商業步行街Strøget的行人一直盯著沃茲尼亞奇看,互相間還示意:「瞧,這是沃茲尼亞奇!」有些行人向她招手,嘴裏還喊道:「祝你在溫布爾登有好運!」很顯然,她在哥本哈根家喻戶曉。
我倆首先聊到了網球,她喜歡談論網球,也愛聊自己爭強好勝。前天,我觀看了她在索尼愛立信公開賽決賽中以6:1與6:4直落兩局擊敗薩法洛娃(Lucie Safarova)奪冠的那場比賽,她贏得並不輕鬆。32號種子薩法洛娃還破了她的發球局。「薩法洛娃很不好對付,」沃茲尼亞奇說。「一旦給了她找到比賽感覺的機會,她會一發而不可收。」但沃茲尼亞奇並未給對方機會,在觀衆喊聲震天的加油聲中,她把球打得滿場飛。每次發球前,她總要舞動一天身子,再停下來看一下對方球員,然後在地上把球彈三下。
不知她是否願意談些網球之外的東西,她確實談及了:對我說自己還未喫早餐。她平時喫飯嚴格按照膳食計劃——按時定點喫專門的食物,今天算是個例外。她對喫的東西極爲講究。「我必須喫得多,但必須喫得合適,喫那些補充身體能量的東西。」整個訪談期間,她不止一次提到這。當然,她的身材看上去無可挑剔。
索尼愛立信公開賽賽後,我採訪過她的對手薩法洛娃,對方告訴我沃茲尼亞奇最難對付的地方是:無論自己打出多漂亮的球,她總能回過來,並把你磨垮。「您說得沒錯,」沃茲尼亞奇說。「即便我的對手打出一記非常好的球,我也並不只想把它回過去,我想的是:球回過去後,對方很難再回過來,這樣我就能主動控制球的落點。」
沃茲尼亞奇非常爭強好勝,老說自己「是個不服輸的人」。她說自己比賽時特別亢奮,一心想著打敗對手。小時候,她排球、足球、跑步游泳樣樣玩過。如今她還打拳擊,在體育館裏每天要練上好幾個小時,進行好幾組的肌肉訓練。她的父母是波蘭人,都是體育明星。爸爸彼得(Piotr)曾效力過丹麥某足球俱樂部,媽媽安娜(Anna)也曾是波蘭國家排球隊的隊員。沃茲尼亞奇出生于丹麥,七歲開始打網球。她說,「與其他網球選手相比,我算是個大器晚成者」。但九歲時就贏了她老爸。幾年後,她開始所向披靡。
她說,「有些時候,自己感覺狀態特別棒,這時感覺球與球場都變大了,自我感覺就不可能輸。但有些時候,自己感覺不是太在狀態,但仍會想方設法找到贏的方法,這時就必須找到自己的強項並把它們發揮出來。」
這時服務員走了過來,沃茲尼亞奇點了一份熱巧克力,我則要了一杯雙倍濃度的Espresso咖啡。但諾頓咖啡屋有個奇怪的規矩,點菜與付錢都得自己走到吧檯去。沃茲尼亞奇想要一大份水果沙拉(裏面有檸檬、草莓、藍莓及菠蘿),我則擠過人羣繞到咖啡屋一邊去排隊。我看到她在視窗排了差不多五分鐘的隊,不時朝她招手,感覺挺彆扭的。
在吧檯,有一排賞心悅目的啤酒龍頭與一臺正兒八經的咖啡機。我點了一份夾著厚實火腿及乳酪的單片三明治以及一大盤沙拉。期間,沃茲尼亞奇在用手機發著簡訊。我於是問她給哪位發?是不是給足球運動員尼古拉•本特納(Nicklas Bendtner)發?丹麥媒體一起盛傳本特納與沃茲尼亞奇是一對;本週的Seoghør雜誌(滿是名人的花邊新聞)發現這位「金髮美眉」與效力於英超阿森納隊(Arsenal)的丹麥前鋒在一起度過了一個親密無間的下午(intim aften),而且還配了二張照片:一張是沃茲尼亞奇身著黑色迷你裙與本特納熱烈相擁,另一張是她在擺弄自己那頭金色長髮,本特納則在一旁調皮地看著她,眼神似乎在說「瞧你那頭濃髮!」此時,我立馬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然而,我們先是談了一會兒飲食——如何爲她這臺網球機器補充能量。在過去一週的賽事裏,她必須保持充沛的精力。「我每天的早餐是燕麥,另外還有葡萄乾與香蕉,以補充能量。午餐是義大利全麥雞肉麵,晚餐不是雞肉與沙拉就是牛排與沙拉。」她說自己最喜歡喫裏脊牛排。「我不喜歡喫牛排上的肥肉,」她說。又補充說:「自己特愛喫椰菜。」但從不喫海鮮,還有過兩次食物中毒,每次各病了一週時間,如今她可不敢隨隨便便喫東西。
兩餐之間喫的零食是堅果。比賽期間,補充身體能量的整個過程更爲複雜。上場比賽前一個半小時,她定會喫點意大利麪,時間很難控制,因爲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前一場比賽會持續多長時間,所以她會時刻關注場上比分,並做出最佳判斷。賽後,她會喫一點富含蛋白質的食物,比如說一盤雞肉,所以她一天要喫五頓飯,另外還有零食。
但今天算是個例外,我們點的飲料端上來了。沃茲尼亞奇的熱巧克力黑稠黑稠,此外還有幾片餅乾與一碗乳酪。她沒碰乳酪,巧克力也只喝了幾小口,此外還咬了一丁點餅乾,然後就把它們放到桌上。
要是由著她的話,她會沒完沒了地說網球,似乎問她其它的東西都顯得不禮貌。我知道自己該問些什麼,想問她是否因爲網球而犧牲了個人生活,是否與阿加西(Andre Agassi)與麥肯羅(John McEnroe)一樣,因登上世界第一後出現了難以承受的心理問題。但過了一會兒,話題又轉向了她的訓練計劃。每天她要在場地上訓練三小時的網球——共分爲二次訓練課,每次歷時90分鐘。二次訓練間隙,每天不是6-8公里的耐力跑,就是在跑步機上訓練速度。
在跑步機上訓練強度很大,她說。「我是個不輕易服輸的人。在體育館訓練強度很大,但就得自己設法挺過去。」她用實心球訓練腹肌,還訓練背部與腿部力量;在拳擊臺上聘請了退役拳擊手,任由自己用力擊打對方的手,然後做些身體伸展訓練,接下來是按摩,之後是沖澡,完後是喫高蛋白的食物,最後是喫牛排。「我得喫上幾大份,」她對我說。
這時,服務員端來了點的東西,不時有人走過,微笑著對沃茲尼亞奇指指點點,還掏出手機來拍照,對此,沃茲尼亞奇顯得特有涵養。然而,她實際上是住在摩納哥(Monaco),就是爲了獨處而不受干擾。照她的說法,摩納哥事實上是那些喜歡隱居的名人與體育明星的聚居地,就好比是超級賽馬的高檔馬廄。他們是明星,但同時又是囚徒。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是她在摩納哥的鄰居,她在那有一套兩臥室與兩個衛生間的公寓,有時父母也過去與她同住。
她要的水果沙拉放在長盤子上端了上來,量真大,但她喫得很慢。她最後喝了一小口粘稠的熱巧克力(現在應該已經放涼了),而我點的雙倍濃度Espresso咖啡早已下肚,眼前的厚實三明治裏面塞滿多種五顏六色的夾菜,調味汁都已滲出來;也許就不該點三明治,用手都拿不起來,於是就大口地啃著喫,結果喫得到處都是碎屑,甚是狼狽。
沃茲尼亞奇拿著叉子喫藍果,並說自己並不太愛喫火腿與臘腸。她對所做的一切事情很有節制,對喫的東西十分謹慎。我喫了一大口火腿與抹著融化乳酪的麪包,再伴以一大口抹著蛋黃醬的滑爽花瓣,自己不是太會喫這玩意,結果整得滿臉都是,嘴角還粘有未曾喫盡的花瓣。
我問她有沒有男朋友,她說自己不願談論此事。丹麥媒體老說她與好多人拍拖。「在短短五週時間裏,它們訛傳我有六位男友,第一個拳擊手,接下來是位乒乓球手,然後是納達爾(Rafael Nadal)……說得太多了,連我本人都沒能記住。」但她並未提及本特納。
然而,沃茲尼亞奇是個超級足球迷,她是英超利物浦隊(Liverpool)的球迷,但她喜歡巴塞隆納隊(Barcelona)的踢球風格;她對利物浦隊的球員如數家珍,也與巴塞隆納隊很多球員認識。我問她阿森納隊怎麼樣?「它的踢法很華麗,」她說。現在她總算提到了本特納。「他人不錯,愛開玩笑。」說到這些時,一直咯咯笑著,但不願再往下展開說。
於是我就問她:成爲世界第一是否很難掌控?成爲頭號種子,是否突然有種高處不勝寒的空虛感?「對我來說,這很容易應對。因爲我年輕輕輕就實現了自己的夙願,知道自己想盡可能長得保持世界第一。我總給自己目標,每次步入賽場,就想贏下比賽。」此時壓根就不會感到空虛。
那麼,有沒有覺得自己作出了巨大犧牲?「沒有,」她回答道。「我並不信犧牲,我只相信選擇。對我來說,在成爲世界排名第一的奮鬥道路上,我作了很多抉擇,我對自己所作的選擇感到很自豪。有時候,自己就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我小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問題:是應該與朋友一起去參加派對直至凌晨4點回來,還是按時上牀睡覺,以便第二天早上精神抖擻投入訓練?」她說自己的抉擇並不總是對。「但多數時候,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她說自己在草地上球感很好——球的反彈與之前自己參加過的室內賽場地沒啥差別。我問她最怕與誰過招。「我不怕任何對手,」她說。「我打得好,誰都別想贏我,對方如果打敗了我,只能說明她那天是超水準發揮。」
沃茲尼亞奇現世界排名第一——但她至今仍未奪得過大滿貫。在哥本哈根奪得索尼愛立信公開賽冠軍之前的法網公開賽(French Open),她止步於第三輪。對於自己的糟糕表現,她說:「有時需要幾場刻骨銘心的失利來喚醒自己。」我們還談到了費德勒(Roger Federer)與納達爾,我說自己喜歡費德勒,但看得出她喜歡納達爾,她是納達爾的粉絲,喜歡對方的力量與韌性。她說,「費德勒的技術非常全面,但納達爾韌勁十足。」
我問她是不是臺打網球的機器?她說,不希望有任何東西阻礙自己打網球——也許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在接下來的比賽中,我們會看著她走向球場底線,做著發球前的身體舞動,然後再把球在地上拍上三下。她將來會奪得多少項大滿貫?「我想先贏得一項,」她說。「然後以此爲契機一鼓作氣往前走。」
我希望她能夢想成真。
譯者:常和
地址:哥本哈根Østergade大街61號
熱巧克力:45丹麥克朗
雙倍濃度Espresso咖啡:30丹麥克朗
水果沙拉:85丹麥克朗
火腿與乳酪三明治:115丹麥克朗
總計(包括小費):275丹麥克朗(約合32.40英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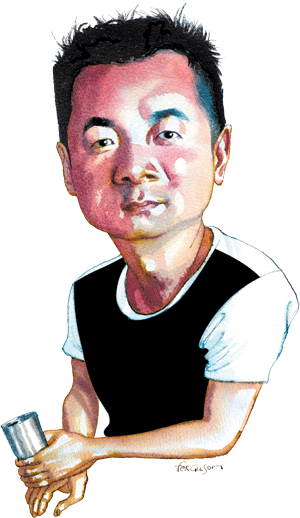
朱駿(Zhu Jun)如何成功說服國際足壇超級巨星德羅巴(Didier Drogba)加盟中國國內球隊申花隊(Shanghai Shenhua)?要知道,這支球隊多數人聞所未聞,而中國也通常與足球不太沾邊。
上個月,德羅巴在歐洲冠軍聯賽(Champions League)決賽中爲東家切爾西隊(Chelsea)罰入制勝點球,這是俱樂部有史以來奪得的一座含金量最大的獎盃。這位象牙海岸球星效力切爾西隊的八個賽季裏,球隊總共奪得10項冠軍,他本人也成爲英超賽場最讓人望而生畏的前鋒。
不久前,34歲的德羅巴在拒絕了包括皇家馬德里(Real Madrid)在內的多家歐洲頂級球隊拋出的繡球後,正式簽約加盟上海申花隊。在擁有16支球隊的中超聯賽(Chinese Super League)中,申花隊目前暫列第12位。
德羅巴一再強調:錢不是自己簽訂兩年半合約的唯一原因(儘管1200萬歐元的年薪可能與他同意加盟存在一定關係)。那麼朱駿成功說服德羅巴的祕訣到底是什麼呢?
德羅巴加盟上海申花隊的訊息正式宣佈前幾周,我與朱駿約定在上海會面。我的採訪對象對足球及外國球星頗爲癡迷、總體爲人也略顯張揚(富有的體育俱樂部老闆往往都是如此),應該會不虛此行。採訪的結果大大超出本人的期望值——只有午餐時間例外,他堅持要求上午10:30會面。
會談地點怎麼會在那兒!當神情緊張的上海興國麗笙賓館(Radisson Blu Plaza Xing Guo Hotel)門衛領我前往酒店的咖啡店時,甭提有多沮喪,但又有啥辦法呢?興國麗笙賓館位於上海以前的法租界。咖啡店擺著金色模擬皮沙發,吊頂則用仿中世紀格子裝飾,這種類似純西式風格的咖啡店在全球隨處可見,供應的是冷早餐。
隨行人員向我的翻譯一再強調:「香樟花園」(Fragrant Camphor Garden,咖啡屋以此時尚名字爲人所知)是朱駿本人最喜歡的餐館——並暗示說朱駿會專門點幾個菜單之外的特色菜(肯定是量大味美),一下子就勾起了我們的食慾。由於本人日程安排中很少有機會與富豪共進午餐,看來這次有望喫到耳熟能詳的中國美食。
但當45歲的朱駿腳穿運動鞋、身穿T恤衫一溜煙走進屋後,本人一下子明白過來,今天享用不到大餐了,應是一次很平常的午餐。朱駿點了可樂,並一再說自己不鋨(最後礙於情面,他點了當天推薦的湯——泰國特色酸辣大蝦湯(Thai spicy sour prawn),他象徵性地喝了一匙,然後就擱在那兒讓它晾涼)。我則點了最適合這個場合的義大利肉醬麵,把我享用大餐的念想全部傾瀉到所點的健怡可樂(Diet Coke)上。
朱駿總是信心十足,「招降」德羅巴這類超級巨星時,他的這種性格定是派上了大用場,「您不覺得我的想法很了不起嗎?」他一度問我,並堅持讓翻譯把問題準確翻給我,以免我一上來就沒聽清。他似乎把自己看作具有哲學家氣質的企業家,屬於比爾•蓋茲(Bill Gates)與佛祖兼而有之。「我的理念就這麼超前,」他說著,並在自己頭頂上方做手勢,「但常人壓根不理解。」
他對我說,德羅巴是「世界最佳中場球員」,許多球隊都想把他招至麾下。朱駿之前也整過讓人意想不到的轉會。今年,申花隊成功簽下德羅巴在切爾西隊的前隊友、前法國國際著名前鋒阿內爾卡(Nicolas Anelka),這樁交易同樣讓人大跌眼鏡。
5月31日,在一場友誼賽中,朱駿與阿內爾卡一起首發出場,踢了半場球方纔下場(2007年,在與英超球隊利物浦隊的一場友誼賽中,他也首發上場,只不過當時踢了5分鐘就下場了。)用午餐時,他一再表示也希望與德羅巴一起馳騁綠茵場。「我倆肯定會同場踢球,我與很多國際球星踢過球。與他們一起踢球不是我的目的所在,要知道,我有能力與任何人同場踢球。」
但作爲球隊老闆,爲何他還要上場?「足球是每個男人喜歡的運動,」他說。「透過踢足球,我們希望變得越發強大。中國如今已經富起來了,但我覺得中國屬於富而不強,整個國家缺乏耐抗性,但足球就是一項充滿對抗性的運動。」
我問他是何種耐抗?「激烈的對抗,」他回答道。「中國並不強大,因爲國人從不說『不』。傳統文化教我們要內斂,而不是持開放心態。不管公衆理解與否,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證明我們實際上有能力做任何事。」隨後,擔心我沒理解,他轉向翻譯,笑著說,「這次訪談一開始就精彩紛呈!就這樣直接翻給她聽!」
「我喜歡足球,」他繼續說,然後不厭其煩向我及女翻譯解釋男人都渴望獲勝,而足球就得爭輸贏。「女人不理解爲何男人總希望獲勝,」他說,然後又補充說他30歲纔開始踢球。在這之前,「自己只打籃球,甚至連足球都沒碰過。」
朱駿關心一件事要勝過與國際巨星同場踢球,那就是心裏老惦記著別人關注他。「我覺得許多富豪看到我與球星同場競技,一定羨慕得要死,」他說。「他們沒機會在賽場上施展自己的僵硬雙腿。」對別的富翁,朱駿顯得不屑一顧,他只看重自己:他說中國富翁有了錢後,無所事事,「每天只是喝酒,然後眼瞅著自己的肚子一點點鼓起來」。
朱駿的財富來自網絡遊戲, 2007年,他出手購買了申花隊(中文意思是「上海之花」(flower of Shanghai)),並把它與同城死敵上海聯隊(Shanghai United)合併。創辦英語版部落格Wild East Football的博主卡梅隆•威爾遜(Cameron Wilson)這樣評價申花隊的老闆朱駿:「他是怪異聯賽中怪異球隊的怪異主席」,Wild East Football專門評論中國足球。
在越來越揮金如土的中超聯賽中,大手筆購買球星的申花隊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廣州恆大隊(Guangzhou Evergrande),恆大隊不久前聘請了義大利奪得世界盃的功勳教練裏皮(Marcello Lippi)。恆大隊目前高居聯賽榜首,每場觀衆多達五萬人。相比之下,申花隊比賽時,體育場的觀衆席有一半空無一人。過去的六個賽季,朱駿給球隊換了九位教練(其中過去二個月就換了三位教練,阿內爾卡臨時作爲球員兼教練還不算在內);他還在自己的微博上威脅要賣掉球隊;當資金週轉不濟時,常靠出售球員來支撐自己的其它業務。然而他堅稱足球是自己的愛好而非主業。
如果希望靠德羅巴與阿內爾卡這樣的世界級球星幫忙打造出一支世界級的國家隊,與中國在全球經濟、或者說乒乓球領域一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那麼還是任重道遠。近2000年前,酷似足球的運動由中國人發明(此事還有待進一步考證)。然而從那以後,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還沒有在這項全球最流行的運動中爭得一席之地。
中國人喜歡看足球;當該國首次成功入圍(迄今爲止也是唯一一次)2002年韓日世界盃時,據報道當時全國售出了1.7億臺電視機,爲的就是觀看中國隊的比賽。但中國國家媒體引用足協官員的話說:在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只有10萬孩子參加各種有組織的足球比賽,部分原因是由於過去幾年足協高層的貪腐所致。
中國內定的下屆領導人習近平(Xi Jinping)最近勾勒了中國足球的藍圖:先是入圍世界盃,然後是舉辦世界盃,最後是奪得世界盃。朱駿的遠景目標的一部分內容就是:「中國足球需要偶像,只有中國足球取得巨大進步才能不斷吸引優秀的年輕球員。」
本人還想進一步瞭解這位雄心勃勃的申花隊老闆,於是詢問他的相關背景,但他變得閃爍其辭。「我在上海長大,沒有任何背景,」他回答道。一再追問下,他才坦承自己中途從上海交大(Shanghai』s Jiao Tong University)輟學,然後去了美國,但清楚地對我說這就是他打算透露的全部內容。我又問他在美國做啥工作?他這樣回答我:「咱不談這行嗎?」
於是我略過前面的不提,直接問他目前的情況:你開什麼車?「我有很多很多車……我只是把它們擱在車庫裏。」我又問他是什麼品牌的車?「各種品牌都有。」最後才摸清楚他共有17輛車:一輛1956年產的吉普車、一輛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一輛法拉利(Ferrari)、一輛勞斯萊斯(Rolls-Royce),實際上各種豪華名車應有盡有——但他說自己給希望成爲富豪者的一點忠告是:「別買奢侈品」。
不清楚這是否屬於不合邏輯的推論、故意違反直覺、還是在反思自己的經濟狀況?2004年,朱駿的網遊公司第九城市(The9)獲得了網絡遊戲《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在中國的獨家代理權。據胡潤中國百富榜(Hurun Rich List)統計,他是中國大陸第57位富豪,個人財富達2.05億美元。由於公司營業收入的90%來自《魔獸世界》的代理,2009年代理權到期後,他也因此被擠出了富豪榜。去年,在美國那斯達克(Nasdaq)上市的第九城市淨虧損2.84億人民幣(約2800萬美元),但朱駿對另一款網絡遊戲《火瀑》(Firefall)會幫助公司重振旗鼓充滿了信心,這款遊戲由他自己控股的工作室所開發。「有一件事是明確無誤的,」他說,「那就是我花在申花隊身上的錢並不算多。」
我問他爲何最近威脅要賣掉俱樂部。「誰告訴你這件事?」他厲聲問道。我指出是他自己把這貼到新浪微博(Sina Weibo,中國版的Twitter)上的。「我當時是氣糊塗了,」他說,並堅稱球員也明白這不是他自己的本意。「球員不關心這些,他們只為給他們付薪的老闆踢球,」他說。
我問他:走馬燈似地換教練,是否也是同樣出於心血來潮?「全世界有這麼多的優秀教練,」他說。「一年換兩個教練並不算不正常,理由是我們不興長遠規劃,中國與歐洲的國情不一樣。」
「足球能表達中國人的思想,」他說道,顯得又像個哲學家。「足球能幫助我們用簡單的方式表達複雜的思想:中國看球的觀衆有4到5億,年輕人將來會理解這其中的道理。雖說這樣考慮問題似乎很荒謬,但我們還得想方設法這樣去做。」儘管他說自己還要老生常談,但他擔心自己死後「幾十年」後別人纔可能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我問他眼下打算用什麼形容詞來描述自己:他立馬回答道:「我」。但即使在中文中,「我」也不算形容詞,所以翻譯與我都以爲他沒理解問題,於是緊追不捨。但朱駿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我」就是他要表達的形容詞,他仍然堅持己見。我覺得朱駿「與衆不同」的特質是固執:他的語法、他鍥而不捨地網羅國際球星以及他的手下員工的阿諛奉承,無不如此。看來對於朱駿來說,世上無難事。他總能得償所願,從不甘心接受失敗。我倆午餐會後兩週,德羅巴正式簽約上海申花隊。
帕提•沃德米爾是《金融時報》上海站記者,Shirley Chen補充報導。
譯者/常和
地點:香樟花園咖啡屋位於上海興國麗笙大酒店
泰國特色酸辣大蝦湯: 45 RMB
義大利肉醬麵:80 RMB
意式小牛肉鱈魚火腿卷(Cod saltimbocca):198 RMB
可樂:45 RMB
健怡可樂:45 RMB
總計(包括小費):475 RMB(約47.55英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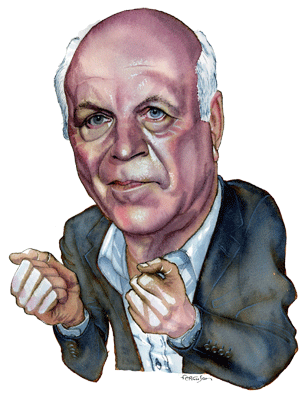
「這是有史以來本人喫得最早的午餐!」格雷格•戴克大聲說道。我剛聽到他隻言片語的歡快倫敦腔,就看見他大踏步走進蘇荷區世紀俱樂部(Century Club in Soho)的餐廳,此時正值12:07,餐廳幾乎空無一人。他抓住我的胳膊以致問候。這位英足總(English Football Association)及英國電影協會(British Film Institute)主席、BBC前總裁(只是他擔任的衆多頭銜中的三個)對於挑選這個時間段頗感自責。
午餐爲何要定這麼早?「因爲本人還是大使劇院集團(Ambassador Theatre Group)主席,我們今早8點舉行了『贊助機會』(sponsorship opportunity,即籌資)活動。」
是否覺得頭銜有些太多了?「這非常適合本人的智商。我從不擅長在一件事上專注過長時間。」但擁有這麼多頭銜,生活不顯得太瘋狂了嗎?戴克看似細想了一下,然後回答道:「不,忙碌比無聊更有意義。」儘管如此,自己難道不願意過——「退休生活?」還沒等我說出口,他就打斷了我。戴克今年已66歲。「不是這個意思,」我趕忙補充道,「但你知道,沒想過到法國南部安享晚年?」
「我覺得自己退休後也不會甘心種種菜,那樣我成了廢物一個,會心生膩煩無聊。」
午餐期間,我還有很多話題要採訪他,然而不到三分鐘,真相就已暴露無遺。本希望打探出這位學習成績糟糕的中下層孩子如何成長爲BBC這家政府機構真正的總裁;希望瞭解這位前BBC總裁爲何會如此受人歡迎,以至於因與布萊爾政府就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報告發生激烈爭執被迫辭職後,憤懣不滿的BBC員工打出橫幅標語要求其留任?簡言之,我希望瞭解戴克事業成功的祕笈,而他已把一切顯露無遺。
必須承認,我是一週後重聽午餐採訪錄音以及仔細回想整個採訪過程後才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抓住我的胳膊致以問候——這種親暱的身體接觸動作在英國不熟悉的人之間幾乎聞所未聞。戴克已過花甲之年,謝頂、身材不高,但他巧妙地把它們轉變成了優勢——這讓他顯得毫無威脅性。他還對我提的空洞問題作苦思冥想狀。隨後他不斷進行自我貶低(用英國人的標準來衡量,有點過了頭):精力無法集中、已過「花甲之年」以及糟糕透頂的園藝水準。說這一切時,語言直白,語調嘶啞又故意壓低,擔任高層30年始終未變的口音。這位BBC前總裁顯得和藹可親、中規中矩。
世紀俱樂部位於沙福茲貝里大街(Shaftesbury Avenue),大門不顯山露水。難道這就是戴克最喜歡的俱樂部?「非也,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誰的地盤,我去那兒僅僅由於英國電影協會就在隔壁緊挨著。沒關係,這兒挺不錯的,無需循規蹈矩。」一份安排滿滿當當的今日日程列印表就巧妙地隱匿在他身旁的盤子底下。他從桌上的大淺盤中抓起麪包就啃。然而,訂起餐來卻是異常沉穩:先是點了豌豆火腿湯,而後是世紀俱樂部的特色沙拉。遵照現代倫敦午餐習俗,他沒點酒水;我則點了血腸以及意式餃子。
. . .
戴克從小在倫敦西邊不遠的海耶斯(Hayes)長大,他是三個兒子中的老么,爸爸是保險推銷員。「我15歲才第一次進餐館喫飯,」他回憶道。「時至今日,我仍然清晰記得那家餐館的名字——位於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的Swan & Bottle牛排吧。老爸一直覺得:下館子喫飯荒謬絕倫。他是個窮光蛋,但我們若要出去,他總這樣說,『你媽做的家常飯要好喫多了。』當然老媽願意下館子,這樣她就不必再做飯了。我記得25歲那年有人帶我去赴宴,這差不多是我的第一頓商務午餐——我覺得那已是自己人生的極致。我被那個場面嚇著了嗎?沒錯,我們這幫去赴宴的人都被嚇傻了。要知道,這是首次到薩沃依(Savoy)這種高檔酒店……富麗堂皇,看得我們眼花繚亂。」
戴克追溯自己早年支援工黨(Labour party)的部分原因就是對升中學甄別考試(11-plus exam)深惡痛絕。他哥哥未能透過該考試。「這真是家庭悲劇,我父母都抓狂了」,他在自傳中這樣寫道。他本人則透過了升中學甄別考試,但只有一門課程優秀,因而以E級(相當於及格)水準從海耶斯語法學校(Hayes Grammar School)畢業。而後成爲瑪莎百貨(Marks & Spencer)的培訓部經理,但很快就被炒了魷魚;他後來開玩笑說所有人都應該從瑪莎百貨幹起,因爲從那以後的境況就會逐步好轉。他下一個工作是擔任《赫林頓鏡報》(Hillingdon Mirror)記者,並對政治萌生了興趣;當了幾年新聞記者後,1971年他以成人學生身份進入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深造(一切自然而然,他如今爲約克大學校長)。
畢業後,戴克一度是個失敗者。他作爲工黨候選人參與競選大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Council),但慘遭失利,自己還曾一度失業。他說,自己是坐在旺茲沃斯公園(Wandsworth Common)一根圓木上在沉思中度過自己的30歲生日,「我到底怎麼啦?」1977年,朋友爲他在倫敦週末電視臺(London Weekend Television, LWT)謀得了一份研究員職位。
戴克逐步成爲電視界的傳奇人物。擔任瀕臨倒閉的TV-am電視臺總編後,透過滑稽木偶羅蘭鼠(Roland Rat)成功提升了收視率;同時獲得了「媚俗」的名聲,但1991年,他成功出任LWT臺長。
「擔任LWT臺長第一天,諸事不順利,」他說。「但我勇敢地走出辦公室,向每位員工緻以問候。這佔了我一天時間,但如果放下架子與員工交流,他們就很可能轉而支援我。1989年,我受電視臺委派去哈佛大學進修了三個月。真正勾起我興趣的是一位名叫約翰•科特(John Kotter)的老師。那時候,大家都在教授領導學這門課程,但他是本人所見過的、第一位以學術方式講授管理與領導的差異的教授。」
管理與領導的差異究竟是什麼?「也正是會計師只能成爲優秀經理、而無法成爲優秀領導的原因所在。尤其在創造性行業,員工必須覺得你與他們彼此理念相通。對方若覺得你在意的只是業績,那麼公司的麻煩便會接踵而至。」
儘管如此,LWT的業績不斷攀升。1994年,當格蘭納達廣播公司(Granada)吞併LWT時,戴克獲利700萬英鎊後離職而去,但他對失去公司異常傷心。
我倆都沒太在意開胃菜,部分原因是我倆已經開始聊起足球來了。在戴克之前,幾乎沒有電視臺臺長對轉播足球賽事感興趣。在上世紀80年代執掌LWT體育節目時,他每年付給足球俱樂部主席1200萬英鎊,從而獲得全年聯賽的電視轉播權。「這些俱樂部主席都睜大了眼睛,簡直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他愉快地回憶道。當時諾丁漢森林隊(Nottingham Forest)的總經理布賴恩•克拉夫(Brian Clough)對他說:「戴克先生,我想與您握手錶達敬意,因爲您是賦予足球應有尊貴地位的第一人:每年拿出1200萬英鎊贊助。」如今,20家足球俱樂部組成的英超聯賽(Premier League)每年獲得的電視轉播費大約是16億英鎊。
1990年,五家足球俱樂部決定發起成立英超聯賽,而那次發起會晚宴的東道主正是戴克本人。但他否認自己成立了英超聯賽。「大衛•戴恩(David Dein,當時是阿森納隊副主席)是我所遇見的、最具足球革新理念的傢伙。是大衛•戴恩成立了英超聯賽,主意是他出的。2007年戴恩離開阿森納隊隊後,該隊再未恢復元氣,」他說。
戴克本以爲LWT會得到英超聯賽轉播權,但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天空電視臺(BSkyB)搶先一步。您失算了,我提示他。「我們誤判了,」戴克愉快地認同我的說法。「但我們終會失算,因爲從付費電視獲取的潛在收入要遠遠多於廣告贊助。」
離開LWT後,戴克擔任曼聯隊(Manchester United)董事,同時經營皮爾森電視臺,當時電視臺還屬於《金融時報》母公司培生集團(Pearson)。1999年,他出任BBC總裁。「入主BBC前,我的年收入是100萬英鎊,但BBC總裁的年薪是30萬英鎊。我從來不爲錢工作。我是個怪人,只要心情舒暢,到頭來總能掙得盆滿鉢滿;再說誰會拒絕擔任BBC總裁這種要職?」
戴克是BBC首位既沒上過著名私立學校、又不是從劍橋牛津畢業的總裁。批評人士指責其「節目媚俗」,尤其是在他把新聞從晚9點移至晚10點後。但他推出了公共廣播數字電視服務節目Freeview,並使BBC一臺節目收視率首次超過了LWT。「有人問我,『你不覺得這是個難活?』我回答道,『似乎不太難。要知道政府每年給我35億英鎊經費,我則負責把它們全花完。』」
. . .
與政府分道揚鑣始於2003年5月29日,當時BBC記者吉利根(Andrew Gilligan)在電臺節目中說唐寧街(Downing Street,首相府)對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相關檔案進行了「刻意渲染」以及「添油加醋」。首相府對此十分震怒。2004年,赫頓勳爵(Lord Hutton)的調查報告爲政府開脫了罪名,並批評了吉利根的報導與BBC管理層。「調查結論荒謬可笑,」戴克氣不打一處來。然而,BBC董事會革去了他的總裁職務。戴克說:「從歷史維度看,BBC董事會已在重大事務上喪失了傲骨。」
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最後查無蹤影,「添油加醋的檔案」成爲全英國的精神創傷,成爲英國版的水門醜聞(Watergate)。許多英國人得出結論:政府有意誤導國民參加伊戰。戴克的精神創傷則只是屬於個人。布萊爾(Tony Blair)想方設法希望彌補缺失。「他邀我喝茶,」戴克回憶道。「但我拒絕了他的邀請。我與布萊爾的關係(壓根不算什麼)徹底破裂。我覺得布萊爾現在非常可悲,儘管腰纏萬貫,但他背叛了工黨的根本理念。我覺得他爲人不地道,一天到晚周旋於一堆不可靠的中東國家之間,靠爲他們出謀劃策賺取大把銀兩,你覺得此等人是何貨色?每當有人與我談高階主管薪酬、說誰都不能掙得比首相多時,我就樂了。我總是這樣說,『且慢,您說的是首相大人擔任首相期間的薪水還是指他未來20年所掙的錢?』」
. . .
戴克如何看待自己的去職?要知道,這是他到目前爲止擔任的最顯赫職務。「我記得自己生了好幾年的悶氣。直到有一天我女兒對我說,『爲啥就忘不了呢?』我想了想覺得,『對呀,言之有理。』」
他從BBC獲得45.6萬英鎊補償款,其中包括一筆8.1萬英鎊的獎金。BBC如今因解僱員工支付過多的補償款而麻煩不斷。我問戴克是否獲得了過度補償?他說自己把獎金之外的補償款悉數捐給了約克大學。並指著我說:「主要原因是我不想回答你提的那個問題。但記住,本人並不差錢,因此這些錢對我來說壓根不值一提。約克大學真有個叫格雷格•戴克、教影視學的教授。有一天,我解釋捐錢的原因是自己覺得這錢來路不乾淨。那個傢伙這樣對我說:『我就是教如何掙髒錢的教授!』」
BBC給的解職補償款是否太高了呢?「BBC的問題是高階主管薪酬定得太高。因此,他們的解職補償款就必然很高。」
我倆要的主菜已經下肚,卻沒太注意它到底是什麼。戴克要了「小份牛奶咖啡」。我說他注重很健康飲食。在英國,這算是某種指責。「這是因爲我起太早、早餐喫太多的緣故,」戴克爲自己這樣辯解。
離開BBC後,他擔任了更多主席頭銜:在自己心愛球隊布倫福德隊(Brentford football club,董事們有時「不得不舉行慈善募捐以支付球員的薪水」)以及英國電影學會。「接受採訪時我曾直言不諱地說:『你們這壓根不是英國電影協會,而儼然成了倫敦電影協會(London Film Institute)。』」爲了扭轉這一狀況,英國電影協會建起了專門的網路影片播放器BFI Player,這個點播平臺給全體國民提供本國經典影片(多數爲免費)。
在英足總,戴克掌管英國足球以及長期戰績不佳的國家隊。我倆午餐會沒過幾天,英格蘭隊就奪得了2014年世界盃出線權,但整個國家隊的情緒依然悲觀低落。「溫格(Arsène Wenger)曾對我說,」——戴克模仿起阿森納隊主帥的法式口音——「您爲何要執掌英足總?要知道,得花上10年才能讓英國足球真正見效,球迷很快就會忘記你。」
但戴克想幹這份活。19歲時,他觀看了1966年世界盃的大部分比賽,這是英格蘭唯一一次奪得世界盃。「我當時在西倫敦工作,完全能在比賽前一天駕車去溫布利球場(Wembley)買票。」
他列舉了自己最喜歡的球星:貝斯特(George Best)以及吉格斯(Ryan Giggs)。很顯然,這兩位都不是英格蘭人。戴克在上月的一次演講中坦承:「英格蘭隊沒有輝煌的戰績史。」當時他爲英格蘭定的目標是奪取2022年世界盃冠軍。他曾抱怨英超聯賽的賽場擁有太多外籍球星,英格蘭本土球員很難取得突破。
我說這也許是英格蘭球員還不太優秀吧。「情況可能是這樣,」戴克回答道。「抑或說可能沒給他們創造成功的階梯。英超聯賽也有大量名不符實的外國水貨球員。」
我倆約定的午餐時間到了,戴克也是諸多重任在肩,但兩個大男人侃起足球來就出了名地難說再見,於是又多聊了25分鐘,爭論的焦點是爲何英格蘭隊老是壯志未酬。
戴克一直在兜售這樣的觀念。「布倫德福德隊的老闆是馬修•貝納姆(Matthew Benham)吧?他統計了英格蘭隊的所有數據,他說英格蘭隊戰績不佳的最大一個原因是運氣不好。他說可以透過罰點球而不是抽籤來決出勝負。英格蘭隊已有四五次因罰點球而慘遭淘汰(這就是英格蘭隊的結局)時,他說如果運氣稍好點的話,英格蘭隊就能贏上一、二回了。」
我們本可以無休止地聊下去,但戴克必須趕去與某政客彙報足球事宜。我問他會以何種方式被後人銘記。「我在BBC工作時,有人曾問過這樣的問題,『您希望員工如何評價您?』我回答說,『本人離任時,希望員工能說,『我來BBC之前,這兒就是個特別溫馨的家。』我想說把自己的孩子培養好了,希望這一代孩子比我們更體貼家長。我29歲時,就不會因爲自己的車壞了而給父母打電話,但我自己的孩子會這樣做,好像我啥都能搞定似的。但我的孩子也經常打電話找我閒聊,我們那時從沒這麼做過。」
回答無懈可擊,避免了太過自負以及道貌岸然的自謙。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可能沒教過學生這樣的管理學祕笈:待人和善。
-------------------------------------------
世紀俱樂部位於倫敦沙福茲貝里大街6163號,郵編號:W1D 6LQ。
豌豆火腿湯:6英鎊
血腸:9英鎊
世紀俱樂部特色沙拉:10英鎊
意式餃子:12英鎊
2份礦泉水:7英鎊
濃咖啡:2.5英鎊
牛奶咖啡:3英鎊
總計(包括小費):55.69英鎊
譯者/常和

與當今世界最具才華、也是最捉摸不透的撞球運動員共進午餐就定在倫敦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的Roka餐館,這家雅緻的餐館薈萃各種日式特色菜,裏面食客如雲,他們談興很濃,餐費大多可報銷。現役撞球選手、五屆斯諾克世錦賽冠軍羅尼•奧沙利文(Ronnie O』Sullivan)之前多次光顧這家餐館。「我認爲這是家本地餐館,飯菜質量上乘,」37歲的奧沙利文柔聲說道,話音中略帶埃塞克斯(Essex)口音。他饒有興趣地盯著一盤正端往旁邊餐桌的開口殼斑節對蝦。
奧沙利文以瘋狂的清球速度而榮獲「火箭」(「Rocket」)綽號,在很多人看來,他是有史以來最具天份的斯諾克選手。今年五月,在最負盛名的謝菲爾德(Sheffield)斯諾克世錦賽上,奧沙利文最終折桂,儘管他在過去的一年中未曾參加過任何職業比賽,試問當今撞球界如此贏球舍他其誰?諸位設想一下,若網球選手羅傑•費德勒(Roger Federer)休戰一年,然後再強勢迴歸勇奪溫網冠軍,其中難度該有多大?
與許多人一樣,我也是個普通的斯諾克愛好者,但卻是奧沙利文的鐵桿擁躉:他是斯諾克界最後的萬人迷,不由得讓撞球迷回想起昔日的那些激情歲月:當時1800萬電視觀衆如癡如醉地收看「颶風」阿歷克斯•希金斯(Alex 「Hurricane」 Higgins)以及「白旋風」吉米•懷特(Jimmy 「the Whirlwind」 White)等頂級選手的精彩賽事。但我以謹小慎微的態度對待我與奧沙利文的午餐會,這位訪談嘉賓是當之無愧的爭議性人物。有時他似乎恨透了斯諾克,而他又是天才選手。
就在我上次採訪他的那一週,奧沙利文又鬧得滿城風雨:他暗示斯諾克比賽的假球行爲可能會變本加厲,幾天後他又收回了自己的相關評論。「大家都瞭解我的爲人與球風,」勇奪今年的世錦賽桂冠後,他曾以略帶歉意的口吻說道,「我情緒的確不太穩定。」
他今天顯得率真、隨和、輕鬆自在,與他的火爆脾氣判若兩人。他點菜的速度堪比擊球速度。「剝皮對蝦,知道吧?」他問服務員,然後轉向我說。「當時咱倆都喜歡這道菜的外觀,沒錯吧?您還想來點啥?肉還是魚?」我回答說除了不喫菠蘿外啥都行。
「行,」他對服務員說,「我們就多喫點海鮮,喫鱈魚,這家餐館的鱈魚味道做得不錯。黑鱈魚行嗎?咱就點它?還要米飯嗎?」奧沙利文的母親是來自伯明翰(Birmingham)的義大利裔,在餐桌他關切地問起我的情況時,我纔看出一絲苗頭。「你若覺得還喫不飽,」他說道,「等會兒咱再加菜。」
他沒要酒,轉而要了綠茶。他並非滴酒不沾,他過去曾酗過酒、吸過毒。在最新出版的回憶錄《飛越迷夢》(Running)中,他坦承自己曾參加過酗酒者互戒協會(Alcoholics Anonymous)以及麻醉藥品濫用者互助協會(戒毒會,Narcotics Anonymous)的活動。《飛越迷夢》書名就取自於成功戒掉酗酒與吸毒陋習的強制性活動。他甚至承認:每年都有好幾天自己想盡情放縱一下時,就會「舊癮復發」。
當我問他何爲「放縱」時,他苦笑道,「唉,就是一年365天中,自己有時想肆意渲洩自己,可能持續一天、兩天、或是三天,自己想離經叛道一下。」我對他說這沒啥大礙,進而問他如何把握這個度?「實際上就壓根不該這麼做。我只是覺得自己不能恣意妄爲、沒有底限;也明白自己若是練長跑,身心就不會過度疲乏。」
他首次練長跑約在十年前——貨真價實的越野跑,和長跑俱樂部的隊友一起沿著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的泥濘土路跑上七、八英里。他每週的長跑量約爲30英里。儘管他口口聲聲說自己太過壯實(超重太多),但今天他穿著緊身牛仔褲與帶帽黑上衣,身材顯得十分勻稱。
「哇噻,我心愛的美食,我啥時候都喜歡喫,」當服務員端來兩盤包子時,他高興地說道。一盤是牛肉、生薑及芝麻餡,另一盤是用辣椒黑鱈魚龍蝦餡。「我媽媽有西西里血統,因此我喫的總是離不了意大利麪,而且我姥爺全家都特能喫。」他用筷子夾送包子入嘴,一邊嚼一邊說:「因此嘛,我真得應該有所節制,否則自己真變成肥肥的豬小弟(Porky the Pig)了。」
我設法把剩的最後一個龍蝦包子留給他,但他堅持說:「你喫了它,還有好多菜沒上呢。」
. . .
他從小在切格威爾(Chigwel)長大,如今仍居住於此,這個富人聚居區位於倫敦金絲雀碼頭東北方的郊區。奧沙利文打小就崇拜七屆世錦賽冠軍、蘇格蘭人斯蒂芬•亨德利(Stephen Hendry)。父親專爲他在花園盡頭修了一間斯諾克練習房。奧沙利文很顯然是個撞球神童:10歲就打出自己的第一個100分;15歲成爲有史以來打出147滿分杆的最年輕球員;17歲成爲排名賽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冠軍。滾石樂隊(Rolling Stone)吉他手基思•理查茲(Keith Richards)透過樂隊隊友、奧沙利文的摯友朗•伍德(Ron Wood)結識對方,他稱奧沙利文爲「斯諾克界的莫扎特」。
奧沙利文對此稱謂一笑置之。獲得自己首個100分後,他在學校觀看了電影《莫扎特傳》(Amadeus),影片中的藝術大師莫扎特桀驁不馴、滿口髒話。「那是我當時所看過的最棒影片,沒覺得莫扎特有啥不正常,認爲他只是在表露自己的內心世界。」
然而當別人稱他撞球神童時,他明確表示不解。「我覺得自己並非天才,」他說。「本人從來就不是最具天份的撞球手,我練得特別刻苦。」我對此存疑:因爲就是他,在1997年的世錦賽上,僅用時5分多鐘就打出147的滿分杆,要知道這是有史以來的最快記錄。
他承認自己好多次曾有這樣的想法:「哇噻,我的擊球速度獨步天下。而且我也知道別人也清楚這是有史以來的最快擊球速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因此倍受關注。」
我們點的兩碗米飯到了,同時還有一盤斑節對蝦,碩大的對蝦被剁成大塊,並用日本柚子豆麪醬料(yuzukosho)烹製而成。他先嚐了一點,然後用粗俗的語言準確評價道:「真他媽的好喫。」
奧沙利文的致命弱點是過分追求盡善盡美。他比賽失利後往往會有極端出格的行徑,如2006年的世錦賽(電視實況轉播),在對陣亨德利的比賽進行到「中盤」時,對自己球場表現失望之極的他選擇中途退賽。
「打出盡善盡美的比賽是可能的,」他說,手中的筷子從碗裏夾個不停。「我對此深信不已,這是本性難移,因爲自己真做到完美時——就感覺這是最美妙的時刻。這是自己終生孜孜以求的東西,而且不管付出多大代價,自己還會繼續奮鬥不止。」
他認爲自己的巔峯時期是14、15、16歲那陣子,當時他自我感覺酷似「一臺永不知疲倦的機器」。父親不斷督促引導他,時刻給他灌輸並非與生俱來的爭強好勝意識。
「我當時就想一門心思打球,」奧沙利文回憶道。「即使輸掉比賽,我也從不悶悶不樂,反而會直接問老爸,『我能去參加下場比賽嗎?』老爸就會看著我(他會因爲我持此態度而重罰我)說,『你應該感到傷心,前幾天你讓我茶不思、飯不香,因爲你輸了比賽。』」老爸每每想起這段往事,都會開懷大笑。老爸的名字也叫羅尼,是個「典型的大男子主義者、做事專橫跋扈,但也很親切。」
奧沙利文家境不錯,但行當屬於旁門左道。他父親在倫敦蘇荷區(Soho)經營性用品店。孩提時代,他就記得裝滿現金的信封落入父親郵箱筒後發出的砰砰聲。1992年他轉爲職業撞球運動員,父親因參與夜總會鬥毆以殺人罪入獄。法官裁定該案件存在「種族色彩」,年少的奧沙利文堅持父親清白無辜。
在他看來,老爸所犯的重罪(殺人罪)是太樂於替人排憂解難造成的。「他爲人兩肋插刀,從不計後果,」他說。「這是老爸栽的一個大跟頭,這也是他最終鋃鐺入獄的原因;他愛打抱不平,就是這類人——『別人有難,那麼我就會拔刀相助。』」
他父親坐了18年大牢後,於2010年刑滿釋放,如今就住在這附近。父親入獄18年,是否激勵他不斷進取?「我要誤入歧途很容易,但他的忠告言猶在耳——『練好身體、堅持做好這、堅持做好那,』我時刻牢記他的諄諄教導。」但奧沙利文的確曾誤入歧途,1995年,他母親因逃稅也被判入獄一年。「當我爸媽……」在找尋合適的詞表達意思時,他略停了一會兒,然後說:「不在家時,我沾染上了酒癮與毒品。我大量吸毒——當時醉生夢死。在斯諾克賽場上,我的表現一塌糊塗,毫無戰鬥力。」
前後判若兩人是其撞球生涯的一大特徵。儘管孩提時代戰績輝煌,但直至2001年,他才真正奪得世界冠軍。他因意志消沉及精神疲憊而錯過了很多場比賽。1996年,他因用頭撞擊裁判而被罰2萬英鎊。2008年,他在中國公開賽的記者招待會上竟爆黃色粗口。中國是斯諾克新開發的舉足輕重的市場。
我問他是否對這些「瘋狂時刻」(奧沙利文字人如此稱謂)心生過愧疚。「沒有,絲毫不存在愧疚。它們屬於成長中的經驗累積,」他回答道。我於是問他:甚至對頭擊裁判事件也不覺愧疚?該事件引發的原因是該執法裁判試圖把他的一位朋友請出選手休息區。「這是裁判自作自受,」奧沙利文略微坐直身子後厲聲說道。「他活該。我當時道了歉,並說,『非常對不起,』但我不會回家後對此悔恨交加、痛心疾首。當時我的想法就是,『去你媽的,我不能受這種汙辱。』」
這時服務員走過來,端上用香蕉葉包裹的黑鱈魚片。「真棒,」奧沙利文讚道。
他最近一次掀起的波瀾事後證明處理起來最爲棘手。三年前,他捲入法律訴訟案,起因是爭奪與前女友所生兩個孩子的撫養權——七歲的女兒Lily以及六歲的兒子小羅尼。就子女探望權相關條款引發的訴訟案讓他錯過了好幾場比賽,此舉招致斯諾克官方管理機構的極度不滿。爲此他曾一度放棄長跑,並患上了恐慌症。如今他仍深受失眠症之折磨。但讓人不可置信的是:每天晚上只睡3個小時的他竟勇奪2013年世錦賽桂冠,要知道,整個賽程長達17天,比賽緊張激烈。
「這是重量級比賽,但有時我也覺得,『去你媽的,自己真想再經歷一次輪迴?』穿著內衣褲與T恤衫坐在房間裏,深感心力交瘁。自己不願出戰,因爲內心既恐懼又焦燥,而觀衆想對我說,『好樣的,羅尼,打得真漂亮,』而內心則覺得,『自己就想縱情嚎叫。』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情緒宣洩時是啥模樣可見一斑。「實際上在過去3、4年,我哭的次數超過以往的總和,」他對我說。「很多次是由孩子引發的,我深深地愛著他們,對他們永遠不離不棄,一直會把他們撫養成人。然而,我被迫進行可怕的法律訴訟,爭奪與他們共度短暫時光的機會。」
他的聲音開始哽咽,眼中閃出了淚花。突然間他嗚嗚哭了起來,背靠著椅子,並用揉皺的白餐巾擦拭淚眼。我試圖緩和一下氣氛,但無濟於事。讓我驚恐不已的是:我儼然成了《金融時報》的皮爾斯•摩根(Piers Morgan,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平媒記者之一,電視節目「英國達人秀」同時也是「美國達人秀」的評審,是三位評委中口味最刁鑽,評判最嚴格的一位)。
「都怪我,」他喘著氣說,並拿走了擦拭眼淚的餐巾。「我不該談論這事,沒想到自己會失控;自以爲有能力應對,我沒事,真沒事。讓你見笑了,你也有孩子,理解爲人父的感受,爲了孩子你也會豁出去的」——他加重語氣說道。
他一用筷子把鱈魚片與米飯撥拉進嘴巴,我倆就實現了角色互換。就是這樣,我對羅尼說:你把鱈魚都喫完,它們可是營養豐富。
「哎喲,好笑吧?」他已恢復了神情。「我覺得一切都已不重要。對於合同簽定時試圖對我施加壓力的相關法規條款,本人心知肚明,我毫不在意,想要什麼你就拿去好了。我已經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
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去年世錦賽奪冠後,他的小兒子從觀衆席中跑出來與他共享勝利。「對我來說,一切都已過去,我無需再證明什麼。我費盡周折獲得他的撫養權,然後把他帶到決賽場,你無法想像我當時的激動心情。」
服務員過來給他添滿綠茶。「還想再喫點啥?你還餓嗎?」他對我說。他要了菜單,然後我倆又點了一份由辣椒、檸檬以及蒜味醬油烹製而成的雞肉。這道菜端上來時,「火箭」奧沙利文重歸沉著冷靜。他把沒喫完的米飯給我。我倆又點了兩份布丁:我要了荔枝冰糕,他則點了日式拔絲香蕉煎餅。
臨近不惑之年,他自認爲展示了最佳競技水準。他把這一切歸功於知名體育心理學家史蒂夫•彼得斯(Steve Peters),對方幫他成功解決了情緒波動問題。球場之外的生活也漸入佳境,他有更多的機會定期探望孩子。今年初,他與女演員萊拉-羅阿斯(LailaRouass)訂婚。然而,他的好運「終結於」布丁,他喫了幾匙後就把那又甜又粘的布丁遞給我。「想喫點嗎?嚐嚐吧,你把剩下的一半喫掉。」我用匙子舀了一大口,已坦然接受午餐貪喫客的角色了。
我們的訪談以領悟達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烹調技術而結束。奧沙利文與這位喜愛斯諾克的設計師已成莫逆之交。他還回憶起頗感愧疚的一次「瘋狂時刻」:當時他威脅要把斯諾克歷史上最偉大的選手、也是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大勁敵亨德利發配回「蘇格蘭過可憐巴巴的卑賤生活」。有好幾年,亨德利都不願和他說話。「這可能是我這輩子幹得最糟糕的蠢事,因爲他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
服務員過來端走了盤子。「沒啥大不了的,對吧?」他說。「實在不好意思,我剛纔情緒失控了,有點丟人現眼。」
不用擔心,我向他保證。掉幾滴眼淚不必無地自容。「費德勒也哭過嗎?」奧沙利文歡快地問道,他很喜歡網球,喜歡勤奮刻苦的納達爾(Nadal)的程度絲毫不亞於費天王。勤奮與天才方能造就成功。「我希望你今天的採訪滿載而歸,」他說道。
《飛越迷夢——奧沙利文自傳》(『Running: The Autobiography』)由英國Orion出版社(Orion Books)出版,精裝本售價18.99英鎊,網路讀本即將面世,售價爲9.99英鎊。
-------------------------------------------
Roka餐館位於倫敦E14 5FW區加拿大廣場(Canada Square )40號
斑節對蝦:18.90英鎊
西蘭花:4.90英鎊
日本柚子豆麪醬烹製的黑鱈魚:29.60英鎊
辣椒炒雞肉:13.90英鎊
大香菇:5.90英鎊
龍蝦黑鱈魚餡包子:12.60英鎊
牛肉生薑芝麻餡包子:6.90英鎊
2碗米色:5.20英鎊
日式銅鑼燒煎餅:7.9英鎊
水果冰糕:2.50英鎊
2杯綠茶:6英鎊
蘇打水:3.90英鎊
總計(包括小費):132.98英鎊
譯者/常和

每年八月,紐約就成了一座空城,城裏的上流人士不是趕赴漢普頓斯(Hamptons)的私人海灘、就是到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起伏無垠的原野度假。可謂只見其名在門上,難見其人在家中————當然時尚界人士除外,因爲每年9月6日開幕的紐約時裝週(New York Fashion Week)就在眼前了。
「哦,我每年8月回紐約,」設計師卡羅琳娜•海萊拉(Carolina Herrera)笑著說。她旗下公司年銷售額已達十幾億美元,她專爲那些東奔西走的達官貴人設計服裝,其中就包括新任駐日大使卡羅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肯尼迪又是瑪莎文雅島(Martha's Vineyard)的夏日度假常客。「這就是幹這一行的代價,但我真的喜歡這行,想去哪裏就去哪裏,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
我倆在聖安布魯斯餐廳(Sant Ambroeus)見面時,當然並無條條框框的限制。聖安布魯斯是家意式餐館,位於紐約曼哈頓西村(West Village)的名流居住區。此處綠樹成蔭,遍佈紅磚砌就的褐沙石豪華房屋以及盛開著白花的梨樹。事實上,如今這兒幾乎空無一人,以至於我不禁納悶爲何選在這裏見面。整天與名流打交道的設計師卡羅琳娜•海萊拉,自己的辦公室位於紐約時裝區的黃金地段,卻捨近求遠到市中心來赴約,這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難道是想增加影響力?知名設計師似乎總想增加影響力。或是實地打探開設新店的理想地段?抑或她與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一樣,喜歡清靜獨處?(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1979年曾完全參照庇隆夫人(Evita)的模樣,給海萊拉創作了一幅絲網印刷作品,自此以後,她盡人皆知。)
「我女兒帕特里夏(Patricia)就住在附近,」當我問海萊拉爲何選此處見面時,她這樣說。「我倆常來這兒,我希望你也能喜歡,我覺得這兒有家的溫馨感。」
海萊拉夫人成立自己的時尚帝國,憑藉的就是這樣的理念:希望與人分享其光鮮亮麗的生活方式————生活闊綽、富有教養、國際視野、謹慎持重,而她就是這一切的化身。卡羅琳娜•海萊拉更爲人所知的稱謂是海萊拉夫人,這既是出於對其實際年齡的尊重(她已73歲),也是因爲她身上特有的那種老派優雅舉止的需要。
她赴約時,上身穿著抽象風格的米色及黑色大麗花圖樣點綴的綠色短上衣(選自自己設計的秋冬季服裝系列),再配以得體的圍巾、黑色短裙以及雙耳大珠母墜掛件,顯得再合適不過了;金色短髮往後梳理,顯得氣度不凡。事實上,她的時尚形象總是那麼完美無缺(這就是爲何她多次榮獲國際最佳著裝獎(International Best Dressed List)的原因)。1980年成功榮登名人堂,並於2011年被《名利場》雜誌(Vanity Fair)評爲有史以來最會著裝的女性。她本人又是自己時裝的最佳模特兒,明快風格的白色襯衣配塔夫綢料蓬蓬裙已成時尚經典,讓好幾代人對定製襯裙連衣裙以及套裙念念不忘,讓心儀者欲罷不能。這種始終如一精心打造出的形象光彩照人,在我這時尚主編面前,都顯得咄咄逼人,其他女性的強烈共鳴也就不難理解了,她們大多都說「我希望裝扮成她的模樣。」她則因此而掙得盆滿鉢滿。
. . .
實際上,她本人並不願意這樣形容自己。海萊拉喜歡這樣答覆我這樣的詢問者:「我只是製作服裝,感興趣的只是美的東西以及讓女性更靚麗。」 這樣的回答似乎顯得滴水不漏,尤其是透過說自己「只是製作服裝」。 出生於加拉加斯的海萊拉也已成爲一系列現代時尚元素的象徵。她不僅展示了女性創業能力(她創業時已41歲,在謝里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看來,海萊拉在服裝界出類拔萃之前,在這一行早已「成績斐然」),展現了拉美新興時尚市場與日俱增的影響力,而且標誌着專爲名流設計服裝的社交型設計師的崛起。但冷靜斟酌後,發現她的這個回答也是個性十足。換個說法也能說明她的性格:儘管她曾多次獲邀擔任電視真人秀節目《天橋驕子》(Project Runway)的評委,但一直拒絕參加。
「那些改編自真實故事的電視節目,」她說,並朝爲我倒蘇打水的服務員微微搖搖頭,然後又低聲說道,「給我倒靜水」——「諸如《暴徒狂妻》(Mob wives),內容全是講自己:誰希望這麼個活法?瞧瞧大家一天到晚關注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以及其體重這類花邊新聞。我敢肯定這是她有意爲之,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被健康減肥諮詢機構慧儷輕體(Weight Watchers)相中。」她翻了翻白眼,然後問道:「您說啥話題最無聊?」還沒等我開口,她就脫口而出,「我對你說:那就是聊自己!」
採訪的開場白就如此調侃自己,似乎有些犯忌。但海萊拉受過良好教育,因爲她這樣回答道,「人的一生就是成家立業、生兒育女,接受良好教育以及謹言慎行」。抑或她後來的說法, 「我被認爲是品牌代言人,但我覺得自己是凡人一個。」點完菜(她要了意大利麪,本人則點了三文魚塔塔、北韓薊沙拉)後,我決定轉向政治話題————今年四月以微弱優勢當選委內瑞拉總統的馬杜洛(Nicolas Maduro),我覺得這個話題似乎不偏不倚,於是問她投票了沒有?
「我當然投票了,」海萊拉說。「我每次都參加。但我就在紐約投票。我投票支援恩裏克•卡普里萊斯(Henrique Capriles)。委內瑞拉需要變革。若一切順利,我會說選誰都沒問題,但如今經濟出現了大問題,反對黨候選人卡普里萊斯年輕有爲、理念又新,不選他選誰?」她經常回加拉加斯,最近一次回國是11月參加自己孫子的婚禮。但她也說:「我設法不談論政治,因爲我女兒和外孫女目前仍生活在委內瑞拉。委內瑞拉是個美麗的國家,但時刻有危險,我不希望出啥不測。」這讓我引出的政治話題「半路夭折」。
生活在加拉加斯的是她的大女兒梅塞德斯(Mercedes)。海萊拉和她現任丈夫、《名利場》雜誌專稿編輯雷納爾多•海萊拉(Reinaldo Herrera)育有兩女,帕特里夏和小卡羅琳娜。另外兩個女兒——梅塞德斯與安娜•路易莎(Ana Louisa)是自己與首任丈夫、地主吉列爾莫(Guillermo Behrens-Tello)所生(他倆結婚時,海萊拉年僅18歲,她24歲離異)。小卡羅琳娜目前供職於海萊拉名下的香水公司,而帕特里夏則專司成衣業。「女承母業益處多多,」海萊拉說。「有啥問題,她們隨時就會告訴我,」勿庸置疑,她的兩個女兒對品牌推廣居功至偉,使她設計出的服裝更符合年輕人的審美情趣。
孩提時代,海萊拉全家就常去歐美遊歷。她有貴族血統,父親是空軍軍官,曾一度擔任過加拉加斯地區的總督。她與雷納爾多的交際圈遍佈全球。 有一天,她與閨蜜、時任美國《Vogue》雜誌主編的黛安娜•弗裏蘭(Diana Vreeland)交談時,提到自己正考慮成立紡織品牌。弗裏蘭卻說「這個想法毫無新意,要是我的話,就進軍時裝界。」海萊拉對此仍記憶猶新。當時,她的全部服裝專業知識僅限於自己離異後,在加拉加斯的璞琪(Emilio Pucci)專賣店打工六個月。但閨蜜的忠言深深地打動了她,不久之後,她在某雞尾酒會上遇見拉美最大的雜誌出版公司老闆德阿馬斯(Armando de Armas),對方願意出資充當其合夥人。
1981年,她在紐約成立了同名時裝公司,從此以後公司總部始終留駐紐約。海萊拉說她自認爲仍是委內瑞拉人,但卻自視是美國設計師。「紐約是世界之都,」她說。「若在這裏能創業成功,在天下就暢通無阻了。」
我對她說,哎,這不就是辛納屈(Frank Sinatra)的歌詞嗎?此時我們點的菜端了上來。但紐約實際上並非舉足輕重的時尚重鎮。我問她:難道您沒有想過若在歐洲創業,不是更聲名顯赫嗎?「我不知道爲何有這種說法,」海萊拉回答道,「這種說法荒謬至極,我的意思是,所有歐洲設計師都希望開拓美國市場。所以爲何要捨近求遠呢?我實在無法接受這種想法。」她的首次個人時裝秀就在紐約的大都會俱樂部(Metropolitan Club)舉辦。
「我覺得當時的想法是推出一個系列後,一切順其自然就行了,」她說,並用手指著自己的意大利麪。「然後消費者購買,我們再接再厲。」她們於1986年推出了低價CH系列香水;1987年,西班牙香水及時裝家族企業蓓格(Puig)推出了她設計的香水。1995年,蓓格出資購入德阿馬斯名下擁有的公司股權,成爲海萊拉公司合夥人。「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她說。如今全球共有95家卡羅琳娜•海萊拉全資門店以及400個時裝銷售點。她專爲傑奎琳•奧納西斯(Jacqueline Onassis)以及小布什夫人勞拉(Laura Bush)設計服裝,也爲影片暮光之城四:破曉(上)(Breaking Dawn – Part 1, Twilight)設計了婚紗。
隨著巴西與墨西哥成爲日趨重要的奢侈品銷售市場以及自己在西班牙語世界聲名日隆,海萊拉對公司的飛速發展前景充滿了信心。去年,她在保加利亞、印尼、巴拿馬、巴拉圭以及烏茲別克等10個國家新開設了門店。今年五月,她作爲特邀明星嘉賓參加了新加坡時裝週(Singapore Fashion Week),以慶祝自己在該國開設的首家門店。
儘管她是時裝界首波交際型設計師的一分子——她們的培訓與資質主要在於穿個性時裝的能力以及對市場瞭如指掌(諸如此類的設計師還有德里貝斯(Jacqueline de Ribes)和瑪麗•麥克法頓(Mary McFadden))————但她是事業至今仍蓬勃發展的碩果僅存者,目前仍沒退休打算。
「我不會把海萊拉門店徹底改頭換面,從而讓自己品牌的擁躉者一頭霧水。」她說。「我秉承迷人魅力以及始終如一的理念。」儘管如此,她也理解進軍時裝界隨之而來的種種質疑,而這往往會付出相應代價。她說當初剛推出自己的品牌時,她對設計師朋友候司頓(Halston,已故)和盤托出自己的計劃時,對方說,「您難道瘋了嗎?」她對那些進軍時裝界、卻鬧得滿城風雨的非科班設計師(托里•伯奇(Tory Burch)、貝嫂維多利亞(Victoria Beckham)以及奧爾森姐妹(the Olsen twins))感同身受,她清楚這些人所面臨的種種艱難險阻。
. . .
「問題是如今人人都成了設計師,」她說。「成功的歌星與網球明星都搖身變成了設計師!人人都對時裝說得頭頭是道,都能品頭論足一番。甚至我的司機對此都略知一二。但真要獲得成功,必須要有獨到眼光,這至關重要————比院校的科班教育要重要得多。設計師對比例、紋理以及色彩要有獨到眼光。這就是爲何有人對維多利亞說三道四、說肯定另有高人爲她的設計捉刀之類的話時,我就氣不打一處來。不親歷爲之,就不能妄下定論。維多利亞有她自己的眼光,她言之有據,源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儘管她不可能操刀所有時裝草圖、親自裁剪所有面料,但從確定每個時裝季的主題到如何詮釋,她都深度參與其中。然而,她從不僞稱一切都是自己親歷親爲。」
沒錯,她告誡年輕一代的同行:「不要包辦一切,打點生意要另請高人。」我問她是否讀過謝里爾•桑德伯格的著作。她說自己沒讀過,但她說對此很感興趣。我問她是否覺得女效能擁有一切時,她答覆說「可以————但不能同時擁有。」
儘管如此,我說她同時把家庭和事業兼顧得井井有條。海萊拉則說,自己創業伊始,女兒上的是全日制學校,而當時時裝界本身發展還很緩慢,也容易操控。「如今還能兩頭兼顧嗎?」我問道。「我真不知道,也許做不到。」她說丈夫全力支援自己,但並非像新派男人那樣。當問她丈夫是否幫忙做家務時,她不禁笑了。
「哦,他不做,」她說,但隨後補充說自己也不願意他這樣:「我覺得女人做家務其樂無窮,女人天生就喜歡操持家務。」海萊拉老公的最大貢獻並非在精神上大力支援她,而是「把女兒帶走、他們仨一起度春假,可以讓我全身心工作!」她說。紐約的春假往往與秋冬季時裝週在時間上重合。
我問她做好這一切的訣竅是什麼,她回答道:「出色的員工。」與其說她感興趣的是當一位女權運動代言人,倒不如說她更是願意爲自己母國委內瑞拉大聲疾呼的政治活躍分子。但這並非說她不看重自己時尚代言人的角色。這時附近一位用餐者走過來問:「不好意思,您是設計師嗎?」海萊拉握著對方的手笑著說「是」。
「這種情況常發生嗎?」她的粉絲離開後,服務員過來清理餐桌,我問她。海萊拉承認這是常有的事。「我心情愉悅,」她說。「爲啥不呢?這表明我們做得好。」我倆都有意迴避甜食,轉而點了咖啡,咖啡端上來時,店方免費贈送了一小盤甜點。
也許她喜歡自己的擁躉,但很不喜歡時裝秀後臺那一套做法————記者搭訕時,要求他們就設計精髓發表高論;而他們獻飛吻時,各大時尚雜誌主編則恭維他們是「天才設計師」。「『您的設計靈感源自哪裏?』是普天下最糟糕透頂的問題,」海萊拉說。「那些恭維者,雷納爾多常對我這樣說:『他們還能說啥————我很不喜歡你的設計?』他們不得不恭維一番。但那意味著你不要相信這一套。」
該買單了,但服務員笑著說,「今天算免單。」很顯然,他頗爲自豪————餐廳對知名時尚設計師很大方。但他們顯然不知道我們《金融時報》採訪付餐費的規矩,我對此作了解釋。服務員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一名叫託德的經理走了過來,他與海萊拉握手,海萊拉則向他介紹了我。託德說傳訊部已說過這頓飯算餐廳請。我則回覆說:謝謝美意,但本人必須買單。
「她必須買單!她是報界從業人員,」海萊拉以責備的口氣說道。託德最終只得同意,隨後離開了我們。海萊拉笑著說:「問題在於:店方想免單!而通常買單時,食客一下子都去衛生間了。」她主要是想開個玩笑。但我倆都心知肚明:不管你有多謹言慎行,終有百密一疏的時候。
範妮莎•弗瑞德曼是《金融時報》時尚主編
-------------------------------------------
聖安布魯斯餐廳位於紐約西四大街259號
蘇打水:7.50美元
靜水:7.50美元
北韓薊沙拉:19美元
三文魚塔塔:19美元
Fusillone all』Arrabbiata:19美元
兩份瑪奇雅朵咖啡:4.5美元
卡布奇諾熱牛奶咖啡:5美元
總計(包括小費):104.73美元
譯者/常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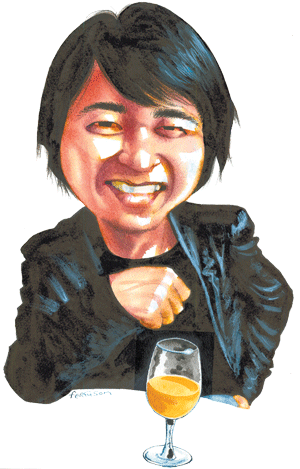
韓寒的笑容一派孩子氣,讓人放下戒心。這個有明星派頭的帥小夥是一名成功的賽車手,有許多女性粉絲,還有許多廠商找他做代言。他非常有錢,也顯然不爲名氣所累。韓寒有一個年輕又漂亮的妻子,還有個可愛得不得了的女兒。對了,他還是暢銷小說作家,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博主。大家崇拜韓寒,因爲他擅長用智慧和指桑罵槐的方式,與中國審查機構玩貓捉老鼠的遊戲。
只有29歲就這麼紅,又取得了這麼多成就,我想像這應該是個自信滿滿又難以捉摸、有些虛榮也有些自大的人。但在藝術家餐廳裏坐在我對面的卻是這樣一個人:儘管非常自信,但聲音不大,語氣輕鬆得近乎開玩笑,表達的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些觀點。有一度,在形容中國教育如何扼殺孩子個性時,韓寒拿起他的筷子,垂直立在桌上,說:「教育體系把所有的人都變成一樣,就像筷子一樣,它必須得一樣長才可以。」
近13年前,韓寒從位於上海郊區的松江二中退學(韓寒在與松江交界的金山區亭林鎮長大),從此開始了他的寫作事業。他父母都在政府部門工作:母親管福利的,父親是個不得志的小說家,筆名就叫韓寒,在金山區黨報工作。韓寒退學一定是因爲厭倦了。他把本應用來唸書的時間,用來書寫自己對學校的怨恨和年輕人的愛情故事,這也就是小說《三重門》(Triple Door)。韓寒說:「這是我自己的生活,幾乎一模一樣。」《三重門》銷量達到200萬冊,韓寒一夜成名。
儘管後來又寫了一些小說(大多數是關於女孩和賽車的),韓寒的生活在2006年出現了一個轉折——他開始寫一些關於以下問題的博文:審查制度、徵地事件、中共官員的腐敗問題、有毒工廠和被中國經濟成長甩在身後的窮人。韓寒的部落格迅速成爲這個網路發達的國度閱讀人數最多的部落格。到目前爲止,韓寒部落格的訪問量已超過5億,他從而成爲中國最著名的博主。《紐約客》(New Yorker)去年夏天的一篇特寫中提到,人們對韓寒瘋狂追捧,他開通個人微博(Weibo)賬戶後,吸引了75萬名粉絲。鑑於他開通微博後只發了一個字:「喂」,能吸引這麼多粉絲已經算不錯了。
我們約好在上海西南郊區松江區會面。韓寒就住在那個灰濛濛的地區。他爲沒有約在上海市區內會面表示抱歉,說自己要爲下週的比賽試一輛車。韓寒用賣小說賺的錢買了賽車之後,他的賽車事業開始了。(午餐後,韓寒的領航孫強開車送我去浦東機場,車速快得會令劉易斯•漢米爾頓(Lewis Hamilton)自愧不如。)
這家餐館是新開的,裝修得很精緻,混合了中式和仿西式的風格。服務員領我進了一個包廂,裏面有一張圓桌和幾把吱呀吱呀的紅椅子。坐下沒幾分鐘,韓寒和他妻子金麗華(Lily)就到了。韓寒穿了黑色皮夾克、黑T恤、灰色修身長褲和黑皮靴。他的頭髮亂蓬蓬的,臉上掛著一絲微笑。韓寒掏出3部手機擺在桌上,這3部手機很少有同時安靜的時候。餐廳舍不得開空調,因此韓寒一直沒脫皮夾克。金麗華出去點菜的時候,我請韓寒先簡要描述一下今日中國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情況。
韓寒說:「雖然我們不擁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但是可能要比西方國家想像的稍好一些。」他的中文表達流暢而有節奏,常常爲了強調而重複一些詞或句子。他還說:「我們其實有自由寫作跟表達的權利,但是問題就是政府有隨時把它刪除的權力。」
第一盤菜上來了,是一盤我認不出是什麼的白色泥狀物(雞汁豆腐馬蘭頭),還有一大扎鮮榨橙汁。菜放在轉盤上,我們把轉盤轉了一圈,每人取了一些。韓寒又說,在進入網路時代之前,有爭議的材料根本沒機會發表。「有了網路以後你就可以發表任意的文章,」韓寒說,「只要你不害怕自己受到傷害。」至於哪些內容會觸怒審查者,這確實取決於他們的心情。「如果這個負責審查的人今天喫了一頓很好的午餐,可能他們的尺度就會大一點。但是如果明天他們心情不好,或者他們失戀了,尺度就會緊一點。」
又上了一盤菜,XO醬茶樹菇魷魚須。我問韓寒,他是不是在和審查者博弈,試探他們的尺度。韓寒說:「其實對於我來說不完全是一些博弈。」他補充說,政府或讀者都不是他首先考慮的因素。他說:「你不能只為讀者寫作。你不能爲了他們的口味去寫文章。」這時韓寒的一部手機響了,他邊說邊把手機交給了金麗華,她拿著手機去了包廂外。
許多民族主義者攻擊韓寒不愛國。還有人說韓寒不夠激進。2月份的時候,有人稱韓寒僱用槍手寫作,韓寒威脅要起訴這個人。儘管如此,韓寒應對批評和審查的方式基本是模糊處理。他說:「如果你想持續地抗爭下去,一定要儲存自己。」2010年,被囚禁的中國作家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韓寒發表了一篇博文,裏面只有一對雙引號,那形狀就好像奧斯陸諾貝爾頒獎禮上那張空著的座椅。這篇博文點擊數達到150萬次。
菜開始一盤接一盤地上。有黑椒牛仔粒、蔥爆蝦球。過了一會兒,女服務員端上一盤中式切法的鹽焗雞(好像是在盤裏用彎刀現殺的一樣)。那道雞非常美味。大家轉動轉盤夾菜時,我斗膽問了一個關於薄熙來(曾經行情看漲的政治明星,現已被免除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他的妻子因涉嫌謀殺一名英國商人被拘留)的問題。薄熙來倒臺,被視爲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最大的政治危機之一。
「對我以及許多中國人而言,我們其實並不知道薄熙來這件事是怎麼回事。因爲中國政府的訊息是不透明的,它只會給你一個新華社的通稿。」韓寒頓了頓,說,「沒有人知道,連他兒子都不知道。」
當然,我也不知道。但我說,我認爲薄熙來最大的過錯在於他將民粹主義政策直接帶向了羣衆——繞過了正常的黨組織機構。「薄熙來會顯得比較高調。」韓寒回答說,「在歷史上還有另外一個人,就是毛澤東,他跨過了黨的組織機構,直接透過《人民日報》向人民來發起文化大革命。」
韓寒說:「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很不喜歡薄熙來的。很多人都有一種擔憂,比如說薄熙來會不會把中國帶向一個言論或者社會環境更加緊張,更加倒退的一個情況。」不過,韓寒認爲不應過快下結論:「有一點最關鍵的是,包括對於最後所宣佈出來的薄熙來倒臺的原因或者說他的太太怎麼怎麼樣,這些我們並不知道具體當中發生了什麼。」
服務員端上一鍋石鍋海鮮豆腐。我把話題轉回一些不太敏感的話題,關於韓寒早年的寫作。韓寒說自己打小就喜歡寫作:「老師佈置一篇,有的時候我會寫兩篇。」
韓寒認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對學生進行政治宣傳。他說:「我們被灌輸了一種仇日情緒。我們從教科書中學到的是,共產黨真了不起,獲得了抗日戰爭勝利。但長大後你會發現抗日戰爭是國民黨打下來的,所以在這個時候你就會產生落差。」
我問及他在去年12月在部落格上發佈的《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這三篇文章以問答形式寫成,許多他的追隨者認爲這背離了以往的風格。文中韓寒過於傾向漸進式轉變的立場也令一些人失望,藝術家艾未未說文中的觀點太過正統。更令一些讀者不安的是,這三篇文章受到了官方媒體的稱讚,顯然是因爲這個寫書的壞孩子宣揚改革,而不是革命,讓他們鬆了一口氣。
「因爲有些時候我會回答一些讀者的問題,」說到這裏,他用筷子夾起了一塊盤中的雞肉,「我發現很多讀者的問題是你會不會去引導一場革命。我發現這是他們的問題,他們把革命想的太簡單了,他們把中國和一些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國家聯繫在一起。」
在一篇文章中,他暗示將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共產黨未免太輕鬆了。畢竟,官方的數字是共產黨有八千萬黨員。「其實我表達觀點不是說我們不能攻擊共產黨,我們爲什麼不能攻擊它?我要表達的觀點是這樣,每個人都覺得這個社會的罪惡,這個國家的罪惡,是源於體制。我只是說每一個人,都是體制的幫兇。」他說,「如果這個體制很明顯地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的話,要做的辦法就是你去改變更多的人民,當人民有了更多的改變的話,那你的政黨、你的體制就會有相應的改變。」
又上來了一道菜,這次是一大盤雞肉和白菜煮成的嫩白色的濃湯。據我所知,中國人點菜可從來都不會少點。「他如果真心想要,在二十年內一定能得到。」他說,「如果在二十年內得不到就說明人民還不是太想要。」
一些讀者和知識分子批評他暗示民主不適合中國人,而韓寒說:「我從來沒有表達過。」他還對去年秋天發生的「小悅悅事件」發表評論。當時兩歲的女童小悅悅倒在地上的血泊中,18個行人都視而不見。「中國的社會冷漠是一直存在的,它冷漠自私。」他接著又解釋,或許行人確實沒有注意到小悅悅,而小悅悅死去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韓寒說:「我也相信這樣的一個解釋,假設說路過的人很粗心,那的確也有可能看不到。」他想說的是,在一個冷漠的社會,人們會對不幸視而不見。
如果說一些事情讓他絕望,那麼其他事件會不會激起他的希望?我很好奇對於去年在示威抗議非法徵地行爲之後,組織了自己的選舉的烏坎村民,韓寒會有什麼看法。他的回答比我預料的更有力。「對於烏坎來說,我當然很高興,因爲我看到了中國未來民主的道路和光芒。」韓寒說,「我的觀點是,我更希望在城市可以先有一些選舉,或者在一些相對比較發達的城市,所以我寫過一篇文章說『讓一部分人先選起來』。」這句話巧妙地借用了鄧小平那句名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韓寒接著說:「我不奢望全中國忽然間明天就開始普選,但是我覺得至少可以讓一兩個城市先選起來,然後讓其他城市的人在那裏看著。」
一些人認爲韓寒在思想上不成熟,但上面的話並不像一個思想上不成熟的人能做出的思索。另一方面,韓寒也經常被人比作中國最著名的雜文家之一魯迅(1881-1936)。「我不喜歡魯迅的文章。」韓寒乾脆地回答,口氣彷彿是一個自傲的英國年輕劇作家,說自己不是很瞧得起莎士比亞。不過我追問道,與這樣一個高大的人物相比較,恐怕會讓人困擾。「其實我就是一個車手。」韓寒回答,臉上又閃現出那種笑意。「我知道有各種各樣的力量,他們會讓我身上賦予各種各樣的希望,覺得我好的人會覺得我很好,覺得我差的人會覺得我很差很差,一無是處。」
承受著如此多的關注,他真的沒有感到煩惱嗎?他聳聳肩說道:「沒有。」我問他,17個月前,他的女兒出生以來,自己有沒有變得更腳踏實地。「反而現在可能要更激進一些,希望那種政治改革推動的決心會更大一些。」是不是因爲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呢?「對,我不希望她離開中國。」他一邊說,一邊拿起突然出現到滿滿當當的餐桌轉盤上的一小塊蜂蜜吐司。「但是我的國家又不夠好,對於我唯一的辦法就是,哪怕一點能力也沒有,我也要儘量讓她變得如我所願。」
這樣一來,我就有了一個最簡單的收尾問題。他希望自己的女兒成長在怎樣的國家?在並不常見地停頓片刻後,他終於說:「就一個答案,當你再來中國的時候,我們再做採訪的時候,永遠不會再問到那種關於政治、關於作家寫作自由這些問題,永遠沒有了,我們談論的完全就是足球、食品、命運、電影。」
戴維•皮林是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譯者/何黎
上海市松江區九亭鎮蒲匯路188號
雞汁豆腐馬蘭頭 26元
XO醬茶樹菇魷魚須 68元
石鍋海鮮豆腐 42元
海鮮焗飯 38元
蔥爆蝦球 68元
黑椒牛仔粒 68元
鹽焗雞 48元
上湯娃娃菜 22元
蜂蜜厚多士 26元
鮮榨橙汁 x2 116元
合計(含稅和服務費)560元(合56英鎊)

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建議在洛杉磯的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進午餐,但爲了便利起見,我們將地點選在了洛杉磯貝爾艾爾酒店(Hotel Bel-Air)的露臺。此處距離他與妻子兼合著者海蒂(Heidi)同住的鋼/玻璃結構住宅不遠。
變化是非線性的
我很高興能在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好萊塢名人經常出沒的地方,採訪現年77歲、全球最著名的未來學家托夫勒。我甚至有可能看到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和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在他們常去的隔間裏喫午飯呢!在等待托夫勒到來的時候,我點了一杯維斯珀(Vesper)馬提尼酒——洛杉磯現在正流行這種復古情調的、由杜松子酒和伏特加酒對半混合而成的烈性酒。我對自己說,這是對托夫勒核心思想之一的印證:變化是非線性的,可以倒退、向前或橫向發展。
36年前,他和海蒂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重磅著作《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不到十年後,他們出版了《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書中預測了「分衆化」(demassification)、多元化、基於知識的生產、以及變化的加速。然而矛盾的是,托夫勒目前在巴西、中國和南韓等國的名氣比他在本土更大——在本土,他所預言的未來或多或少變成了現實。美國新聞界對他們的新書《財富的革命》(Revolutionary Wealth)並未作太多報導,只有《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今日美國》(USA Today)刊發了一些不錯的書評。不過,此書已在德國和義大利引起媒體關注,並已在中國和印度成爲暢銷書。他剛訪問日本,他在那裏被視爲真正的哲人智者。
歐洲已經落後
打過招呼之後,托夫勒開始悲嘆中東事態。這並非我想討論的話題,因此我脫口問出第一個問題:你在自己的國家裏是一位無名的預言者,這是因爲沒有人願意傾聽你的觀點呢,還是因爲美國人已經徹底接受了你的觀點,以至於再沒什麼可爭論的了?他多多少少接受了後一種解釋,並提到歐洲對他重新興起的關注,似乎緣於「歐洲已經落後」的觀點。「革命的財富體系,完全是關於分散經營、細分市場、靈活性以及權力的分散和下放,而歐洲領導人卻試圖建立一個龐大國家。」他表示。「歐洲人的機構和社會運轉非常緩慢。他們爲這一點感到驕傲。這沒啥不好,但總會有代價。較大的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和義大利,與美國和亞洲相比正陷入相對衰退之中。
我建議我們點菜,因爲這看來會是一次長談。托夫勒點了一份帶有烤蝦的柯布沙拉和蘇打水。我點了火腿、甜瓜和一杯黑品樂葡萄酒。我們繼續談論他的預言在哪裏引起的反響最大。托夫勒列舉了這些年來聽取他和海蒂建議的領導人,這份名單令人印象深刻:1986年,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策劃改革之時;1988年,中國改革派總理趙紫陽;從中曾根康弘(Nakasone)到小泉純一郎(Koizumi)的多數日本領導人;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印度的阿卜杜爾•卡拉姆(Abdul Kalam)。南韓的金大中(Kim Dae-
jung)和委內瑞拉總統雨果•查韋斯(Hugo Chavez)曾在獄中閱讀過他的著作。托夫勒最近的交談對象是墨西哥電信業巨擘、全球富豪之一的卡洛斯•薩利姆•埃盧(Carlos Slim Helu)。
影響力僅次於比爾•蓋茲和彼得•德魯克
托夫勒停下來喫菜時,我開始考慮人們會如何定義他所做的事。儘管管理諮詢機構埃森哲(Accenture)最近將他列爲影響力排名第三的商業領袖,僅次於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已故的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但托夫勒既非湯姆•彼得(Tom Peters)式商業諮詢師,亦非管理學大師。他更接近於人們過去稱爲大師級思想家的那類人。那麼,他在想什麼呢?
他目前提出的一個重大概念是:新技術正使得生產者和消費者透過根本的融合,形成「生產消費者」(prosumer)。老齡社會到來的跡象之一是:「60歲以上的人口很快就會達到10億,」這有巨大的潛在意義。他指出,「從自我診斷,到即時尿檢,到自我治療,他們將使用奈米科技帶來的新療法,完成以前需要醫生執行的任務。這將改變整個保健行業的運作方式。」無疑,非貨幣經濟的這一巨大前景將推動醫療技術市場的發展,創造巨大的新價值,併爲某些人創造巨大財富。
不拿薪資的「生產消費者」
他表示,有這種桌上型生產,「生產消費者」將真正發揮作用。在某些情況下,生產/消費合一,將導致「第三職業」興起——企業不再將勞動「外包」至印度或菲律賓,而是交給不拿薪資的消費者,譬如我們透過自動取款機(ATM)自己進行個人銀行業務操作,以取代銀行必須僱傭的出納員;或透過網路追蹤聯邦快遞(FedEx)遞送的包裹,而不用依賴拿工資的職員。
托夫勒認爲,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轉折點,是在1.2萬英里高空創造財富。他辯稱,今天的財富產生於各處(全球化)、無處(網路空間)及別處(外太空)。「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爲從手機呼叫到ATM提款的萬事萬物,同步精確時間和數據流的關鍵。由於追蹤精確,它們使準時化生產成爲可能。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對空中交通管制也變得至關重要。衛星還可透過追蹤天氣,提供更準確的預報,提高農業生產率。」
在托夫勒看來,多元化財富體系將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中得到體現。「我們不會看到家庭的消亡,但會看到家庭形式的多元化。我們處於接納同性戀民事婚姻的邊緣。社會上存在著單身母親、未婚夫婦、已婚無子女夫婦、經歷多次婚姻的父母。一夫一妻制不會消失,但一夫多妻制可能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工作將回到家中
與以往那些有地理界限、有著不同社會歸屬的族羣社團不同,他預測將出現志同道合者的網路,使人們前所未有地集合到一起。在托夫勒的新財富體系中,我們將從標準化需求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生活在符合個人節奏的「定製時間」,按照自己的日程表工作和玩耍。隨著我們成爲生產消費者(prosumer),大部分時間花在貨幣經濟之外,「創造項目」將取代傳統的工作和職業。工作將告別工廠和辦公室,回到家中。
托夫勒沉浸在他的想像之中,忽略了盤中的沙拉。我提出,由於很多人是現狀的既得利益者,這種劇變無法順利地被人們接受。如果大機構都在這種新的動態體系之下逐漸消亡的
話,安全也將不復存在。看看那些抗議他所描述的經濟模式的法國學生們吧。
托夫勒回應道,我們將看到「浪潮衝突」在全球爆發。他指出,我們正目睹它在墨西哥發生,最近的大選表明,該國已差不多一分爲二,一邊是「第一次浪潮」中的南方農民和「第二次浪潮」中的城市工會,另一邊則是「第三次浪潮」中受益於北美自由貿易聯盟(Nafta)和全球化的北方,它更爲繁榮。類似的衝突也正席捲中國和巴西。
新老體系間的「速度衝突」
即使在美國,彼此不同步的機構,也陷入了新老體系之間的「速度衝突」。「標準化教育屬於調整速度最慢的機構。假定你是一名監督過往汽車車速的警察,你爲『商業之車』計時——它在競爭壓力下會以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迅速改變。但理應面向未來培養年輕一代的『教育之車』,卻僅以每小時10英里的速度行駛。在如此明顯的不同步情況下,你無法擁有成功的經濟。」
在托夫勒看來,日本同樣面臨著不同步問題。「技術是比較容易的部分。難的是讓機構與社會結構產生協調一致的變化,進入同步狀態。這正是社會與文化僵硬刻板的日本的失敗之處。日本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放鬆』。」
這種速度衝突延伸到了地緣政治領域,不止是虔誠的前現代伊斯蘭教徒和後現代世俗消費者階層之間的衝突。托夫勒指出,在南韓,金大中令人欽佩地爲其旨在改變北方的「陽光政策」,設立了循序漸進的30年時限。但一些突發事件——比如金正日近來的飛彈試射行動——在該政策有時間奏效之前改變了政治日程,使該政策不了了之,就像戈巴契夫推行的改革,其發起人心目中也有一個長達10年的時間框架。他警告稱:「這種速度衝突往往會偏離當前的變革軌道,或至少會使其走上彎路。」
「線性推斷法容易誤導」
「這就是線性推斷法爲何如此容易誤導的原因。在今後20年的某一階段,很有可能出現一次重大的社會劇變,令所有預測都出現問題。」午餐現已延續到了午後,我們開始感受到灸烤著洛杉磯的熱浪。托夫勒的新書並未花費多少筆墨談論全球變暖問題,我想知道他在這方面的想法。「我首先懷疑那些對未來的預測和對過去的推測——我懷疑這真會告訴我們今後幾百年將發生什麼,以及人類出現前發生過什麼。」
他表示,「還記得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吧。如果說曾有過關於2000年的誤導預言,那就是這本書。」
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在他預言未來的這些年中,有沒有弄錯的時候?「上世紀70年代,我們討論過人類和動物克隆,認爲它將在80年代中期成爲現實。」他回答道。「我們低估了科學發展的緩慢步伐。儘管我們指出了道德上的難題,但我們沒有預測到反科學的基督教徒的強大力量。」我們見面這天,正趕上布希(Bush)否決了放寬幹細胞研究的法案,這一點無須我提醒。「此外,」托夫勒笑道,「無紙化辦公尚未實現。」
托夫勒點了咖啡。我點了櫻桃果汁冰糕。從我們的談話中,不僅看到了他那真正宏大的思想——開放、客觀、無私,也就是說,知性的正直——而且看到了一個真正的好人。無論未來變化有多快,他明顯走在了未來的前面。
譯者/牛薇
柯布沙拉1份
甜瓜和義大利燻火腿1份
蔬菜沙拉1份
櫻桃果汁冰水1份
濃咖啡1份
幹馬提尼1份
聖沛黎洛礦泉水2份
黑品樂葡萄酒1杯
總計:
128.28美元

鋼琴家郎朗享有的全球聲望,讓他在自己選擇的一家巴黎中餐館接待我時,讓我感到一些慌亂。當我提出已經以郎朗的名義預定了座位時,女服務員似乎沒有聽懂我的話。接著我被領到餐廳前面的一張小餐桌前,我擔心我在拼讀郎朗的名字時把音調搞錯了——在講廣東話和普通話時,音調至關重要。儘管這兩個詞在英文中看上去一樣,但在中文裏,他的名寓意「快樂和陽光」,他的姓寓意爲「受過教育的紳士」。
17歲成名
令人高興的是,26歲的郎朗很快就到了,以他浮華的標準來看,他今天的裝束相當嚴肅,黑色夾克,黑色襯衫還有牛仔褲。他名譽的光環以及友好徹底改變了局面。餐廳經理熱情地跟他打招呼,並領我們走到了餐廳後面的一張餐桌前,一扇竹木屏風給我們帶來了一種私人房間的效果。這是北京和上海所有高級餐廳的設計。我問他,他是否覺得在中國外出就餐很難,因爲他是如此的著名。他回答:「極其困難,這既是幸運,也是不幸。」我後來意識到,這番話反映了他成爲一位著名鋼琴家冷靜的處事方法。然而,他可能很久不在中餐館點菜了,因爲我們那張小方桌上很快就堆滿了燒茄子、甜玉米羹、美味的京醬肉絲以及一壺茉莉花茶,食物還在不斷端上來,以至於我的筆記本幾乎都沒地方放了。
上菜的速度趕不上郎朗的筷子在盤子間跳躍的速度,他好像在指揮一個管弦樂團,他手法敏捷地把菜夾到我的盤子裏。(一次,他夾起一塊我掉在筆記本上的豬肉,把它放到了旁邊的盤子裏。他隔一會就責怪我光顧著記錄,卻沒有喫菜。)他說道:「這家餐廳非常好,每次我到巴黎都會與朋友和親戚來這裏喫飯。」他來到倫敦是爲了參加一場音樂會。我剛剛乘坐歐洲之星(Eurostar)從倫敦趕來與他會面。我告訴他,幾年前當我第一次從香港搬到倫敦時,我一直在倫敦西區Queensway附近找房子,因爲當地的餐館能夠提供一些倫敦最好的中餐。
有段時間,我一直在擺弄我的數字錄音機,他忍不住開玩笑說「它肯定是英國製造」。這是對人們有時取笑中國製造的產品質量的反駁。
中國出口商已開始走向市場高階,郎朗也成爲新時期中國最爲人熟知的面孔之一。他第一次受到世界的關注,是在1999年芝加哥附近的拉維尼亞(Ravinia)音樂節上,那是一場神話般的首演,當時17歲的他頂替安德列•瓦茲(André Watts),站在1.7萬名觀衆面前。演出前一天晚上,他曾夢到他的鋼琴變成了「一艘宇宙太空船,環繞地球」。當他演奏完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氣勢磅礴的第一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後,獲得了現場觀衆雷鳴般的掌聲,此後他的事業蒸蒸日上。演出結束後,聚集在一起的音樂大師們,包括指揮家克里斯托弗•艾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Isaac Stern)、該音樂節的音樂總監以及其他人,邀請他在凌晨2點後開始的私人演奏會上背譜演奏了難度很高的巴赫(Bach)的《哥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
10年過去了,郎朗曾與奧迪(Audi)、萬寶龍(Montblanc)和索尼(Sony)和Adidas(Adidas)等品牌簽約,他經常被視爲一位跨界明星,一位有著搖滾明星吸引力的古典音樂家。(Adidas現在銷售的一款印有郎朗簽名和金色條紋的訓練鞋售價125美元。)他曾在北京2008年奧運會(Beijing Olympics)開幕式上演奏,他在東西方有著無數的追隨者,在YouTube上,他的影片廣受關注。如今,超過3000萬的中國人正在學習彈鋼琴,鋼琴如此受歡迎至少要部分歸因於郎朗如日中天的事業。
普及古典音樂
錄音機終於恢復正常了,我問他關於本月的音樂會系列以及與倫敦交響樂團(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的計劃。他對4月18日舉行的大師班尤其感到興奮,該活動的高潮將是他爲來自倫敦東區學校所有等級的100位鋼琴家演奏舒伯特的《軍隊進行曲》(March Militaire)。這是他在幾個城市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讓年輕人從音樂中找到樂趣。
「我發現,問題是我們的工作的形象。人們認爲,我們是非常枯燥的人:從不說話,像機器人一樣,而且非常傲慢。(他們認爲)我們是精英。實際上,我們不是。我們只是一般人。當我們走入每一所學校時,這是我們需要改變的第一點,要鼓舞他們,然後說『看,我們是正常人。'」與學生的年齡更接近也會有所幫助:「許多父母說,『你能跟我的孩子說些什麼嗎?因爲如果你說什麼,他們會聽。'如果你從其他人那裏學到了優秀的知識,那麼與年輕人分享很重要。」
郎朗非常熱衷於努力普及古典音樂。對於一個每年以每場約5萬美元的出場費參加多達130場音樂會(這些數據發表於《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人而言,他仍花費很多時間走入校園。去年11月,他創辦了郎朗基金會(Lang Lang Foundation),以推動美國、歐洲和中國的音樂教育。他還是萬寶龍文化基金會(Montblanc Cultural Foundation)的主席,該基金會爲藝術贊助人提供1.5萬歐元,以捐贈給他們青睞的文化事業。
他這種對教育的關注並不意外。郎朗的自傳《千里之行》(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將於下週在英國出版,本書可能會被稱爲「與一千位老師的旅程」(Journey with a Thousand Teachers)。在他人生中的幾乎每一步,老師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1982年6月,郎朗出生在中國東北城市瀋陽。他的母親是一名電話接線員,父親是一名警察,但卻擁有音樂才能。郎國任拉過二胡,在郎朗3歲那年開始讓他彈鋼琴。4歲時,郎朗師從音樂教師朱雅芬。朱雅芬自己的老師在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時期自殺,當時西方古典音樂家曾受到學生們的嘲笑。她留給朱雅芬的遺產是巴赫和莫扎特(Mozart),然後朱雅芬又將其傳授給了郎朗。郎朗回憶道:「她是一位優秀的啓蒙老師。問題是,懂得如何演奏巴赫的中國老師並不是很多。她可能是中國最優秀的教授如何彈奏巴赫作品的老師。」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遺產。他解釋道:「許多老師都是在前蘇聯接受的俄羅斯曲目的訓練。」
朗朗的自傳
郎朗9歲時,他的父親辭掉工作,帶兒子來到了北京,因此郎朗纔有可能攻讀北京最具聲望的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父子倆每月依靠郎朗的母親從瀋陽寄來的150美元生活,他們住在一間冬天沒有暖氣的房子裏,他的父親晚上要先鑽進被窩,給兒子暖牀。生活很艱難,父子倆曾因爲練琴的時間發生激烈爭吵。一天他父親大發雷霆,歇斯底里地嚷道,郎朗應自殺,而不是給家裏抹黑,之後這個倔強的孩子4個月拒絕練琴。
郎朗的自傳讀上去像是華裔作家譚恩美(Amy Tan)的小說:父子間的矛盾終於化解,一位賣水果的人幫助了不快樂的孩子,並鼓勵他繼續彈琴。當時在美國任教歸來後,郎朗的啓蒙老師朱雅芬意外造訪父子在北京的家。她安排郎朗與一位教授合作,這位教授讓郎朗做好了在第二年夏季被中央音樂學院錄取的準備。
這部自傳詳細描述了他父親的憤怒和霸道,但卻獻身於他和他的媽媽周秀蘭。我說道,這部自傳最後的閃光點是父親對兒子的那種望子成龍式的愛,而非美國讀者關注的父親的憤怒。本書於去年在美國出版。「在西方,人們很難理解。但亞洲人卻對生活有著不同的理解。」
郎朗告訴我,他父親曾經告訴「一名(中國)記者,這本書讓他深受感動,因爲他認爲這表明我已長大。我感到很自豪,因爲他沒有感到傷心或有其它不舒服的感覺。」
1997年,15歲的郎朗得到了赴美、從師於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的獎學金,格拉夫曼自己的事業因爲他的手受傷而被迫中止。與其他在費城頗具聲望的柯蒂斯音樂學院(Curtis Institute)學習鋼琴的學生一樣,郎朗有了自己的一間公寓,他與父親合住,公寓裏還有一架7英尺斯坦威鋼琴(Steinway)。在來到學校的第一天夜裏,郎朗在睡夢中醒來,走過去摸了摸那架鋼琴,以確定這一切都是真的。「感覺就像是到了天堂,」他回憶道,往事似乎歷歷在目:「那是全世界最小的學校。整個學校就像是(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的一個班。在中央音樂學院,你會看到5個或6個人因爲一架小小的、愚蠢的立式鋼琴而競爭。要想彈鋼琴,必須先得到入場券。」
儘管擁有柯蒂斯和朱利亞音樂學院(Julliard)等名校,但郎朗表示,音樂教育的危機出現在美國,而非中國。倫敦和紐約的古典音樂聽衆似乎正迅速老化,而在臺北或香港,古典音樂聽衆的平均年齡有時似乎只有10歲左右,這可能反映了亞洲的進步。郎朗回答,在美國,預算赤字意味著「他們首先削減的是音樂和藝術開支,許多學校不再設立音樂課。沒有任何真正教授如何聆聽貝多芬(Beethoven)和莫扎特的培訓。(這好像是)你是一名學生,但卻不學雨果(Hugo)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你不可能指望,一位從未聽過古典音樂的人在30歲時突然開始去聽這樣的音樂。」
儘管郎朗技藝嫺熟,但他一直因爲演奏時有些「情緒放縱」而受到批評。從某種程度上爲了幫助剋制自己,他邀請指揮家兼鋼琴家丹尼爾•巴倫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以前也是一位神童——擔任他最新的導師。(郎朗在與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以色列音樂家首次會面時就向其請教。)郎朗每隔幾個月就會去拜訪柏林的巴倫博伊姆。「他教給我如何控制自己……不要讓情緒控制知識。但關鍵是,你必須有幻想,否則所有人彈的都一樣。」
午餐結束了,餐桌很快被收拾乾淨——蔥爆羊肉、中式炒雞蛋以及油炸饅頭幾乎都沒動過就被撤下了——,然後是一大盤外國水果,我們剛喫了一點,就到了郎朗該離開的時間了,他要稍事休息,然後參加當晚的音樂會。
與郎朗交談的話題漫無邊際,從北京在主辦奧運會後轉型爲一個外向型城市,跳躍到去年5月份的四川大地震。郎朗曾幫助組織了一場音樂會,爲受災者籌款。我問起了維權人士黃崎的境況——地震中,由於劣質校舍倒塌,有上萬名學生遇難,黃崎因支援其中一部分學生家長上訴而被捕。郎朗表示自己不知此事,從而略過了這一政治問題;作爲中國的一名超級明星,他可能認爲回答這個問題很不明智。
郎朗開朗的形象並未受到影響,開始講他以前的老師格拉夫曼(Graffman)的一件趣事。「我們在紐約時就住對街,並一起參加聚會。」郎朗用手機爲格拉夫曼的公寓拍了一張照片,併發給了他。格拉夫曼立即回電,「他說:『教我,教我(怎樣拍照)。'他確實很可愛。81歲了,還非常喜歡科技。」郎朗不費力就把美國俚語和不拘禮儀,與中國尊師的傳統融合在一起,這令人難忘。如果這就是全球公民之所指,那我們需要更多像他這樣的年輕人。
譯者/何黎
北京食堂(龐蒂厄(Le Bistrot de Pékin)Ponthieu)街38號,75008,巴黎,
玉米羹 2份 10歐元
中式豆腐 6.5歐元
燒茄子 8歐元
京醬肉絲 12.5歐元
蔥爆羊肉 11.5歐元
中式炒雞蛋 8歐元
北京薄餅 4歐元
米飯 2.5歐元
茉莉花茶 2份 5歐元
果盤 25歐元
小費 7歐元
總計100歐元

看著安吉麗娜•朱莉大步流星地穿過餐廳的樣子,就可以教會大家如何在公共場合不引人注目。她面無表情地目視前方,腰板挺得很直,走路速度無出其右,其他用餐者可能覺得只是瞟見了這位天皇巨星,但來不及再多瞧上一眼。
朱莉與Grill餐廳(位於好萊塢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旁)其他用餐者明顯不一樣,所以她一來我就知道了,雖說我坐在餐廳後邊,但她一走進來,我立馬就認出了她。她渾身上下一身黑色行頭——黑裙、黑褲與黑鞋——一頭棕色披肩長髮,一隻手拿著LV (Louis Vuitton)包。一溜煙功夫她就來到了我跟前,我茫然不知所措,慌忙從座位上起身作自我介紹。「嗨,」她朝我打招呼,並伸出手來與我握手,笑得那麼燦爛,差點兒沒把我弄暈菜。
我倆面對面在小包間坐定後,服務員過來問她喝點啥。我早到了10分鐘,所以嘛,已經捷足先登,品了一半的阿諾德•帕爾默(Arnold Palmer,一種加檸檬的冰茶)了——這是加州午餐的主食。她要了薄荷茶,並對我莞爾一笑。
她解釋選擇這個地方會談的原因是租用了攝影棚的一間辦公室,對自己執導的首部影片進行最後加工潤色。她首次自編自導了影片《血與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故事的背景是波斯尼亞(Bosnia)戰爭。這是一部小製作影片,所用的演員也都是些無名之輩,今天是電影后期製作的最後一天。「今天是個不尋常日子,」她說著,同時翻看著菜單。「我們的後期製作已接近尾聲,今天下午4點會宣佈影片徹底完工。封存後,就不再作任何改動了。」
花了一點兒時間,總算定下來午餐喫啥。除了拍攝電影外,今年36歲的朱莉有6個孩子,作爲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UN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的親善大使,她還有諸多人道主義事務。作爲聯合國親善大使,過去幾年她的足跡遍佈獅子山、巴基斯坦與厄瓜多(Sierra Leone, Pakistan and Ecuador)這些國家的難民營。
她沒有專門的公關人員,因此我倆這次會面是透過一位名叫大衛的神祕法國人,經過幾周的電子郵件與電話的溝通聯繫才最終敲定。「我既要告訴你好訊息,也要告訴你壞訊息,」有一天大衛對我說。「好訊息是朱莉明確答應了你的訪談請求。壞訊息是你得趕到馬爾他(Malta)去見她。」她的伴侶、影星布拉德•皮特(Brad Pitt)一直在歐洲拍片,她與孩子們要趕往那兒與他會合。
我們最終商定還是等她回到洛杉磯後再作訪談,這就是我倆緣何現在就坐環球公司(Universal)旁餐館的原因,這兒也是名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工作室、多家攝影棚以及衆多電視節目場景的大本營。在Grill餐廳的牆上,掛著環球公司發行的《羣鳥》(The Birds)與《黑湖巨怪》(The Creature from the Black Lagoon)等經典影片的鑲框照片。坐在Grill等朱莉時,我已經熟悉了一下餐廳環境,如今她已到場,我也就無暇再左顧右盼了。面對面看朱莉,她的美美不勝收,她笑的時候,晶瑩透亮的大眼睛閃著頑皮的神情,那對人所皆知的嘴脣中,露出讓人神魂顛倒的亮白牙齒。她很少接受訪談,所以剛開始對我存有戒備之心——尤其是當我提問她不願答覆的話題。比方說,她不想透露太多自己執導的首部影片,因爲她不想搶了首映式前媒體發佈會的風頭。但她迴避此類問題時,臉上露出狡黠的笑容,並聳聳肩膀表示抱歉,似乎想說,「對不起,這就是遊戲的組成部分」。
服務員端來茶後,朱莉給自己倒的茶加了點蜂蜜,我倆再次拿起菜單看。「這家餐廳有時有意大利麪,」服務員問我倆是否準備點菜時,她說道。「我要份帶雞肉的意大利麪。」我則要了加祖傳番茄(heirloom tomatoes)的烤鮭魚。
朱莉說這次出遊,她帶上了閨女們。她解釋說自己與皮特不管去哪兒旅遊都會把孩子們帶上,全家從不在一個地方逗留太久。「我們輪流拍戲,這樣就可以保證有一個人在家陪孩子。」可是,我倆這次會談時,他倆人天各一方。「這很難做到——我已經在洛杉磯呆了一週,彼此分離這麼長時間,這種情況很少見。我帶上閨女出遊,所以呢,我們組織的是一次特別的女士遊。男孩子們則跟著布拉德……他正在拍攝一部殭屍影片(《殭屍世界大戰》(World War Z))。」
朱莉與皮特的家恰似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縮影版。年紀最大的兒子馬多克斯(Maddox)快10歲了,2002年從柬埔寨(Cambodia)收養;扎哈拉(Zahara )6歲,出生在衣索比亞(Ethiopia);希洛(Shiloh)是這對伴侶生的第一個孩子,5年前出生於那密比亞(Namibia);帕克斯(Pax)於4年前收養,出生在越南;三年前,朱莉在法國又產下了一對龍鳳胎——諾克斯(Knox)與維維安(Vivienne)。「他們都很自豪自己母國的文化,同時又相互學習,」她說。「所以並不會出現男孩光學亞洲人的行事方式。每個孩子的牀頭都掛有各自母國的國旗,都有自己值得誇耀的地方。我們還沒去越南,因爲帕克斯有自己的計劃。扎哈拉想回非洲老家看看,希洛也一樣。所以每個孩子都能輪流做回東道主。」
朱莉今年去了柬埔寨,是爲LV拍攝一部廣告片,它由安妮•萊波維茲(Annie Leibovitz)執導。象LV這種奢侈時尚公司到柬埔寨這樣的窮國去拍廣告片,似乎顯得不倫不類,但拍不拍最終由朱莉自己定奪。「到柬埔寨實地去拍廣告片,並著力宣傳它的美景,這種事我樂意爲之,因爲這個地方太值得一遊,」她說。她與皮特在當地確實有幢別墅——「是幢面積不大的高腳屋」。她拍攝廣告的所得會悉數捐給該國慈善項目,她告訴我,依靠以馬多克斯名義建立的家庭基金會來開展相應的工作。「基金會致力於阻止濫伐山上森林、反盜獵以及清除地雷。我們都是以馬多克斯的名義做這些事,希望他長大成人後,屆時能接手。」
我們點的菜端了過來,朱莉的意大利麪很簡單,裏面有幾塊拌西紅柿醬的雞肉。但我點的烤鮭魚做工較爲考究,做成了寶塔狀,還帶有華麗裝飾的小茴香、祖傳番茄以及我叫不出名字來的蔬菜丁。整道菜看上去有點滑稽,朱莉看後,也忍不住大笑起來。
鑑於他們全球轉的地方很多,我不禁問她:家的內涵是什麼。「身在何處,何處都是我們的家。」那這樣是否感覺空落落的?「沒錯,但內心很愉快。我不習慣老是呆在一個地方,也不喜歡一天到晚坐在那兒。當初在學校,我可是個難以管教的學生。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去尋幽探訪……所以我特喜歡旅遊,覺得四處旅遊是培養孩子的最佳方式。」
聽到她提及自己的少女時期,不由得讓我想起她自出演中學生網路驚悚片《駭客》(Hackers)一舉成名以來,這15年裏她所發生的鉅變。想當初,她就象典型的好萊塢式放蕩不羈的孩子。她是名演員喬恩•沃伊特(Jon Voight)與瑪奇琳•伯特蘭德(Marcheline Bertrand)的女兒,自己說少女時期曾經自我墮落,30歲不到就已經有兩次婚姻——先是嫁給《駭客》中的搭檔、英國演員約翰•李•米勒(Jonny Lee Miller),第二次是嫁給了美國演員兼歌手比利•鮑勃•桑頓(Billy Bob Thornton)。她對刀情有獨鍾,身上刻了好幾處刺青,胸前戴著一個小盒,裏面盛著比利的血。
各種爭議伴始終隨著她的成名之路。2000年,憑藉在《移魂女郎》(Girl, Interrupted)飾演一位精神病病人的出色演技而榮獲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隨後憑藉在《古墓麗影》(Tomb Raider)中飾演勞拉•克勞芙特(Lara Croft)以及在《史密斯夫婦》(Mr and Mrs Smith)等影片中的角色成爲一流的功夫影星。正是在出演《史密斯夫婦》時,朱莉初次邂逅皮特,隨後這對伴侶逐漸成爲好萊塢的金童玉女,他們也隨之聲名日隆,拿他們的好友馬特•戴蒙(Matt Damon)的說法,達到了「恰似囚犯」的程度。媒體的窮追猛打毫無偃旗息鼓的跡象。去年,《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登載了一則假訊息,聲稱他倆正在鬧分手,他們一紙訴狀把對方告上了法庭;我問朱莉:對《世界新聞報》最近遭停刊是否感到哀傷。「我的確聽到了相關報導……可見我從不讀該報。所以嘛,實在難以知曉所謂的損失到底有多大。」
成年後,她生活中的一舉一動始終在公衆的關注視野內。但這次喫飯前,我從媒體瞭解到的朱莉與坐我對面這個坦然自若的朱莉儼然判若兩人。她說,爲人母改變了一切,尤其是她對演員生涯的看法。「對於能成爲一名演員,我始終抱著一顆感恩的心……但我覺得年輕時,我想不斷地拍戲。我想方設法想弄清楚生活中的各種疑問,所以呢,你發現自己出演的角色能幫助解答這些問題,並幫助自己成長。」
她解釋說,在過去幾年裏,自己與演職生涯的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好比是治病,」她說,並叉起長通粉與雞肉往嘴裏送。「有些角色讓人慾罷不能,因爲他們探究生活、愛情及自由中的種種問題。伴隨著你的成長,你總是拷問自己這些問題:我堅強嗎?我神智正常嗎?我理解愛情、瞭解自己嗎?」現如今,她補充說,「我已長大成人,對自己有了清晰的瞭解……作爲女人、成年人、以及站在家庭的角度,我如今並不太在乎角色能否幫助我解答這些問題,而是關心自己是否能解答這些問題。」我倆又談到了去年推出的影片《特工紹特》(Salt),安吉在其中擔任女主角,她過關斬將,出生入死於中情局(CIA)、特工處(Secret Service)以及一小撮兇惡的俄國間諜之間。劇中主角原先是爲男性所備,但在安吉表示願意出演後,劇情隨之就被改編。「那時我剛生完雙胞胎,」她回憶道。「我已經穿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睡衣了。當時穿著睡衣坐在醫院裏,我邊給孩子餵奶,邊讀劇本,慈母溫情湧上心頭……我快速翻看著劇本,都是些打鬥與槍戰的場面。我當時就覺得,『這正是我需要的,我想脫掉睡衣,好好拿槍過把癮。』我敢肯定,許多剛生完孩子的女人都認爲『稍微活動一下身子骨、瘋狂上一把……重溫一下原先生活的另一面是件美事。』」
她說自己要很久以後纔會考慮息影。「但已經不象過去那樣愛拍戲。我如今喜歡的是爲人母。」但很明顯,她對執導影片興趣正濃。「相比拍電影,我更喜歡當導演,」她說。我問她是否利用了之前與導演共事的經歷。「我覺得從所有導演(甚至那些我不喜歡的)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我絞盡腦汁想讓她損一番那些不喜歡的導演,但她禮貌地回絕了。她對邁克爾•溫特伯頓(Michael Winterbottom)讚不絕口,他執導的影片《堅強的心》(A Mighty Heart,自己在其中出演了角色)講的是記者丹尼•波爾(Daniel Pearl)的故事,波爾在巴基斯坦遭綁架,隨後又慘遭塔利班殺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也讓我受益匪淺,本人在他執導的影片《換子疑雲》 (Changeling)出演角色,他教會我如何發掘演職人員的優點,放手讓每個人去工作。我從未與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執導了影片《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與《社交網路》(The Social Network))合作過,但我把他當好朋友,看到他對待工作一絲不苟,對細節精益求精,是個工作狂——即便演員已經累趴下了——直至演滿意爲止。」
芬奇有望執導朱莉出演的下部影片《埃及豔后》(Cleopatra),但朱莉暗示將來影迷看到她出鏡的機率會越來越少。「隨著我與布拉德的年歲成長,我們打算少拍戲。這一行我已經幹太長時間了,布拉德也是如此……我倆也算功成名就,不想一輩子幹這一行,還有很多事等著我們去做。」
中國仍是她日程表上期望的探祕之地,她也希望能去緬甸(Burma)看看,「但目前的形勢不允許」,原因是該國仍處於軍政府的專制統治下。「還有伊朗,我很想去伊朗看看。」但她的夢想是「穿越撒哈拉沙漠,整個行程共需28天……必須得騎駱駝,我希望能一段一段分開走,這樣一路上就可以讓孩子們歇歇腳,」她若有所思地說。
我對她說,對於她們這個居無定所的家庭,這樣的計劃再理想不過了,隨後我倆站起身道別。雖然她湊過來親了親我的雙頰,但這一次我們沒再握手,隨後她快步走出餐廳(已經走得半空),走到陽光沐浴下的加州大街上,趕回工作地。
馬修•加拉漢是FT洛杉磯站記者
譯者:常和
阿諾德•帕爾默:2.50美元
熱薄荷茶:2.50美元
雞肉意大利麪:19.00美元
烤鮭魚:23.00美元
總計(包括小費):61.11美元

「當我想起勞動節時,我會想到中國人,你呢?」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發來這樣的資訊,暗示我在順利樓(Shun Lee)訂位子,它是一家位於上西區的餐廳,距離這位紀錄片電影製片人在紐約的公寓很近。於是我打電話,接待員在聽到我客人名字的時候,變得興奮起來。「邁克爾•摩爾?噢,他經常來我們餐廳,」他說。在這位美國最著名的煽動者,爲了擠進隔間裏我對面的高背座位,而把桌子往外推時,我把這個告訴了他,他從聖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帽子下面露出疑惑的表情。「我大概,一年來這裏三次。」
摩爾來紐約是爲了工作——他最近在寫一本傳記——也爲了「獲得一點私隱」。在他家所在的密西根湖畔的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他是公衆人物,不僅因爲他獲得了奧斯卡獎(Oscar)和金棕櫚獎(Palme d』Or),還因爲他在2005年發起了一個電影節,爲這座城市的經濟帶來了雪中送炭的刺激。當地由共和黨主導的商業協會提名他爲年度商人,對於這位左翼電影、電視和檄文文集——包括《資本主義:一種愛情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2009年),一部在危機後對大企業提出控訴的影片——的幕後製作者來說,這是一份出人意料的嘉獎,他十分享受其中的諷刺性。
他的新書《麻煩來了》(Here Comes Trouble)是另一種風格,其中集合了他憑藉《羅傑和我》(Roger & me)(1989年)成名之前的生活片段。他在這部片子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的大裁員對他曾經的家鄉弗林特(Flint)的影響。他曾因爲提問而被高中開除,羞辱過種族主義社交俱樂部,爲了報復一名施虐狂老師,在十幾歲就當選進入學校董事會,所有這些,只是爲摩爾後來製造的種種麻煩,提供了一點預示。
摩爾關於槍枝遊說(《科倫拜恩的保齡》(Bowling for Columbine),2002年)、伊拉克戰爭(《華氏911》(Fahrenheit 9/11),2004年)和藥品公司(《精神病人》(Sicko),2007年)的紀錄片,使他既成爲受美國左翼崇拜的英雄,也成爲被右翼妖魔化的魔鬼。不過他說,在特拉弗斯城,沒有哪一天是沒有共和黨人跑來與他握手或擁抱的。「我猜,他們是近水樓臺,可以把我當普通人來認識。我們都是美國人。我們在同一條船上。」
我問,這本書是否是爲了從更細微的角度展示他自己?他的回答讓我喫驚,他說,他更大的動機是,「追求一點修女們曾努力教給我們的東西——文學」。
和摩爾的許多作品一樣,這本書並不把非小說類文學作品的傳統定義當回事。《羅傑和我》毫不標榜客觀性,這或許令傳統紀錄片的製作者感到震驚,但摩爾認爲這樣才真實。不過,批評家一直用他的成功質疑他的資格。例如,《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就稱他爲僞善的「坐飛機到處亂逛的百萬富翁」、在「資產階級」郊外長大的「騙子」和受「對美國的憎恨」驅使的「賣國者」。
「如果你留意的話就會發現,這類攻擊從來不是來自工薪階層的,」摩爾回應道。「顯然,我現在過得不錯……當然沒喬治•克魯尼(George Clooney)那麼好。但是,讓我告訴你一個事實,當你是工薪階層的一份子時,你會希望脫離這個階層,」他說。回到家裏,「我只會聽到『加油,邁克』」。
按照摩爾的說法,順利樓是「紐約唯一不油膩的中餐廳」,內部燈光幽暗,以黑漆裝飾,佔據兩層方形空間,牆壁上蜿蜒著半透明的紅眼龍。在這個潮溼的假日星期一,只有幾桌客人。
在我四處尋找侍者的時候,摩爾說,他正在計劃寫第二本傳記,同時也在籌備新的電影,和一個「關於美國政治現狀的」項目——「電影、書、網路、舞臺表演、冰上表演,一切皆有可能」。更多細節他就不願透露了。
10年前,在世貿雙塔(Twin Towers)倒塌的那個早上,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正將5萬本《愚蠢的白人》(Stupid White Men)運往書店。這家出版社曾要求摩爾把對「竊賊中的竊賊」——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的批判改得溫和一些。他拒絕了,該書後來成爲2002年銷量最高的非小說類書籍,但時間沒有緩和摩爾對這位前總統的觀點。「布希政府頑固而不思進取,」他說:「而我們要花費餘生的時間來消除它的影響。」我問他是否對布希的繼任者感到失望。「我那天激動異常,投了[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一票,」他說,然後突然垂下眼睛,灰白的胡茬下,下巴鼓起來,雙臂抱在胸前。「我認爲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他的意願是好的,但是……」接下來是長時間的停頓。「我曾對他寄以厚望……以爲他會是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那樣的人物……多棒的作爲一位偉大總統而名垂青史的機會啊——可惜浪費了。」他看上去很難過。
他苦澀地繼續說道,共和黨人「決心把歐巴馬看作一個隱形總統」。摩爾就知道我會提到《隱形人》(Invisible Man)——這是拉爾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52年寫的一本關於種族不公正的小說。
我在餐廳掃了一圈,但沒有發現侍者。我問摩爾,你認爲歐巴馬是否會連任。他回答道:「這取決於誰與他競選。一些共和黨候選人非常瘋狂。他們認爲美國和他們一樣瘋狂。事實並非如此。假設有5000多萬美國人是瘋狂的,但這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有2億多選民。我們可以戰勝這5000萬白癡。」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開玩笑,但摩爾曾經遇到過白癡甚至更窮兇極惡的人。在2003年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之後,摩爾發表演講稱:「一個虛僞的總統……讓我們因爲虛假的原因發動了戰爭」。這番話讓他受到了威脅。當他寫到招募安全專家、「聯邦政府使用的前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隊員預防暗殺」時,聽起來就像一個妄想狂,但他在書中詳細描述了一系列未遂的襲擊活動——帶著刀具、「鈍物」和削尖鉛筆的暗殺者,並且抓獲了一個策劃炸掉摩爾住房的男子。
現在他仍然感覺到威脅嗎?摩爾垂下目光,再次雙臂抱在胸前。「現在沒那麼嚴重了,因爲美國已經改變……我不能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下」。
《麻煩來了》開頭引用了格林•貝克(Glenn Beck)的一段長篇大論。貝克口無遮攔的娛樂方式以及對右翼思想的鼓吹,與摩爾的左翼做法如出一轍。貝克說道,「我在考慮殺了邁克爾•莫爾」,如果這是一個玩笑,那也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玩笑。摩爾表示:「我爲他感到些許遺憾,我認爲他不怎麼樣。」
這種刻薄話似乎戳到了選民們的痛處,但摩爾辯稱,絕大多數美國人(即便是那些從未自稱爲自由主義者的人)都希望加強環保法律,降低高階主管薪酬和從海外撤軍。他表示:「我現在的政治思想屬於這個國家的中間派。」但美國人不會選舉中間派。我對這種說法有些意外。
他回答道:「恩,這是因爲金錢控制了選舉過程。」摩爾認爲資本主義是一個「作弊遊戲」。在這個遊戲中,400名最有錢的富翁控制的財富比半數美國人控制的都多。但「資本家階層」玩過了火,剝奪了中產階級的美國夢。
餐廳看起來非常空曠,尤其是侍者更少。摩爾認爲,明年美國大選可能的候選人有四位——歐巴馬、一個持主流思想的共和黨人、一個茶葉黨代表以及一個對歐巴馬感到失望的民主黨的傑出「左派」人士。我問道,你宣佈參選了嗎?摩爾對此感到意外,他迅速予以了否認。
飄然走過的一個侍者說道:「慢慢聊,彆着急。」我們已經交談了近一個小時,於是趕緊把他叫回來點菜。順利樓晚上有湖南牛肚、「酸辣腰花」和「獅子頭」等菜餚,但中午的菜譜較爲清淡。摩爾點了麻油雞和糙米,叮囑不要油炸,也不要太辣。
現在已經是接近下午兩點十五分,我感覺非常餓。我一直想點些開胃菜,但我像摩爾一樣保持了剋制,問侍者「天堂魚柳」是什麼東西。它其實是黑鱸炒菱角,聽起來相當不錯。出於趨同心理,我也點了糙米。摩爾只要了自來水,我也一樣。
我問摩爾,他喜歡談論的「普通工人階級」是否已經拋卻了摩爾式的政見,轉向了貝克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這些討茶黨歡心的人。聞聽此言,摩爾像是受到了侮辱。他說:「他們代表不了大多數。」他堅稱,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會把票投給蜜雪兒•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他們不會選一個瘋子。」儘管摩爾透過電影《華氏911》向布希發出了犀利的抨擊,但後者仍在2004年連任成功,而伊拉克戰爭也一拖再拖。因此我問他是否相信電影會影響選民。「當然,和每一個人都可能有關,」他答道。「在《精神病人》問世前,沒有人討論醫改……(但)一部電影或一本書只能起到導火索作用。」
我們的菜上來了——摩爾是一大份熱氣騰騰的雞肉,而我的是少得可憐的一盤魚、小蝦和雪豆。米飯碗看起來很小。「我看過報導,說你減過一次肥,」我問摩爾,很好奇爲什麼他只點了那麼點兒喫的。「一次?我這個型號的人,誰沒有減過幾十次,」他大笑道,將他的減肥計劃概括爲「管住嘴,邁開腿」。他補充道:「我來自中西部,在我的家鄉,我這號身材是正常的。這可不是好事兒。」
我開動起來,欣喜地發現一絲姜味,這時,摩爾提出了兩個理論,分析爲何英國人不如美國人肥胖。「你們是一個小島,所有東西都小一號:酒店房間,盤子……」他說道:「還有你們的足球。踢英式足球的話,大塊頭可沒有好處。」
在去了一次阿森納後,他愛上了英式足球,這時他突然唱起球迷編的歌來:「維埃拉,哦-哦-哦-哦,他來自塞內加爾,他爲阿森納效力。」他的歌聲響徹整個餐館。兩個國家對待足球的看法很能反映出兩國不同的文化。摩爾笑著說:「你們進一個球得1分,對吧。我們進球能得6分。」
摩爾在我們喫飯的同時還錄了一場棒球比賽,他說,自己和相識30年的妻子過著「非常傳統的生活」,每週日都去做彌撒。他抱怨許多左翼人士喪失了幽默感,並告訴保守人士,如果他們能關掉熱線廣播,去看看他的電影,「你也許仍不同意我的政治觀點,但你會知道我熱愛這個國家,也有良知,你也會發笑,因爲這些電影也確實很有趣。」他這番話真是樂觀得令人驚訝,接著他又就如何與對立黨派達成妥協提出了另一個建議。
「共和黨人會推選美國民衆喜愛的人(上臺),」他舉例說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阿諾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弗雷德•湯普森(Fred Thompson)。他說,民主黨人爲什麼不去提名湯姆•漢克斯(Tom Hanks)或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呢?「有什麼可擔心的呢?他們應該考慮馬特•達蒙(Matt Damon),而不是哈里•利德(Harry Reid)。」我介面道,或是邁克爾•摩爾?他急忙說:「哦,上帝,不。這可不是一個好主意。」
侍者開始收盤子了,同時問我們:「可以收了嗎?需要冰淇林嗎?」他還沒來得及滿懷期望地看一眼摩爾,摩爾就拒絕了他的提議。
我們起身準備離開,這時我提到,他的書中對於他年輕時的美國充滿了感傷的回憶,但批評起來又毫不客氣。摩爾的童年時代如田園詩般快樂美妙:在樹林裏打BB氣槍,在廣播裏收聽摩城音樂,牙醫與技工之間的收入差異不大;但那個時代也不乏汙點:種族歧視、敵視同性戀等等殘忍的行爲。「我熱愛這個國家,但這不意味著看見問題時保持沉默或裝作視而不見,」他說道。
我們走出餐館,還沒走出幾步,他就被一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學生給攔住了。「摩爾先生,我是你忠實的粉絲。非常感謝你所做的一切,」他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部iPhone手機,讓我拍一張他和摩爾的合影。當我們走到街拐角,更多的行人大聲打著招呼。摩爾看起來有些不自在,我們就此告別。他消失在百老匯的人流中,而我轉身走向一家三明治店,隨便喫點東西。
譯者/何黎
紐約西65街43號
麻油雞 24.95美元
Heavenly Fish Fillet 21.95美元
糙米 2份 3.50美元
總計(包括服務費):63.87美元
本文作者爲英國《金融時報》媒體編輯

從事藝術品交易的納哈邁德家族(The Nahmads)因三件事而聲名遠揚:第一是財富,福布斯(Forbes)估計其家族財富爲30億美元,據佳士德(Christie』s)紐約拍賣行總裁克里斯多佛•伯格(Christopher Burge)的說法,「該家族售出的藝術作品超過當今世界任何畫商」;其二是家族珍藏的畢加索作品;其三是他們的行事極爲詭祕,這種行事風格不但對其所收藏的藝術珍品(免稅存放於日內瓦(Geneva)機場專門的藝術品倉庫中)如此,而且還影響到與35歲的海利•納哈邁德(Helly Nahmad)午餐會的地點。他經營著家族在倫敦的畫廊;另一位與他同名的表兄——兩位的名字取自祖父希勒爾(Hillel)——則執掌著該家族位於紐約的另一家畫廊。
執掌倫敦畫廊的海利同意接受《金融時報》的採訪,因爲他剛剛在蘇黎士藝術之家美術館(Zurich』s Kunsthaus museum)首次公開展出了家族所藏作品。他選定巴黎作爲訪談地,並派他的司機到巴黎火車北站(Gare du Nord)來接我。繞了大半個巴黎城時,對方纔告知我喫飯的地方——麗圃咖啡館( Brasserie Lipp),它還是20世紀初法國講究藝術和文化修養時代(belle époque)的裝潢——熟鐵做的樹形燈以及陶瓷馬賽克依然保持原樣,想當初,普魯斯特(Proust)常在此買阿爾薩斯啤酒(Alsatian beer),海明威(Hemingway)也正是在此文思泉湧地寫出一本本小說。
只有常客纔能有資格就坐前室,但還沒等我驗證是否仍是傳統的就坐習慣(巴黎人坐裏屋,遊客坐樓上)前,身著休閒海軍套衫以及藍色開領襯衣的納哈邁德一頭扎進咖啡屋。他身材高大、圓臉、一雙藍色的大眼睛,一頭黑色的捲髮向後梳理,厚厚的眼鏡片後面是濃密的眉毛,他把手伸過那張貴賓專用的、位於正中央的桌子,差不多都能把我摟到懷裏——「我們來個熱烈擁抱」,同時親切問候服務員,嘴裏還恭維說「您的笑容真燦爛」。
他問我想喝些啥,我則說隨便。「可是你可能會不喜歡喝我點的東西!」他高聲說道,於是點了伏特加酒與橘子汁。我則要了一杯香檳,以慶祝他的畫展成功舉辦——全面展出了家族所收藏的100多幅藝術珍品,包括畢加索(Picasso)、馬蒂斯(Matisse)、米羅(Miró)、萊熱(Léger)、格里斯(Juan Gris)等的作品,它們平時「養在深閨人不識」,是納哈邁德家族的鎮館之寶——這些作品與衆不同,極其珍貴,一旦拍賣出去,就很難會再次在市場上流轉。
「偉大藝術家傳遞的最重要資訊就是他們能參透作品隱含的內涵——即真實的東西,」納哈邁德以此作爲開場白。「藝術家反對物質世界,就好比這些杯子,」說著他從桌子上取了幾個杯子,然後又把它們砰得放到桌上,「這些都是人造東西,只是幻象,麗圃咖啡屋也是如此,」他說得手舞足蹈,把旁邊桌子用餐的食客以及穿梭的服務員都吸引住了——「所有這一切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喜歡自己從事的工作是由於我們能近距離接觸藝術家所創作的人與物,而且可以說,『我存在於斯,這就是我真實的感受。』」
如此精闢定義現代主義藝術(家族財富倚仗於此)後,納哈邁德取消了伏特加酒,與我一樣,改而要了一杯香檳。「今天是10月24日,我很高興就坐在雅姬•武爾施拉熱對面,巴黎總是陽光明媚,我想在此呆上幾年。慢條斯理地感悟生活中的一切。」事實上,他語速很快,說得滔滔不絕。不時從他的話語中聽出一絲歐洲口音,但發音並不太準;納哈邁德的第一語言是義大利語,家族說的是法語。「我們都心知肚明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得相互珍愛!如果能達此境界,就能避免太多的分心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
當然,納哈邁德生性率真。他的父親以斯拉(Ezra)與叔叔戴維(David)出生於貝魯特(Beirut)的一個猶太家庭,家中既有拉比(rabbis),也有銀行家。上世紀60年代,10來歲的以斯拉與戴維移居米蘭,開始從事藝術品交易。在哥哥約瑟夫(Joseph)的保駕下,他們把畢加索與米羅的畫作綁至車頂,再從巴黎運至義大利。他們還有一個名叫艾伯特(Albert)的哥哥,不幸死於上世紀50年代的一場空難;約瑟夫曾經是個「紈絝子弟,如今卻是堅守清規戒律,與快樂的人呆一起時就會感到不自在」,他幾十年來一直是鬱鬱寡歡,納哈邁德說。
上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當時的藝術交易商並沒有如今高古軒(Gagosian)與豪舍和威爾特(Hauser & Wirth)這樣的實力,在全球各地擁有多家畫廊;它們都是在地化經營,多數僅限於坐鎮國內進行收藏,也沒有弗雷茲藝博會(Frieze)與網際網路可資利用。但納哈邁德家族的觸角遍佈世界——戴維移居紐約——以斯拉以歐洲爲基地,先是在倫敦,如今坐鎮摩納哥,所以家族可以從大洋兩岸不同的藝術差價中大收漁翁之利。
海利受教於倫敦的聖保羅學校(St Paul』s)及考陶爾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青少年時代大部分時間都徜徉於歐洲的各大博物館——「我是個精神分析師,不僅僅因爲我不像別人那樣欣賞油畫,我喜歡湊到跟前看,觀察那些稜邊倒角的地方」。1998年,21歲的納哈邁德就在梅菲爾區(Mayfair)開設了首家畫廊。
但藏品保管在倉庫中,意味著家族從來沒看到自己的藏品集中展出,直至他組織了這次蘇黎士畫展方纔算是圓了這個夢。「這次展覽將是遊戲規則的改變,讓我們看清楚潛意識中正在做的一切。畫作是證實我們存在的一種方式——所有的艱難與抗爭,恰似我們的家風——每時每刻都在不懈地努力。我從事這一行當已經15年了,家族之前幹這一行也已40年了——這次展覽就是全家族努力的結果,對此我倍感榮幸。我們這個家族既傳統又前衛——對流逝的一切,我們需要感悟及尊重,無論是基於價值還是傳統,過去的一切有其存在的道理。每個人的夢想就是能做成業界翹楚。」
然而,很少有藝術家能做到這一點。納哈邁德家族的成功在當今聒噪的藝術圈遭人憎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對當代藝術作品的公然鄙視。戴維•納哈邁德(David Nahmad)最近說這「基本上是胡說八道」,並提到了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的作品,他是位剽竊他人概念的藝術家,「都是些天價作品」。我問海利是否能苟同?
「沒錯,簡而言之,我認爲理查德•普林斯也並不希望自己的一生都耗在無聊透頂作品的創作上。所以,對有些人來說,他的作品物有所值,至於究竟值多少錢那是另一碼事。我們並不是傻子,理解了《萬寶路牛仔》(Marlboro Man)所蘊含的意義(普林斯翻拍了萬寶路香菸廣告中牛仔的形象),但我們需要預估其價值,若說它藝術價值等同於1890年的梵高(Van Gogh)自畫像,那就肯定有問題了。我們必須在題材的敏感性與表現手法的詩意之間相權衡,我們做出判斷的依據是堅信它有真正的價值。」
青少年時期,納哈邁德就購入達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畫作——「我花了2400英鎊買了他的「菸灰缸」(ashtray),倫敦上世紀90年代經歷的經濟蕭條,(看到菸灰缸)讓我有了切身的感覺。即便赫斯特的作品售價高達10萬英鎊,我仍然喜歡——但要是達到百萬英鎊呢?1百萬英鎊能買到一幅畢加索的作品。我不喜歡藝術作品過度商業化,也不喜歡大規模創作。我喜歡有濃厚藝術底蘊的作品,所以我不得不選擇退出。也許最終證明我是錯的,市場會消化掉所有新創作的藝術作品,但我還是覺得藝術的真實性最重要。我們家族取得成功是因爲我們始終與現實保持近距離接觸。我喜歡各種藝術作品,你可以買下這張桌子」——他做出抬的樣子——「並把它拿到威尼斯雙年展(Venice Biennale)上去展出,我敢打包票……」——他停了很長時間然後說——「這很有趣。但我們關注的目標是那些反映真實內涵的藝術家,並非那些操捷徑者。本質的東西要貫穿始終,就好比這家咖啡屋——最重要的是飯菜要好。來不得半點投機取巧。」
說到這兒,服務員來了。納哈邁德顯得很是詫異。「我們乾坐在這兒這麼長時間了,看來不點菜也能湊合——這樣一來倒可以成爲史上最便宜的午餐了。」然而,他瞧都沒瞧菜單,就要了兩道最貴的菜——鵝肝(foie gras)與法式幹煎塌目魚(sole meunière),看來這次我只能客隨主便了。
「如今大家一窩蜂地追求藝術品,而且附庸風雅之風日盛,所以都耐不住性子,也不管是否與未來的藝術發展方向相關聯,」納哈邁德繼續道。「如果你是個藏家,那麼藏品並不是你存在的理由(您並不靠此爲生),而它卻攸關我的生計,我不能犯致命錯誤。對我們而言,這就是現實生活,其他人正是由於我們(做出的合理估價)而喫了定心丸。這涉及到你能耐心等多長時間,我們能做到,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筆無價的財富。如果我財力不濟,或許會關注一下現當代藝術的動向,因爲等到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浮現時,我或許已經不在人世了。所以資金很重要,但生意絕不能光盯著錢。」
然而,資金充足可以讓納哈邁德憑籍無懈可擊的策略——低價喫進、靜觀其變以及現代藝術大師創作的作品日漸稀少——來抬高市場對藝術品的需求。「一般人都認爲:『海利•納哈邁德,你有的是錢,不屬於此列。』我想說:有品味的生活需要一定財力的支撐,在這之後,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我們家族中有人喫了經濟不景氣的虧,問題的關鍵是要時刻保持與人接觸。」
肥而不膩的鵝肝厚片,再伴以薄面包片與芝麻菜端了上來。「我們喫菠蘿這事,記得也要寫進你的文章!」納哈邁德說,然後再要了些香檳。我們喫的時候,他講了一則寓言:在猶太人贖罪日(Yom Kippur)那天,一個小男孩受命吹羊角號(喇叭)。他覺得自己難以勝任,於是邊吹邊哭,但沒想到卻受到了表揚,誇他吹得好,因爲他吹的時候「傷心欲絕,精神寓意是:王宮裏的鑰匙一般是各開各的門,但有一把鑰匙卻能把所有的宮門都打開,那就是悲傷的心。故事不錯吧?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就能暢行於天下——既不虛情假意,也不會過分自負。你若是堂堂六尺男兒,表現出悲傷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得慶幸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所有的人最終都難逃一死。小男孩的故事徹底驚醒了我,我們得批駁一下美國人的樂觀主義心態。」
納哈邁德家族的人結婚時都非常年輕——他的妻子生第一個孩子時才18歲,這是納哈邁德家族的傳統(他的母親生他時才17歲,生最後一個孩子時已經42歲高齡)——在我眼裏,納哈邁德就像個「六尺高的大小夥子」「那只是個託詞而已,」他爭辯道。「我們想讓一切顯得順其自然,不想讓人覺得我們付出了多大努力。」
「沒有經歷人生曲折的人一生平淡無奇。他們就好比是沒有調試好的樂器,因爲他們沒有經歷過悲痛。」 他補充道。猶太人是天才的商人(突出的例子是畢加索的經紀人——「頗具英雄氣」的畫商康維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或許原因是「藝術品交易讓人覺得深不可測,心情悲痛時,自己並不想說太多,但需要理解得更透。猶太人太需要理解爲何他們在20世紀遭受了這麼大的苦難」。
過完油的幹煎塌目魚與今年的新土豆一起端了上來,魚的刀功沒得說,上面還澆著汁。納哈邁德沒動蔬菜,直奔魚而去,但話題卻不離畫展。「在蘇黎士美術館所舉行畫展,當時爭論的焦點是畫商所展示的藏品是否屬於藝術珍品。如今,展出的作品已經衆人皆知,我們看到了強項所在,也看到了不足之處——但並不是有很多缺陷;也就是應該展出一幅蒙德里安(Mondrian)更棒的作品,也許還應該展出一幅梵高的畫作。現在應該會有很多人爭購這次展出的藏品。毫無疑問,我們會更加努力,讓這個展覽系列主題顯得更爲連貫,也更有震撼力。今年競拍萊熱畫作《靜物》(『Still Life』,納哈邁德家族最終以790萬美元拍得)時,我就想,『這是爲蘇黎士畫展準備的作品。』就像是爲博物館量身打造的一幅作品——等級超過一般藏家收藏的作品。畫展更讓大家覺得所有的展出作品爲一個整體——都是優中選優的作品。」
我問:畫展的最後一站放在哪裏?「我們準備在某博物館展出三個月,之後我們會感到很難過,因爲畫作將不再以整體爲單位展出,而是各自封存起來,但是,藏品將來的結局一清二楚——也許是在我們自己的博物館展出,也許是長期的出租。蘇黎士畫展後,我的電話就沒消停過,」納哈邁德說,「全球的博物館都爭相要求展出我們的藏品。毫無疑問,西方沒有哪位藏家能積聚這麼多的作品。」
正如他所說的,「我們不能喜歡什麼就買下。自柏林牆(Berlin Wall)倒塌(冷戰結束)以來,創造的財富是個天量——與其他畫商相比,我們算是資金雄厚。但我們是與財大氣粗的藏家競爭,對方輕易就能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他們鋪設輸油管道後,從北極地區大量開採石油;我們的家族資產雄厚,但比起從事油輪建造、採礦以及化工業的老闆來說,我們的實力實在不值一提。俄羅斯人、烏茲別克人(Uzbeks)以及擁有龐大中產階級與巨大財富的巴西人,在國際收藏界呼風喚雨。與我們一樣,你可能是藝術界最大的經銷商,但不幸的是,最好的作品(畢加索的作品之類)的買家並不是我們。打個比方,在池塘中,我們與鯊魚狹路相逢的話,我們逮到魚的機率是零——真能逮到的話,也得好好想想得付出多大代價。我不排除存在這樣的機率,但相比之下,對於這些富豪來說,就是少買一條遊船,少拿一幢豪宅,甚至都不值一提。」
我考慮把納哈邁德家族看作新時代的窮人,納哈邁德卻邊喝咖啡邊說:「我們的強項是以家族爲單位出擊。我們並不存在對跨國公司的忠誠度。我喜歡讓員工覺得像一家人一樣。在巴黎坐計程車時,我問司機喜歡些啥,對方回答說,『唱歌,』我說,『那您就唱吧!』他給我唱了一首頗爲動聽的歌。關鍵問題是對生計奔波時,得找到適合自己的事——如果某人自我覺得適合做汽車售票員,那他就能爲此心安理得。」
說到這兒,我看到此時的麗圃咖啡屋已經空無一人,這時一個報販走進來,向我們兜售《世界報》(Le Monde)——報上探討的是有關畢加索作品的買賣問題:納哈邁德家族是否依靠幾近過時的理念大發橫財?抑或是家族的成功戳穿了海利所謂「藝術成爲媒體關注焦點」的真面目?
「整個藝術品市場的成交額也許比不上一家汽車公司。據測,每年的交易量約爲150億美元,」納哈邁德說。「唯一能堂而皇之拿到市面上銷售、如同從廠裏製造出來似的就是當代藝術——它毫無限制,而且用工廠化流程,就可以製作出天價作品來。但消費者現在已經心知肚明這樣的事實:他們可以在網上購買作品,反過來很快就能把它出手,他們希望能找到作品的思想性。他們急需有價值、有確定思想的作品。」不一會兒他又顯得憂心忡忡。「自吹自擂總覺得不對勁,感覺自己是個狂妄自大的人。」我們談完後,我就付了飯錢,並再次表示很榮幸與他共進午餐。「真的嗎?」他追問道,這時我已經步出咖啡屋,走到聖日耳曼大街(Boulevard Saint-Germain)上了。
譯者:常和
三杯香檳:37.50歐元
2份鵝肝:42.00歐元
2份法式幹煎塌目魚:79.00歐元
麪包:6.50歐元
咖啡:4.50歐元
總計:169.50歐元

銀幕上有過很多經典的餐館戲。比如,影片《當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中梅格•瑞安(Meg Ryan)在曼哈頓熟食店裏假裝高潮那一幕,《教父》(The Godfather)裏阿爾•帕西諾(Al Pacino)在紐約布朗克斯區一家義大利餐館向一名對頭和壞警察開槍那一幕,甚至《五隻歌》(Five Easy Pieces)中傑克•尼克爾森(Jack Nicholson)努力說服一位頑固的女招待爲他單點一份吐司那一幕。
但說起讓人笑破肚皮的電影場景,沒有幾個能超越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西德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在1982年那部《窈窕淑男》(Tootsie)裏午餐會面那一幕。霍夫曼飾演一名不得志的演員,爲了獲得角色打扮成一名中年婦女的樣子,在紐約曼哈頓的俄羅斯茶室(Russian Tea Room)撞見了他的經紀人(由波拉克飾演)。霍夫曼飾演的那名演員捏著嗓子、用帶南方腔的女性嗓音與片中他的經紀人調情,然後突然換成正常的男性嗓音告訴他自己是誰。波拉克大喫一驚,馬上點了一杯雙份伏特加來壓驚。他說:「我的天,求求你有病治病。」
我與霍夫曼約好共進午餐。在等待期間,我想到了以上這一幕。霍夫曼選的是比弗利山四季酒店(Four Seasons)裏的Culina餐廳,《風塵女郎》(Hustler)創辦人拉里•弗林特(Larry Flynt)的那輛賓利照例停在酒店門口的固定位置,我小心翼翼地泊好車(避免蹭到那輛賓利),在停車員的帶領下走進酒店。
這位兩度獲得奧斯卡獎的電影界傳奇人物,在74歲時出演美劇《好運賽馬》(Luck),這是他首次出演電視劇。這部電視劇由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執導,講述賽馬界的故事,是HBO電視臺的最新影集。我早到了幾分鐘,在HBO預訂的包廂裏等了一會兒。曼和《好運賽馬》編劇大衛•米爾奇(David Milch)今天也要在那間包間裏接受採訪。米爾奇也是廣受好評的西部劇《戴德伍德》(Deadwood)的編劇。
霍夫曼出現了,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皮膚曬得很黑,銀色的頭髮筆直衝上,身著深色西裝和淺藍色T恤,顯得乾淨利落。我們直奔餐廳而去,路過擺在大堂裏的五顏六色的大型花架。霍夫曼走路慢而靈巧,瀟灑地制止了一名粉絲繼續訴說某次看到他打網球的事情。之後,經過片刻的猶豫(他有些緊張地問:「坐這張桌子行嗎?」),我們在四周激動的竊竊私語聲中落座了:就連四季酒店那些有錢的老主顧們也忍不住中斷他們的午餐,來搞搞追星活動。
一名女侍應來到我們桌前,我拿起酒單,默默祈禱霍夫曼會點酒(與FT共進午餐最近請的一些嘉賓點單非常節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霍夫曼點了酒——雖然不是葡萄酒。「我一喝葡萄酒就犯困,」霍夫曼用他獨特的沙啞嗓音對侍應生說,「我還是要一杯血腥瑪麗好了。」我點了一杯嘉維(Gavi)白葡萄酒。
Culina標榜自己的食物有「濃郁的加州義大利風味」(餐廳所在地是加州洛杉磯),不過,餐廳也提供很多類似壽司的意式刺身(crudo)。我們要了扇貝刺身、金槍魚和紅甘魚(夏威夷琥珀魚)手卷,我還點了明蝦和龍蝦沙拉。
等飲品的時候,我告訴霍夫曼,大約1年半以前、他剛剛拍完《好運賽馬》試映片的時候,我們曾短暫地透過電話。他皺起眉頭回想,但怎麼也想不起來。於是,我問他,從電影轉向電視劇有何感想。霍夫曼憑藉在《畢業生》(The Graduate)(1967)和《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969)中的出色表現而成名,在那個年代,電影明星都瞧不起電視劇。
「我趕上了好萊塢(Hollywood)的黃金時代,但我們當時並不自知。」霍夫曼說,「當時的大製片公司製作的一些影片,如今已不可能再由製片公司製作了。那時候我以爲自己永遠不會去拍電視劇。」霍夫曼說,電視劇已今非昔比;如今只有小成本獨立電影和資金充裕的付費電視臺(比如HBO)纔會冒險拍一些有創意的片子。「他們有的是錢,所以不會像一般的電視製作商那樣,讓你急急忙忙一天拍完20頁(劇本)。HBO給你充分自由,不做任何審查。你能自由發揮。」
女侍應給我們端來了飲料和刺身。「我以爲電視劇會跟電影有所不同,」霍夫曼抿了口血腥瑪麗之後繼續說,「但卻沒有,因爲導演是電影導演,而且我們每天只拍四五頁劇本。」
《好運賽馬》上月在美國開播、下週將登陸英國Sky Atlantic頻道,劇情圍繞南加州一個賽馬場展開,描述了騎手、訓練師、馬主、賭徒等各色人羣。《好運賽馬》一劇系出名門:試映片由邁克爾•曼執導,他曾執導《盜火線》(Heat)和《借刀殺人》(Collateral)。霍夫曼說,全劇導演邁克爾•曼和他指定的分集導演們奠定了《好運賽馬》一片的基調。「所有演員都夢想與他合作……爲力求表演真實,他讓你『沉下去』(編者著:原文爲「 to go 『under』」),而很多導演可能會讓你撕下牆紙(編者著:原文爲「to pull the wallpaper down」)。」我問是什麼意思。「他希望演員的表演更貼近生活,」霍夫曼說,「演員說『用力』演(編者著:原文爲『pushing』)……(但)沉下去,意味著要讓人不覺得你在用力演。」
霍夫曼在《好運賽馬》中飾演Chester "Ace" Bernstein,一名剛剛出獄的意志堅強的前書商。這個角色給了他一個少有的挑戰:要分12集來表現一個角色。「在劇院裏,經過3周的彩排之後,你或許會說:『啊!我找到感覺了。』而如果你拍電影拍到第3周時說:『啊!找著感覺了!』導演會看著你,說:『不錯,不過你得跟前3周的表演保持一致。』你不能改變人物性格,因爲你不是在連續拍攝。而《好運賽馬》是部電視劇,它的劇情是不斷推進的,我們在之前表演的帶動下向前走,拋棄不受歡迎的部分。」《好運賽馬》第二季已獲續訂。
霍夫曼的電影生涯始於在《畢業生》中大放異彩的演出(飾演本傑明•布拉多克(Benjamin Braddock)),但他險些沒有接演這個角色。「那個角色是爲羅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寫的。」霍夫曼回憶道,「書中對這個角色的描述是,淺金色頭髮,一名帥氣的田徑隊員。我告訴(導演)邁克•尼科爾斯(Mike Nichols):『我覺得我根本演不了這角色。』」即便是被尼克爾斯說服、接演這個角色之後,拍攝早期的反應仍然很糟。「每一場拍攝之後,都有人去找製片人拉里•特曼(Larry Turman),說:『真可惜,你這部片子這麼好,卻選了個不合適的人演主角。』」
在《畢業生》中,霍夫曼扮演的角色被安妮•班克羅夫特(Anne Bancroft)扮演的羅賓遜太太(Mrs Robinson)勾引。這部電影后來成了那個時代的代表影片之一。不過霍夫曼說,他並不是特別喜歡當時的經歷和之後的反響,他說如果沒有得到《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中的那個角色,恐怕會迴歸戲劇舞臺。「《畢業生》得到的評論中有一些措辭猛烈,讓我十分驚訝。我幾乎覺得其中的一些評論是蒙面的反猶言論。比如『大鼻子』、『很高的鼻音』、『怎麼能想像這個長相搞笑的矮個子猶太人扮演本傑明•布拉多克(Benjamin Braddock)呢?那個角色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Wasp)的特徵十分明顯啊!』」他說,應當感謝尼科爾斯。「他沒有服從角色安排……這是他想證明的事情之一。」
這時我的沙拉快喫完了,霍夫曼飛快地喫完了剩下的幾塊意式刺身。侍應生走上前來告訴我們,還剩兩盤菜。不過霍夫曼已經喫飽了,所以侍應生把菜上到了我面前。
我問他在演藝生涯中的其它時期,有沒有遭遇過反猶主義。他沉默地思考了片刻後說,「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投射,還是現實……」侍應生回來時,又打斷了霍夫曼的講述。她又往桌上放了幾盤扇貝和金槍魚,旋即靜靜地飄走。霍夫曼又沉默了。片刻之後,他說:「我也不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一個電影明星代表著社會中的一大部分人。因爲你總希望讓走進電影院的人裏,有儘可能多的認同那個角色。世界上有60億人,只有1700萬猶太人,這麼一算就明白了。選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或喬治•克魯尼(George Clooney)肯定不會錯,可是換一種安排就相當於賭博了。」
大多數人都以爲霍夫曼是紐約人,但實際上他在1937年生於洛杉磯。他的父親是一名傢俱推銷員,一家人總是搬家。霍夫曼回憶道:「中產階級的下層總是在向上看。他是個推銷員,總是嘗試以超過自己生活水準的方式生活。在我人生的頭十八年,在六個不同的地方住過,因爲他總是想向上挪,但又付不起房租,所以我們又得回到當初本來就不應該離開的地方。」
霍夫曼對紐約一直都有一種嚮往,他的這種嚮往是看過《東區少年》(East Side Kids)後產生的。這部20世紀40年代的黑白系列電影講述的是曼哈頓的出租公寓中,一羣吊兒郎當的小夥子的故事。他說:「我在星期六的日場電影看到他們以後,就感覺只想成爲他們那樣。」
直到1958年,霍夫曼才第一次到紐約。「一架螺旋槳飛機整整飛了13個小時。我當時大概20歲,我記得從機場坐巴士到了……」侍應生又過來收走了盤子。「我來把這幾個放到那兒,」霍夫曼邊說邊把自己盤中的兩個手卷放到我的盤子裏。他對侍應生說,「別告訴他我是用手指拿的」,把侍應生逗樂了。
「總之,我在第二大道和34街的路口下了車,在街對面,我的正前方,有個傢伙正在往巴士輪胎上撒尿,人來人往衆目睽睽。我還記得我當時的第一反應,」他說到這裏頓了一下。「當時我覺得,『到家了。』從那時我就愛上了紐約。」
霍夫曼對紐約的愛在1970年很險地逃過一劫。當時左翼極端組織「地下氣象臺」(Weather Underground)的幾名成員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意外地引爆炸彈,把自己炸死了,剛好就在霍夫曼家隔壁。
「第二天我上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頭版,上嘴脣上是爲一部電影蓄的鬍子,手裏拿著從家裏搶出來的油畫,還有烏龜。我把烏龜放到了口袋裏,可是它們只活了一個星期。在我原來放桌子的地方,炸開了一個巨大的洞。」我說,本來可能會有十分不同的後果的。他用低沉、渾厚的聲音哈哈大笑。「是啊,演藝生涯會短一些。」
霍夫曼的演藝生涯繼續前進,總共贏得了七項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最近一次是1998年因爲政治諷刺片《搖尾狗》(Wag the Dog)。他第一次獲得提名是因爲《畢業生》,隨後又因爲《午夜牛郎》再一次獲得提名,但兩次都並未獲獎。「強•沃特(Jon Voight)也因爲《午夜牛郎》得到提名,但是得獎的是(《大地驚雷》(True Grit)的主角)約翰•韋恩(John Wayne)」,他眼睛看著我,很有心機地沒有再多說。在1979年,他終於因爲在離婚電影《克萊默夫婦》(Kramer vs Kramer, 1977)中的角色,拿到了小金人。後來又因爲在《雨人》(Rain Man, 1988)中扮演患有孤獨症,但又具有數學天才的雷蒙德•巴位元(Raymond Babbitt)時的出色表演再次獲獎。
我問他最享受扮演哪個角色的經歷。「我覺得任何一個角色都不算有趣,因爲你永遠都不知道能不能演得成功,你會時不時地覺得自己某一點做的不錯,感覺找準感覺了。可是我參加過自己演過的電影的首映,比如《畢業生》,再比如《雨人》。所有大腹便便、衣冠楚楚的人都來看首映,可是等電影放完後,他們就擺出這樣的臭臉,」說著他擺出一副痛苦的表情。「你覺得自己演砸了。但其實那只是因爲一幫錯誤的人,因爲一個錯誤的理由,來看首映了。」
與此相反,他說,他的首部導演作品《四重奏》(Quartet)最近剛剛殺青,劇中瑪吉•史密斯(Maggie Smith)、湯姆•考特尼(Tom Courtenay)、比利•康諾利(Billy Connolly)和寶琳•柯林斯(Pauline Collins)飾演一羣退休的歌劇演員,這部電影的拍攝是一段令人精疲力竭的經歷,但他十分喜愛。
霍夫曼該走了。「你永遠都不知道一部電影能讓你得到什麼,」他說著開始講最後一段故事,和《克萊默夫婦》的導演羅伯特•本頓(Robert Benton)重新聯手拍攝《勝者爲王》(Billy Bathgate, 1991)時的事情。「我們在北卡羅來納州拍攝,有一套全明星陣容,有一個拿過奧斯卡獎的編劇型導演,我們都以爲自己拍的是一部藝術作品。就在隔壁,離我們幾百碼的地方,在拍另一部電影。那部電影的名字我都叫不上來,所以就問,『那個破爛兒叫什麼來著?』」他說得很慢,彷彿是因爲發音讓他很爲難。「忍……者……神……龜。我們那時覺得自己多麼牛逼啊!可是那部片子被捧上了天,我們的電影卻被反響平平。」
霍夫曼站起身來,問我:「你還滿意吧?」我說,滿意。他說:「那就好。我真的想起來你當時給我打過電話了,那次我們聊得不錯。」然後他微笑著和我握過手,就離開了。
作者馬修•加拉漢(Matthew Garrahan)是英國《金融時報》駐洛杉磯記者
譯者/何黎
地址:Four Seasons Hotel Beverly Hills, 300 South Doheny Drive,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48
意式手卷,2份,24.00美元
意式金槍魚刺身,2份,24.00 美元
意式紅甘魚刺身,3份,36.00 美元
意式三文魚刺身,2份,24.00 美元
意式扇貝刺身,3份,24.00 美元
明蝦、龍蝦、蟹、鱷梨沙拉,29.00 美元
血腥瑪麗,19.00 美元
一杯嘉維白葡萄酒,14.00 美元
總計(含稅和服務費):230.55 美元

集模特兒、演員、導演於一身的伊莎貝拉•羅西里尼(Isabella Rossellini)是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與羅伯託•羅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女兒,一生多數時間生活在衆目睽睽之下,卻不喜歡被人評頭論足。
她不喜歡被人評判、不喜歡爲自己辯護、不喜歡上紅地毯拋頭露面、也不喜歡(當然不喜歡)接受採訪。但她喜歡動物、各種昆蟲以及它們稀奇古怪的繁育方式,這倒是個不太遭人待見的話題。
我發現她的這一點是在很早之前的一次見面會,地點就在莫薩酒店(Mercer),這是SoHo區的一家酒店,按照本人以往的經驗,幾乎每個時尚達人都希望被記者採訪。但與馬克•雅可布(Marc Jacobs)及阿爾伯•艾爾巴茲(Alber Elbaz)這些時尚名流不一樣的是,我與伊莎貝拉•羅西里尼卻是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會面,她沒在大廳裏就坐,要知道,這兒是名流薈萃之處。說實話,雖然她是個紅得發紫的名模,但稱呼其爲「時尚名媛」也許有些誇大她對時尚圈的興趣。
相反,她選擇了咖啡區酒吧角落一個毫不起眼的小長椅,那兒的裝飾風格與其說是突出高檔時裝,倒不如說是爲了服務高級食客。她走進來,身穿深藍色套裝褲,上身穿著深藍及白色條紋T恤衫,瞧見我已就坐,就徑直用腳後跟站定,並隨手抽把椅子坐下來,周圍是否有別人用餐,她一眼都沒瞥。但那天是週四,於是決定不單喫午餐,而是早餐午餐放一頓喫。週四上午11:30時,即使在莫薩酒店,早餐午餐擱一塊喫的人以及盤桓於酒店、向名人暗送秋波者也是廖廖無幾。
她說自己不喜歡在紅地毯上拋頭露面的說法不攻自破,原因是:雖說60歲的羅西里尼聲稱 「自己從根本上說,已經退休」,但任何最近讀過時尚雜誌者都知道她是珠寶品牌寶格麗(Bulgari)今年秋冬季的形象代言人。我倆會面時,她不時炫耀手上戴的寶格麗手錶,只能說明這個身穿簡單T恤與套裝褲的女人個性中可能還有魅力十足的另一面,而不是象一開始所展示的那樣。她還在剛剛公映的兩部電影裏擔任主演——第一部是2011年的《大愛晚成》(Late Bloomers),該片由名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 Gavras)的女兒朱麗(Julie Gavras)執導,伊莎貝拉與威廉•赫特(William Hurt)在片中扮演一對夫妻,講的是兩人人到老年相濡以沫的故事;另一部是加拿大導演蓋伊•馬丁(Guy Maddin)執導的《鑰匙孔》(Keyhole),她在片中飾演傑森•帕特里克(Jason Patric)的亡妻(但仍是很關鍵的角色)。她還在紐約主持了爲保護威尼斯遺產基金會(Venetian Heritage)籌款的特別活動,該基金會旨在修復威尼斯的藝術與建築,並幫助加固威尼斯城池的陸地(羅西里尼的父親有一半是威尼斯血統,雖然她本人在羅馬長大)。
在籌款活動中,播放了由圭多•託洛尼亞(Guido Torlonia)執導、理查德•基爾(Richard Gere)與蒂爾達•斯溫頓(Tilda Swinton)解說、介紹義大利電影導演呂切諾•維斯康第(Luchino Visconti)生平的話劇。羅西里尼還專門作了簡短致辭,還得耐著性子竭盡全力做好宣傳活動。上述所有活動中,沒有一項真正能與「退休」扯上關係。
. . .
「拋頭露面上紅地毯儼然成了另一門行當,」點完菜後,羅西里尼這樣說。她爲自己點了一個山羊乳酪煎蛋與新鮮橙汁,我則點了混合漿果,我打算一次喫一個,以便延長我倆的會談時間,就象正常用餐時間那麼長。
「第二天,電視節目、雜誌大肆報導,全是『您對那件裙子喜歡與否?』以及『她看上去胖了嗎?』之類的內容。不斷借穿贊助商的裙子與佩戴其珠寶似乎成了我的全職工作。我必須生活在如夢如幻之中,而這我永遠無法企及,所以總是感到很鬱悶。當名人很累不容易,遠遠超出演電影本身,有時付出與回報成正比,有時卻並非如此。我記得1986年拍《藍絲絨》(Blue Velvet)時,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剛從戒毒所出來。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未曾謀面,因此見面都說,『哎喲,見到您真高興,您可是個大腕,』他則說,『大腕,什麼大腕:誰給我買單?』」
說到這,羅西里尼突然捧腹大笑,笑得整張臉都皺成一團了。她老是這樣笑,舉個例子,當她打算要份檸檬汁時(本人當時正喝),我則對她說:我點了一份壓榨檸檬汁,把服務員整得雲裏霧裏,對方一個勁地問我要的是不是檸檬汽水(保羅•紐曼(Paul Newman)生產的那種有機飲料),並勸她也許應該點橙汁,聽到這,她捧腹大笑起來。
說到檸檬汽水時,她對我說,「有一天,我去逛一家大超市,一個貨架上擺的全是保羅•紐曼的產品,只不過他的形象各異:有墨西哥版、有義大利版、還有法國版。這樣做很弱智,但你知道,他女兒是這一切的幕後操盤手,運籌帷幄出了這個商業巨無霸。我老買檸檬汁與狗糧,因爲它們都屬於有機食品,但從不買色拉調味汁,你知道……我可是義大利人。」她又哈哈大笑起來。
五年前,羅西里尼離開紐約市,她1979年與電影導演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結婚後,一直在那居住,他倆於1982年離婚,她後來又嫁給喬恩•維德曼(Jon Wiedemann),並生下了女兒埃蕾特拉(Elettra),兩人又於1986年分手。她移居長島(Long Island),部分原因就是想躲避明星那種生活,過自己淡泊平靜的生活。她指出自己母親也是如此,離開好萊塢(Hollywood)回到歐洲生活,就是躲避沒有任何私隱的美國名利生活。
在長島貝爾波特(Bellport),羅西里尼爲導盲犬基金會(Guide Dog Foundation)飼養導盲犬——她在鄉間精心照料、其演員搭檔琳達•拉金(Linda Larkin)則在城裏飼養導盲犬——一旦狗兒成年,就交由新主人收養。羅西里尼近日購買了30英畝土地,這塊地原用於樓市開發,沒想到隨後經濟危機重挫了房地產業,她目前正在申請把該地變成農場。她說自己如今多數時間都花在「農場小型會議」,正與當地政府機構進行洽談,自己只是偶爾進城。
然而,不管她願意與否,羅西里尼依然是大明星,不是由於她那張被人津津樂道的亮麗臉龐,而是她的所作所爲;她依然我行我素、離經叛道——尤其是好萊塢那一套。經營農場只是展示其性格特點的冰山一角;她還是位在麪包上抹黃油的明星。上次與明星或模特兒同進餐,對方不但當衆喫麪包、而且當衆塗黃油,本人已經不知道是猴年馬月。
「哈,」她輕蔑地說,把塗抹黃油的麪包塞入口中,此時她點的煎蛋端上來了。「那些人(我猜她指的是那些喫麪包不抹黃油者)斷言我的演職生涯27歲就終結了。」想當初,她的演職生涯基本上還是在影視劇中飾演跑龍套的角色,其中就包括在她母親1976年主演的影片《花落花開》(A Matter of Time)中飾演一個小角色。事實上,她的演職生涯纔剛剛拉開序幕。
羅西里尼28歲步入模特兒生涯,當時她的朋友、攝影師布魯斯•韋伯(Bruce Weber)問她是否願意爲英國《Vogue》雜誌拍攝封面照片,事後她與化妝品公司蘭蔻(Lancôme)簽了一份爲期14年的合同(諸如此類的美事不勝枚舉)。40歲那年,蘭蔻單方面中止了合約,她公開表示譴責,此事一度鬧得沸沸揚揚。她在大衛•林奇(David Lynch)執導的《藍絲絨》中首次飾演主角,此後又先後飾演了《親親表妹》(Cousins,1989年)、《飛越長生》(Death Becomes Her,1992年)以及蒂娜•費(Tina Fey)的《搖滾三十》(30 Rock,2007)電視連續劇。
. . .
雖然她出了名地長得漂亮,但她臉上絲毫沒有塗抹化妝品後留下的常見跡象——臉上是老年女性的那種皺巴巴皮膚,腰圍也已變粗變圓。相比演電影,她似乎更喜歡模特兒這行(或者說,相比出演大影片,自己至少更喜歡出任知名化妝品牌的模特兒),原因或許是沒人希望模特兒清晰說出內心的動機,模特兒只需按部就班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是,也許意識到自己的模特兒生涯不會長久,六年前,羅西里尼涉足另一項職業——先是自己寫劇本,然後是自己執導短片。她的首部影片是2005年的《我的父親100歲了》(My Dad is 100 Years Old),該片由蓋伊•馬丁執導,她寫此劇本是紀念自己的父親,並親自出演,在片中分別飾演費里尼(Fellini)、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以及大衛•塞爾茲尼克(David O Selznick)。該片隨後被羅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的聖丹斯(Sundance)頻道買下,再之後,雷德福本人決定拍攝幾部網路小短片時,給羅西里尼打電話,對方建議拍攝一部系列片,分別介紹不同昆蟲的性生活。
「從根本上說,本人希望拍攝喜劇片,因爲可以從中學到一些知識;我對昆蟲感興趣,原因是它們遠離人世生活:它們是雌雄同體,或者說能改變性別,」她說,把麪包嚼得格格響。這部系列片取名《Green Porno》,羅西里尼在片中把自己裝扮成蜜蜂、家蠅等動物;她隨後又拍攝了一部名爲《Seduce Me》的系列片,介紹海洋生物如何繁育後代的故事。2011年,她還爲Discovery頻道製作了一部名爲《動物擾我注意力》(Animals Distract Me)的長片,介紹都市動物的一天生活。如今她正拍攝製作另一部介紹動物的母性本能的系列片,爲此,她說自己閱讀了雌性生物方面的大量材料。
「生物學中最重大的問題是探究利他性的起源——即願意爲別人(甚至可能傷及自己)做出一定犧牲——達爾文(Darwin)推斷根源可能是母性本性——甘願爲自己的後代犧牲自我,」她說,並用叉子叉起一塊炒番茄。「但是,你若觀察動物,就會發現有些母親會喫掉自己的幼崽,有些動物則任由它們死去,所以還不能如此倉促下結論。」
. . .
當羅西里尼開始考慮拍攝介紹動物生活的影片時,她重新回到學校讀書——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攻讀動物研究方面的學位——她將於明年五月畢業。「我想拍攝生物方面的影片,我覺得自己需要『充電』,」她說。事實上,我倆在莫薩酒店會面的原因與時裝毫不相干:酒店離紐約大學很近,會談結束後,她還要急著趕去上課。有趣的是,她女兒埃蕾特拉(目前是模特兒)剛剛從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獲得生物醫學方面的學位(羅西里尼還收養了一個兒子羅伯託,今年正好19歲)。
對於自己作爲成年人重回學校讀書,羅西里尼顯得異常興奮。「年齡大了重回學校讀書,效果要好得多,因爲自己知道需要什麼,自己想學什麼,也知道自己學習的原因,」她說,這時服務員走過來端走了我倆的盤子。羅西里尼不想喝咖啡,但要了蘇打水。
「你知道,上世紀50年代,我在義大利生活時,基本上是自耕自種,」她說。「當時食物很重要,農產品非常重要。大家都是自己榨橄欖油,我移居美國後,花了很長時間才整明白多數美國人遠離食物生產地。我的意思是:小時候,復活節(Easter)喫羊肉前,我才知道羊是啥東西——儘管家裏人不說這就是同一頭羊。我總以爲紐約漢普頓斯(Hamptons)所有居民都有自家菜地,嘿嘿!」
在她長島自家農場裏,她打算自己種蔬菜、水果及養雞;養更大的動物,農場面積有限。讀完紐約大學的學位後,她考慮繼續深造,以瞭解各種有害的昆蟲。她的農場還僱了一些年輕小夥種地,其中一位還想要一頭馬用來犁地,因爲動物對錶層土的破壞要比金屬犁小得多。
「我買地、並希望把它改成農場的訊息剛被公之於衆,年輕人(通常受過良好教育)就不斷聯繫我,這讓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羅西里尼說。「我們年輕時,若是受過良好教育,就想去城裏,不願當農民,但如今的年輕人很關心環境與食品,對他們來說,當農民只是選擇了另一種生活方式——與當藝術家或技工相似,這是觀念的改變。」
「技工」——羅西里尼喜歡這樣自稱,她爭辯道,若當了「技工」,別人評判依據是你的勞動與生產的產品、而不是你扮演的角色,當然也不是你代言的形象。這就是爲何她總把工作重心偏向獨立影片拍攝,而且這還需要「不斷學習」。
這就是她爲何拍攝《大愛晚成》以及喜歡與先鋒派導演馬丁合作的原因——「我對拍攝老年人的喜劇片很感興趣,而它們通常被視爲悲劇片,而非喜劇片,」她說,她與馬丁已經合作拍攝了五、六部影片,如今還共用了很多演職人員。(他倆的首部合作影片是2003年的《悲歌之王》(The Saddest Music in the World),片中羅西里尼傳神地飾演了海倫•波特-杭特利男爵夫人(Lady Helen Port-Huntley),一位失去雙腿的啤酒店老闆娘。)
「我與蓋伊合作時,拍的與其說是影片,倒不如說更象是裝置,」她說。「它們既能在博物館放映、也可以到劇院播映。蓋伊甚至可以製作出一部帶有生動對話與現場樂隊的無聲電影。因爲投資額不大,拍攝獨立影片時,可以進行大膽嘗試。然而影片的投資構成還是頗爲複雜。」她嘆聲說道。「這就好比拯救威尼斯。」或者說也類似於偶爾參加訪談節目。
她搖搖頭,站起身來,對我笑了笑。「我得趕去上課了,」她歡快地說道。她就這樣趕去上課了,去播灑思想的種子。
範妮莎•弗瑞德曼是《金融時報》時尚主編
羅西里尼生平年表:
1952年6月18日出生於羅馬;
1971年入讀紐約芬奇學院(Finch College);
1976年:出演首部電影《花落花開》;
1979年與斯科塞斯結婚;
1980年:布魯斯•韋伯爲英國《Vogue》封面拍攝其寫真,比利•金(Bill King)則爲美國《Vogue》封面拍攝其寫真;
1982年,成爲蘭蔻形象代言人;當年8月,其母親去世;同年11月,與斯科塞斯離婚;
1983年:嫁給來自德克薩州的男模喬恩•維德曼(如今是微軟高階主管),並育有一女埃蕾特拉;
1986年:在大衛•林奇執導的《藍絲絨》擔任主演,飾演一位意亂情迷的歌手,同年與維德曼離婚;
1992年:客串麥當娜(Madonna)的音樂電視《Erotica》;
1994年:收養一位男孩、並以其父親名字取名爲羅伯託;
1995年,推出自己的化妝品牌Manifesto;
1996年:在一片爭議聲中與蘭蔻解除合同;
1997年:撰寫半虛構傳記《Some of Me》;因在《綁票疑雲》(Crime of the Century)中的出色演技而獲金球獎(Golden Globe)提名;
2008年:她拍攝的《Green Porno》系列短片在聖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上放映。
彙編者:彼得•雷加特(Peter Leggatt)
譯者/常和
檸檬汽水:5.00美元
橙汁:7.00美元
山羊乳酪煎雞蛋:14.00美元
混合漿果:6.00美元
聖沛黎洛礦泉水(San Pellegrino):7.00美元
總計(小費計入):39.0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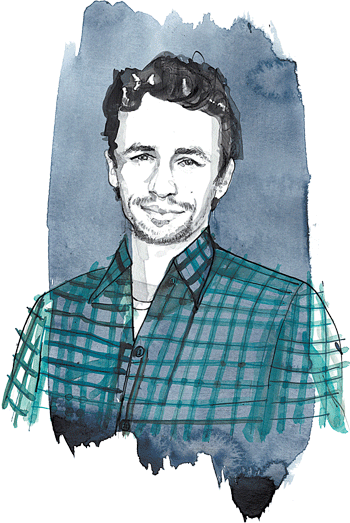
柏林的冬天嚴寒異常,卡爾馬克思大道(Karl-Marx-Allee)上空飄落著零星雪花。寬闊的道路兩旁,鱗次櫛比地矗立著豪華樓宇,它們都是拜前民主德國(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堅定不移地實行共產主義政策所賜。但與所有城市一樣,一切都已是歷史的匆匆過客,如今這裏變成了時尚藝術區。在這條街上,我與詹姆斯•弗蘭科(James Franco)相約在Peres Projects畫廊會面,畫廊正在舉辦他最新的「Gay Town」藝術展。彼此介紹後,我倆便一同離開畫廊,來到街頭的一家餐館共進午餐。
弗蘭科友善地笑著說:「我還帶了幾個從洛杉磯來的學生呢,是與他們一起共進午餐呢,還是就咱倆?」這問題讓我有些糾結,儘管我很想把「與FT共進午餐」的訪談節目變成天馬行空的加州媒體交流研討小組會,但我思考再三,覺得還是遵循《金融時報》的老規矩爲妥。「就隨你的意思吧,」弗蘭科摟著我肩膀說道,笑得很high。
毋庸置疑,詹姆斯•弗蘭科的笑容具有無窮魅力,正是這讓他成了影視明星。他是貨真價實的好萊塢巨星:片酬已達數百萬美元,和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共同主持奧斯卡頒獎典禮以及不得不應對網路上鋪天蓋地的流言蜚語。弗蘭科是個演戲天才——在丹尼•博伊爾(Danny Boyle)執導的影片《127小時》(127 Hours)中,他自斷胳膊以求生的出色演技讓他獲得了奧斯卡提名以及衆多獎項。但正是他魔力般的笑容,讓他快速竄起,成爲好萊塢的熠熠生輝的大明星。
但34歲的弗蘭科並不僅僅是個演員,他還是藝術家、作家與學者。勿庸置疑,在闡述名聲與藝術的關係方面,他是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以來最博學、也最具顛覆性的評論家,要不他就是個自命不凡、自我吹噓的大騙子。批評界可是六親不認——《好萊塢報導》(Hollywood Reporter)譏諷他是「好萊塢不知疲倦的媒體活躍分子」——但它本身又是弗蘭科忘我工作的不竭動力。
對名人的感想是弗蘭科此次「Gay Town」藝術展的主題。展品風格汪洋姿肆、雜亂無章,甚至猙獰恐怖,顯然是思維混亂者混合運用了各種素材——錄像、畫有圖案的破布、霓虹標牌,其中很多作品更顯大不敬,而所有的作品都在質疑文化的真正動機,當今文化賦予名人尊貴地位後,既對他們歌功頌德,同時又極力詆譭貶抑。過目不忘的是一張粗略繪製的「蜘蛛俠」, 「嘿咻蜘蛛俠」的潦草字樣則是橫貫畫面。(弗蘭科在山姆•雷米(Sam Raimi)執導的《蜘蛛俠》(Spider-Man)三部曲系列影片中飾演男主人公的朋友兼復仇者哈里•奧斯本(Harry Osborn)、又名新惡魔(New Goblin))。
這次展覽的名字「Gay Town」不由得讓人對弗蘭科的性取向浮想聯翩——這只是流言蜚語者津津樂道的其中一個話題,他飾演的其它一些角色更讓這些八卦訊息甚囂塵上:他在2008年的傳記影片《米爾克》(Milk)中飾演同志政治家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由西恩•潘(Sean Penn)飾演)的戀人;在2010年的影片《嚎叫》(Howl)中飾演 「垮掉派」同志詩人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聯合執導並送柏林電影節(Berlin Film Festival)參展的《皮革酒吧》(Interior. Leather Bar)則重新想像與演繹了影片《虎口巡航》(Cruising)中觀衆沒能看到的那些赤裸裸性描寫情節,《虎口巡航》是威廉•弗萊德金(William Friedkin)在1980拍攝、由艾爾•帕西諾(Al Pacino)主演的一部同性戀圈連串兇殺案的偵破片。
坐在亨澤爾曼餐廳(Henselmann),我與弗蘭科似乎都遠離了腐化墮落的現實世界。亨澤爾曼兼咖啡屋與餐館於一身,窗明几淨,擺放著賞心悅目的黃座椅,裏面則沒有其他顧客。餐館的名字取自同名建築師,對方還主持設計了柏林當地好幾處建築。目前還不到中午,因此餐廳的招牌菜還未到供應時間,湯(牛肉與加刺山柑燒土豆)的名字聽起來有些不倫不類,所以我倆決定點素乳蛋餅沙拉。
弗蘭科身穿綠格子襯衫、黑色短外套,下穿牛仔褲。我由於剛坐早班飛機從倫敦趕來,所以略顯疲憊。「我也剛從洛杉磯坐飛機趕過來,」弗蘭科的話頓時驚醒了我。「但我對此已經習以爲常。」於是,我們點了兩杯卡布奇諾熱奶咖啡。
「因此,我說,Gay Town藝術展看似荒誕不經,」弗蘭科深吸了一口氣,深思熟慮後審慎向我講起自己爲何會想到要舉辦這個主題的藝術展,它展示的完全就是他自己的心路歷程。「有此想法大概就在六、七年前,當時我重回大學攻讀英國文學與藝術,我想與演電影一樣,認認真真地舉辦藝術展。
「剛開始,我覺得無法將自己的從影經歷放進藝術展中去,觀衆也不會太待見我——他們會認爲這並非合適的主題。但我在09年舉辦了名爲「被遺忘的詹姆斯•弗蘭科」 (Erased James Franco)藝術展,靈感就來自於羅伯特•勞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擦掉的德•庫寧素描》(Erased de Kooning),我收集了自己之前演過的電影圖片與影片,以此作爲展覽的素材,它們都是很有意思的資料。
「09年的個展,讓自己覺得這些取自個人所演電影與外在形象的資料實際上是藝術展的絕佳素材。很多藝術家,如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保羅•麥卡錫(Paul McCarthy)以及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觀看影視作品後,就把觀感透過自己的作品表現出來。而我身處的位置比較獨特,涉足參與了各個領域,它們是很好的展覽主題。」
姑且不論他的笑容與銷魂的黑眼睛,正是這一番高談闊論就能決定你對弗蘭科好惡與否。「Gay Town」中的某些展品竟然是文章,而內容就涉及他本人,圖片周圍寫滿了他自己的心得體會。我覺得這次展覽挺陰鬱,弗蘭科回應說:「我覺得你可能會說展覽主題很陰暗。但換個角度看,其實不然。我只是想讓觀衆深切感受我們如今的生活方式,彼此如何交流、圖片如何再次傳播及欣賞。」
那麼這個可憐的蜘蛛俠,你又該如何解釋呢?他看似憤憤不平。
長時間的沉默……
「他的憤怒不針對任何人與事。山姆•雷米執導了蜘蛛俠三部曲,拍《奧茲巫師》(Oz The Great and Powerful)我倆再次合作。這些圖片只是來揭穿某些虛假表象。我知道自己只是這個龐雜製作系統的一部分,我並非有啥抱怨。但我們花費數億美元拍出組成這些影片,它們畫面好看,給觀衆了帶來無窮歡樂,它們是了不起的藝術形式。
「但是,電影的確精心打造了很多不可思議的表象,很難讓人看到深層的內涵。我卻對此產生了濃厚興趣,所以這些影像圖片就是起揭穿作用。」我對他說,自己倒覺得這些圖片挺有意思。「我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中加點幽默,」他說。「因爲喜劇並非藝術的重頭戲,而大製作影片卻非常看重它。」
正說著,我們的乳蛋餅端上來了,味道遠勝於外觀。此時背景音樂開始播放羅德•斯圖爾特(Rod Stewart)的《不想再提起》(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但弗蘭科此時看上去心情不錯。把自己紛繁複雜的生活和多面工作分門別類清楚,不知他覺得困難否?
他笑著說:「的確很難。光當演員時,自己就不想做分外的任何事。別人說我得學傑克•尼克爾森(Jack Nicholson)與艾爾•帕西諾——不參加任何脫口秀節目,因此才能得心應手地扮演各種角色。但如此心無旁騖我很難做到。我爲此耗費了大量精力,但收效甚微,成效也不明顯。事實上,我並不反感採訪,相反我還很喜歡接受採訪。」弗蘭科朝我的話筒擺手示意,表示他的態度。「而且我依然能遊刃有餘地扮演各種角色,觀衆也依然買賬。」
弗蘭科曾說過睡覺純屬浪費時間,他不斷飾演各種角色,都十分成功,偶爾也出演火爆的撞車場面。2011年與安妮•海瑟薇一起主持奧斯卡典禮時,站在光彩照人、熱情洋溢的海瑟薇身旁,他顯得很呆滯。網上傳言他嗑藥。但在大衛•萊特曼(David Letterman)主持的深夜秀(Late Show)節目上,弗蘭科竭力否認。「我很喜歡安妮,但她太富激情了,我覺得就算大嘴怪(Tasmanian devil)站她身邊,也會神情恍惚的,」他說。
. . .
2006年,在輟學10後,弗蘭科重返大學校園,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UCLA)攻讀文學與寫作,隨後又在四所不同的研究生院修課(算是他的一大特色),最近還執起了教鞭(因此算是UCLA的教職人員)。我問他對此有何感悟。「學校可以宣洩掉拍電影的一些壓力。每演一個角色,我常與其共生死。有了這些新的發泄口,就感覺輕鬆多了。」
我問了他上大學是否仍爲了拿學位。弗蘭科答道:「我最後想拿的就是耶魯大學的博士學位,這得花相當長時間。」我於是問他的攻讀方向。「大致屬於電影與文學的交叉學科,以及兩者相互轉換後會發生什麼。」弗蘭科熱衷學習在好萊塢圈子內自然被視爲異端。「不要疏於學習!」,在最近的訪談節目中,萊特曼曾以戲謔的口吻對採訪對象如此結語。
弗蘭科出生在加州帕洛奧圖(Palo Alto)一個有葡萄牙、俄羅斯、瑞典以及猶太血統的家庭,從小就深受學術與世俗氛圍的薰陶。他最初進入UCLA是攻讀英國文學專業,但一年後退學,轉而進入演藝圈。他事業的分水嶺是2001年,當時他在同名電視傳記片《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中飾演迪恩,他的精彩演技使他隨後得以出演《蜘蛛俠》第一部。
他隨後的演職生涯走的完全是折衷路線:從斯托納喜劇(stoner comedy,代表作是2008年的《菠蘿快車》(Pineapple Express))到電視肥皂劇(以濃郁的後現代派風格,在《綜合醫院》(General Hospital)中飾演了一個名叫弗蘭科的系列殺手),莫不如此。201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關聯短篇小說集《帕洛奧圖》(Palo Alto),講述了生活在美國郊區的青少年故事。弗蘭科爲數不多的散文行文簡練,儘管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冷嘲熱諷,仍好評如潮。
我問他爲何對青少年的話題一直這麼感興趣,弗蘭科的回答頗具技巧(這倒讓人出乎意料):「青少年感覺啥事都很不得了,但經驗卻差強人意。正是由於這樣,雞毛蒜皮的事往往會興師動衆。儘管我如今已長大成人,但心中仍在糾結同樣的問題:如何與別人交流?該對誰忠誠?如何對待朋友與仇敵?如何對待自己的夢想?」
我於是問他:成了影視巨星後,這些問題是否會在溫牀似的演藝界變本加厲?「這正是它成爲本人另一大關注主題之原因所在,」他回擊說。
不看其它的,單單是身爲好萊塢巨星,就讓弗蘭科有幸獲取大量鮮活多樣的材料,成爲他藝術創作的素材。到柏林除了舉辦自己的藝術展外,他還在柏林電影節上推銷自己的《奧茲巫師》與另外三部影片,其中包括《拉弗蕾絲》(Lovelace,他在片中飾演休•海夫納(Hugh Hefner))與《皮革酒吧》。我問他《皮革酒吧》的情況,該片今年初在聖丹斯(Sundance)首播後,惡評如潮,但他似乎對此並不以爲然。
「這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即如何把電影作爲其它創作的源泉,」他說。「我對《虎口巡航》情有獨鍾,但從美學上說,我特別喜歡《皮革酒吧》。威廉•弗萊德金使用了上世紀70年代末真實的皮革酒吧作爲拍攝地,還運用了很多真正顧客。當時還是艾滋病流行前的那段歲月,但如今一切已是時過境遷,但整個場景看上去依然那麼棒。
「我想在影視中展現真正的性愛。但我不敢親自操刀,因爲我從未在電影中表演過真正的性愛。」所以弗蘭科決定與專拍情色藝術的同志導演特拉維斯•馬修斯(Travis Mathews)聯手。「他是拍同志影片的高手,生活中也是個同性戀,而本人兩者都不是,我倆之間的合作非常融洽。」
這幾乎等同於明確宣佈弗蘭科本人是個異性戀者,再說誰會在乎這呢?
他爲何以及如何惹很多人不悅,原因再簡單不過了。對於不符合行規的演員,影視界不由自主地表示猜疑,原因並非弗蘭科破壞了規矩——他是風度翩翩的脫口秀座上賓,對演藝界種種要求能應變自如,否則他的片約早就成了無源之水了。
更要命的是,他用自己的遊戲規則補充了好萊塢的行規,卻往往喫力不討好。藝術圈也是非常自私自利(這一點很讓人抓狂),對於不經意破壞規矩者並不待見。在Gay Town藝術展開幕當晚,柏林某藝術商會對我說自己覺得弗蘭科的作品十分「稚嫩」——如此反應再正常不過了。
但我覺得弗蘭科的重要性遠不止於此。在橫跨演戲與藝術這兩大文化領域時,弗蘭科均有耳目一新的洞察力。生活與藝術捉摸不透顯得司空見慣,但由於大衆媒體不停地炒作,而更變本加厲,比過去更咄咄逼人,也更冷酷無情。如今與安迪•沃霍爾的時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生存狀態仍是一把雙刃劍,但傷起人來更狠更痛。弗蘭科比舍曼、麥卡錫與戈登更深知此種感受,我問他,針對新興媒體生態圈(blogosphere)推出的這些辱罵性藝術作品是否屬於某種報復?畢竟,展覽推出了很多放蕩不羈的作品。
「但這一切我難以掌控,」他說。「而且我也不想去掌控。我所做的就是把它們作爲我藝術展的原始素材。所以若有觀衆指責我,我不會甘願成爲任人宰割的對象;如果有人說我的作品只是徒有虛名,那麼相信我,我並不想讓自己外表光鮮亮麗。若真想做的話,我能做得更加無懈可擊。」
如今沒必要對此爭辯下去了,況且也沒時間點更多菜了。弗蘭科還得在畫廊舉辦一個倉促的記者會。結完賬(實在少得可憐)後,我跟著他去了記者會。記者不止一次、而且變著法子問爲何他的電影與藝術作品念念不忘性的問題。「性是我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家都在談論它。而且就我所知,大家也都是身體力行者,性是人類繁殖生存的工具。」
哈維爾•佩雷斯(Javier Peres)是畫廊老闆,正在向困惑不解的觀衆講解此次展覽的內涵。「弗蘭科作品的基本成分是名聲,」他說。「就像一個畫家運用顏料一樣。」隨後有記者問弗蘭科:當他身爲名人感到膩煩時,往往會做些啥事。
「我主要生活在自己的私密空間中」,弗蘭科回答道。「這並非根本性問題。」
彼得•阿斯普登是《金融時報》藝術方面的記者
譯者/常和
2份素乳蛋餅:15歐元
2份卡布奇諾熱奶咖啡:5歐元
總計:20歐元

眼下,邀中國官員飯局,是越來越難了。約部長級的高官,更是非份之想。習大大反腐,讓中國官員對應酬退避三舍。三個多月前,我約傅瑩午餐,碰碰運氣,畢竟她曾經與FT喫過午餐。那次餐桌上的採訪,是2009年,她行將卸任中國駐英大使、告別倫敦之際。這次約她,她的身份已變: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會議的官方發言人。三月中旬,「兩會」落幕,她答應了這個飯局。
北京崇文門內大街上,立著一幢內蒙古大廈,裏邊是內蒙古駐京辦事處。傅瑩是蒙族,推薦了那裏的蒙餐廳。在首都,每個省份都設有駐京辦,各立門戶,像一塊飛地,伏在中南海眼皮底下,小心呵護與中央的聯繫。每個駐京辦內,有京城最正宗的本省餐館,打拼舌尖上的競爭力。
我提早到了內蒙古大廈。走廊上,出奇地冷落,可能時間還太早,兩旁一溜包房,大門敞開,似無人跡。背景是曠遠的蒙古音樂,我找到「胡楊秋色」。包間不大,中間一圓桌,背後有個沙發區,正中一幅吳冠中水彩畫,地毯的色彩熱烈,有大塊橘色。兩名年輕女服務員正彎腰趴在餐桌上,擺放著三頭羊、一匹馬、一個白色蒙古包。當然,都是玩具,只是讓客人有些蒙古的聯想。
中午11點整,不遠處的長安街上,電報大樓上的大自鳴鐘緩緩敲擊出東方紅的旋律。再熟悉不過的曲子,已敲了半個多世紀。聽到的一剎那,彷彿毛主席走來,有時空錯位的恍惚。緊跟著東方紅漫溢的尾音,鐺鐺的撞鐘聲在空氣中迴盪。窗外,一小片紅灰磚色的老民居,雜亂而破敗。路旁停著不少新的私家車,恍然兩個時代。
傅瑩在車裏發來微信說,她堵在路上,會遲到幾分鐘。在北京,人們已習慣一天辦一件亊的節奏。遲到,是老常態。準時,纔是非常態。推進門的一刻,傅瑩再爲遲到道歉。她穿了件灰色細格西裝外套,白襯衣,一條紫色灰底的圍巾,閒適而不失莊重。與她結識是她出使倫敦期間,一直稱她「傅大使」,再難改口。駐京五年多,我仍不適應王總、李局、周處的官場熱乎。
事先約定,既然是她的家鄉菜,點菜就由她包了。坐定後,我問她,是不是此地常客。她點頭說,常在這家請客,雖然有點貴。平時她與家人去得更多的,是那家呼市辦事處小館子,正宗但便宜。我開玩笑說,爲了這頓蒙古菜,把早餐都省了。她喊過男服務員,神速地報了一長串菜名,好像有奶茶、老額吉奶皮子、奶豆腐、羊排手把肉、蒙古饊子、巴盟酸菜。她說,她喫素,我多喫肉。
服務員輕聲問她,要點酒嗎?傅瑩沒徵求我意見,擺擺手,單方面否決了。聽說,當下官場紀律嚴明。自中紀委公佈「八項規定」後,官員因公餐敘, 除了外事,一律禁止點酒。我喊住服務員,對傅瑩說,今天你是FT的客人, 我做東 。喝點你們老家蒙古酒,總可以吧?傅瑩倒也爽快,那就喝點吧。問我,低度的,還是高度的?想到蒙古人的豪氣,我說,高度的吧!服務員拿來一瓶 「蒙古王」,烈酒,53度。一看產地,內蒙通遼,傅瑩的老家。
前年基辛格訪華,傅瑩在這裏宴請了他全家。她說,那是基辛格第一次喫蒙古菜。服務員向他敬酒,獻哈達,肉食一道道地上桌,他喫得盡興。我說,在釣魚臺今年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剛見過93歲的基辛格。他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前駐美大使張業遂對話後,被一批VlP粉絲圍住,動彈不得,最後還是傅瑩上臺挽著他走下講臺,成功營救。我看到,基辛格滿臉父輩的滿足。
我問她,1971年,基辛格祕密訪華,之後四十多年,訪華上百次。他對中國的看法有大的修正嗎?
「我認爲他比較穩定。這並不是說他的觀點沒變,而是沒有脫離中國的實際。當別人覺得中國不行的時候,他沒有對中國失去信心。當別人覺得中國可怕的時候,他也不會跟著那股風走。每次來中國,他要跟中國領導人談話,也要接觸普通中國百姓。你看他評論中國,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講中國人民的生活,這是他親眼看到的。對中國,他從來沒有迷失過。那麼多研究中國的人都會有恍惚和搖擺的時候,對中國的預言錯了或者沒看準的時候,他很少有這種情況。」 對這位中國的老朋友,她顯然頗有好感。
一大鍋羊排湯上桌。服務員爲我們衝滿奶茶,斟上一小杯「蒙古王」。傅瑩催我下筷。我把話題引到剛去世的新加坡開國之父、與基辛格同齡的李光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年輕的女外交官傅瑩曾是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中國領導人去新加坡訪問。有時候李光耀會設家宴,就在他家後院裏,很溫馨,燈光、燭光。他挺關心人的。翻譯沒有那麼多時間喫飯。有時甚至沒有桌牌,不上桌的。他就把紅毛丹剝了,遞給我,讓我趕緊喫。」
傅瑩最後一次見到李光耀,是去年在獅城的香格里拉對話。我很好奇,李光耀與幾代中國領導人交往,一直很直率,常常醜話在先,風格強悍。從鄧小平、趙紫陽到江澤民,倒都能接受他的風格?
你說,中國領導人不接受誰的風格?傅瑩反問我。
「我在外交這個行業幹了一輩子,從當翻譯到直接參與。中國領導人和外國領導人的交往,一直是有交鋒的。外交這個東西,就是有來有往,是有事要談。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不同,相互間肯定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毛澤東、周恩來這代人奠定的外交理念特別好: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平等對待。能幫你的,幫你。辦不了的,也告訴你爲什麼。我想讓你辦事,也會有你幹得了和幹不了的。利益問題上,各國都有自己的位置......李光耀最大的貢獻,是他從新加坡的利益考慮。有的人批評他,認爲他這樣或那樣。你不可能指望他從中國的利益出發......」
我們開始喫手抓羊排。看傅瑩優雅地處理羊排。我暗忖,手抓的美食,看來很難進入國宴的菜單。如果兩國領導人能在國宴上一起喫手抓羊排或大閘蟹,雙邊關係一定鐵得牢不可破。
「對外交往當中,不能說什麼事都自己拿著,需要在得失之間權衡。有必要的話,該放手就要放手......這裏頭,還是要有是非觀的。」
服務員又斟上一杯「蒙古王」。
「近代以來,中國外交從哪兒開始的?西方國家的外交,源自戰爭,需要停火、談判,包括劃分殖民地。中國外交,是從改變屈辱地位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始的。鴉片戰爭後相當長時期,中國的外交是被別人強加來的。我在英國當大使時,瞭解過19世紀、20世紀這段歷史。中國的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怎麼去的?是被英國人逼著去那兒,租給你一幢房子,請你來看看大英帝國是什麼樣子,要你接受他們的很多要求。清王朝被迫在英國開了公使館。多年後,1942年民國政府的外長宋子文赴英,要求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而不只是宗主權,被拒絕。直到2008年,英國人還只是承認中國對西藏有宗主權,而不是主權。2008年我作爲中國大使與英國人就這個事談了多少個回合。時任總理溫家寶和來華訪問的英國首相布朗在釣魚臺喫晚飯,一直講這個事,講「西藏問題」的由來。最後,英國明確承認了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1949年以前的中國積貧積弱,在國際上沒有地位,個體的外交官再出色,也難有作爲。」
現年62歲的傅瑩,是幸運的。文革中,她在內蒙插隊三年,做過廣播員,放過露天電影,後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學英語。進入外交部後,再到英國留學攻讀國際關係。她出使的第一個國家是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她是中國的第一位蒙古族大使、第一個派駐要國大使,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外交部第一位女性副部長。文革中,毛澤東的外甥女、文靜的王海容,曾曇花一現,出任外交部副部長。
傅瑩很想多聊聊她現在的工作:中國人大。我告訴她,我連續跑了五、六年「兩會」,仍很困惑。一些代表坦承,人大的功能至今仍是一枚橡皮圖章。我說,每年「兩會」,搭出租車去天安門,司機都不願去,都怕那個地方,擔心被罰,警察要趕。他們不覺得人民大會堂裏發生的事情跟他們有什麼干係,帶來的只是麻煩,也不知道誰是他們的人大代表。
她顯然不滿意我的說法,喝了口奶茶:「在英國,每年議會開會,第一次女王演講,也是打不到車的吧?沒有哪個計程車司機會往西敏寺那兒跑,進不去出不來的,這種情況在哪兒都一樣。交通不方便,司機肯定不願意去,這完全可以理解,要尊重他們。」她就我對中國人大制度的責疑,作了一個有關交通管制的解讀。
2013年傅瑩轉任中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之前,一輩子的歷練和積累,都在外交。如果讓她選,她會去政協。她的先生、民族學家郝時遠在那兒,很多資深的大使也在那兒。現在她倒喜歡人大這份工作了。她說,如果年輕時有選擇,或許會選讀法律。在她看來,法律與外交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她更心儀確定的東西:「法律很嚴謹,是非很清楚。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沒有那麼多灰色地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潛意識裏,她或許想在法律中尋求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在她早年的動盪生活中顯然不存在:「我是經過文革的,知道無法無天是什麼概念。突然有一天,有人把父親拉走了;突然有一天,母親不能按時回來了; 突然有一天,學校不上課了;突然有一天,別人可以當兵你就是不行,別人可以進工廠你就不行。社會的規則和秩序都沒有了,這是很可怕的。」 文革中,時任內蒙古軍區宣傳部副部長的父親、一位有書卷氣的軍人,遭受迫害。
我已喝空了第三杯奶茶。傅瑩顯然已感覺到了我對中國人大制度的深度疑慮。
「人大制度需要不斷完善,很多法律可能不是很完美,執行也不一定很完美,肯定要有一個過程。但是,老百姓的感覺也不可能超越現實。如果沒有做得那麼好、沒有做到,你想讓老百姓覺得做得特別好也不可能。老百姓有不滿意,我覺得挺自然的。可能外國人看到中國老百姓有這個不滿意、那個不滿意,好像就證明中國怎麼了!其實我在英國、澳洲時,看到人們不滿意的地方多去了。對中國的決策層和立法機構來講,知道老百姓有什麼不滿意是很重要的,要知道老百姓哪兒不滿意,搞清楚爲什麼,怎麼解決。」
一大鍋羊排,停在桌上。對她的解釋,我有所保留。FT的餐桌上,總得有點茶杯裏的風暴吧。
我說,人民大會堂裏,中國人大開會的方式幾乎與五十年前一樣,仍是蘇聯時代的。當然,現在配備了表決器,是個進步。不過領導人坐檯上,代表坐檯下。很多代表只是在舉手和拍手。中國人大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太慢了?
「人的期望,永遠比現實要高,否則就沒有意思了。但是,對外國記者來講,我也比較理解。因爲你們看到的只是表面、外在的東西。對裏面的東西,你們能看到的就比較少!人大有責任依法監督政府,有時我們提出的意見也是很尖銳的,但是目的不是讓政府難堪,而是希望政府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好,告訴他們哪裏有問題,希望改進。所以,人大不監督有責任,政府不改進也有責任。」傅瑩回答得很坦率。
我說,外國記者確實看不到啊!
「你們可能看到,我們人大的報告很少有被否決掉的,雖然否決票在上升。我們人大常委會開會,每個法律基本上都能透過。這是因爲我們在審議和溝透過程中,花了很長時間去尋求共識。比如立法法修正案,已經過了二審,也向社會公佈過,經過專家們的千錘百煉,再拿到會上。將近三千代表討論,一千多人發言。根據這些意見,做了七十多處修改。如果不改,硬扛著,投票的結果就不一定了!」
她又提到英國,她最後出使的國家。她說,這種情形下,估計英國國會不會改,只要能透過就行。中國則是連夜開會,晚上討論修改,甚至作很重大的修改。再解決不了,還要到代表團一個個去解釋和說明。表決時,雖然有人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但是大部分代表會投贊成票。
我決定與中國人大發言人抬扛:「兩會」加起來,會期長達15天。坦率地說,旁聽兩會,相當一部分議程並非議政,不少代表更有興趣的是拍照留念。不少省份,人大代表的發言還要事先審查把關。審議報告時,更像是向領導同志彙報工作或表功。 如果連人大代表都信不過,他們如何議政?
「如果你們記者在,肯定要小心。要是我,也會小心講話。你們記者多厲害,到時候如果報不準,說歪了,現在這個時代,資訊傳播很厲害。」
傅瑩半開著玩笑,夾起一塊奶皮子,作出反擊: 「話說回來,英國議會里,有時議員念稿子那麼長時間,下面一個人都沒有,電視上誰看?!政治裏肯定要有些程式性的東西。」
我夾起一條羊排,繼續發問。我說,每年採訪「兩會」的中外記者,多至三千人。那麼多記者,總得有事情讓他們報導吧。除了聽李克強總理花兩小時,一口氣唸完長達40頁的政府工作報告,記者能採訪的人和事極其有限。
「西方媒體看中國,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層是對這個制度是否認可,再一層是這個制度運作得怎麼樣。比如我有時候跟一些歐洲記者辯論,準備記者會之前我要開好幾次圓桌會,辯論非常激烈。他們根本上就不認可中國的制度......你橫說豎說都認爲你們不對。他們的參照系數就是自己的制度。德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英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美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我只能耐心地跟他們講,我是幹這行的,已經講了三十年。有這個耐心,繼續講!」
聽得出,素來談吐溫婉的傅瑩,語調裏已有一絲不悅:「他們從根本上不認可你這個制度,所以看不懂,也不可能看懂,甚至是拒絕看懂。」
每年「兩會」都爆出不少「雷人」提案。你對人大代表的產生機制和議政能力,印象如何?
奶茶再添一壺,午餐已過半。我接連喫了幾條蒙古饊子,補充能量。她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她解釋說,批評不是壞事。中國的人大制度是有效的。聽到此,我耳邊響起人民大會堂內數千代表聆聽報告時,檔案翻頁時整齊劃一掠過全場的聲響。
傅瑩當然清楚,中國的人大制度不乏批評者。作爲發言人,她當然相信這個制度:「人大制度的好處,在於它有方方面面的人,帶來方方面面的資訊,讓這個國家沒有死角......外界特別看不懂的是,爲什麼中國13億人口能夠治理得這麼好,總能不斷往前走,總能解決問題?!」
我說,是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取得了決策的高效率吧!很多西方領導人到中國訪問,一方面覺得北京的制度有問題,另一方面又很羨慕,覺得這個制度至少有效率,能辦成事情。
「你說中國集權?……西方說我們集權,所以有效率。我認爲這是一種偷懶的說法。他們的制度走到今天,有它的道理……誰跟誰比較,不太好說。你解決不了問題,是你的事。我能不能解決問題,是我的事。西方人容易一會兒說中國多好多好,一會兒說中國多差多差。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好,也沒那麼差。」
這段話,我曾在另一個場合聽她說過,是她的直覺,也是深思熟慮的判斷。即便輕聲細語道出,骨子裏仍有點咄咄逼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高收入國家元氣大傷,效率滯緩,對自己制度的自信似乎打了折扣。他們開始羨慕中國的效率、成長與速度。他們不再責疑,而是尋找「中國模式」的合理性。他們高調地向中國領導人伸出大姆指。我明白傅瑩這番話的底氣。
我換了個話題,問她,可否請張德江委員長向李克強總理建議一下,政府工作報告能否簡短一些,也不用全文通讀?
「過去也有較短的政府工作報告。凡事都有它的原因。你說哪個領域的事兒能漏了?水利不說?農業不說?工業不說?都得說!誰重要?誰不重要?!中國這麼大,發生這麼多事,讓總理去取捨也很不容易……政府報告有動員人民的任務。你在這兒聽兩小時,感覺時間長。但在很偏遠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決策怎麼回事。聽上兩小時,就可以把過去一年的事弄明白了。」
中國的事情,越來越多。看來政府工作報告只會越來越長。我說。
「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前人沒有經歷過,想都想不到。就像霧霾。在英國,一個時期是煙霧,一個時期是工業汙染, 一個時期是汽車尾氣,是遞進的。而在中國,全都一起發生,結果就產生了新的化學反應,形成一個新的東西。」
出任人大會議發言人兩年,平時低調的傅瑩已成公衆明星。過去兩年,媒體和民間對她記者發佈會的表現稱讚有加。我問她,有沒有聽到過激烈、刺耳的批評?
「能聽到批評!家裏人的批評更直截了當。我先生就關心我的語病。去年,他就批評我講話時 『這個這個』太多了。今年發佈會前那個晚上,他在政協開會,特地跑回家一趟。見我正焦頭爛額地背詞,就給我寫了一張紙。早上我看到了:在『呃』旁邊打了X, 『這個』旁邊寫了X,意思是不要說這幾個字。發佈會那天,我在臺上,就把這張紙放在檔案夾的左手,一低頭就能看見,提醒我克服語病。他認爲,這些語病讓我的講話顯得鬆散,反正他不喜歡。」
很少有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自嘲,或表露內心的不安全感。傅瑩是例外。她說,直到現在還沒有看過自己新聞發佈會的影片。 她不敢看。「看到有毛病,我會後悔死了。 」
今年「兩會」,作爲人大代表的傅瑩,她的提案仍是有關中國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河流如何維護、界河泥沙如何及時處理、錢從哪兒來,邊境道路維護,沒有路怎麼辦。「我咬住一件事,能辦好就不錯了。」
你覺得媒體可怕嗎?我問她。外界向來覺得傅瑩很會與媒體打交道。
「挺可怕的!」 她說,她對媒體的戒備, 因於她的慘痛教訓。在菲律賓和英國當大使時,媒體採訪時,挖了很多坑,不留神就掉進去了。
我把話題挪到當下熱到發燙的話題-「一帶一路」。我問她,對中國,是不是過早了?
「九十年代,歐亞大陸橋曾經談得很熱火,但一直是紙上談兵。二十年後,中國條件有了,資金也有了,可以付諸實施了,怎麼就成問題了呢?我們現在幫著大家實現歐亞大陸橋。歐洲以外可能沒有人記得了? 也許他們換代了!」
傅瑩說話,很少提高聲調。雖然她已遠離外交圈子的談判桌,她的直覺與反應仍是外交官的。該機敏時機敏。該尖銳時尖銳。該溫情時溫情。所有的註腳背後,都在國家利益。
午餐,快臨近尾聲。在領導人習慣統一染烏亮黑髮的中國,有人問過我,一頭銀髮的傅瑩,是不是有意染白的?我問了多年來一直想問的問題。傅大使,你的一頭白髮,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頭頂有白頭髮比較早。後來白得更多,就開始染髮。在英國生活期間,我看很多人頭髮白了都不染,我也就放開,不染了。」
你平時怎麼放鬆呢?
「走路、散步。」 她答。
我說,北京好像已經不太適合散步吧。
「只要天好,還可以。我在家裏,可以在跑步機上走路。 我還是喜歡看書。書是另一個天地。」
我問她,一年裏,她的先生能喫上幾頓她做的菜?我知道,在家中,她是很享受的。她先生是主廚,廚房是他的領地,不放心太太動油鹽醬醋。傅瑩只有洗碗的份兒。談起家裏的事,她從剛纔討論地緣政治的緊張中解放出來。她的臉上,寫著小小的得意與滿足。
午餐已過兩個半小時。最後, 我們又滿上一杯「蒙古王」,算是收尾。她小喝一口,笑著說,有點微醺。我說,今年「兩會」,據說習大大在會見一個省市代表團時問道,代表們聚餐喫得很乾淨,是不是最近油水少了?
「中國這一段時間,大力度反腐敗,大家都挺有感觸,揭露出來的事情觸目驚心。十年前,都無法想像,不能理解。有的官員,貪的錢一輩子都花不掉。這個國家、這個制度、這個黨,確實應該解決腐敗問題。」
她站起,披上搭在椅背上的紫色圍巾,匆匆告別。
桌上好幾碟菜,沒怎麼動。與FT午餐,喫飯好像永遠是個美麗的藉口。這頓午餐,按中國官方標準顯然有些「超標」。看了賬單,這瓶「蒙古王」要價頗高,近人民幣600元。我趕緊讓服務員把剩下的半瓶酒打包,帶回編輯部。
菜單
北京崇文門大街,內蒙古大廈
醇香奶茶 1份
香酥炒米 1份
老額吉奶皮子 1份
醇香奶豆腐 1份
蒙古饊子 1份
金帳手把肉 2份
巴盟燴酸菜 1份
莜麪窩窩 2份
熱湯 2份
蒜蓉西蘭花 1份
拔絲奶皮子 1份
活性阿爾山500ML 1份
經典燒麥 1份
經典大帳蒙古王 2份
服務費:228元
消費總計:1746元

阿爾•戈爾(Al Gore)誇張地擦去額頭汗水,顯出精疲力竭的樣子。現在是上午,這位美國前副總統剛剛完成了他一天中第一項重要任務——對滿滿一個大廳(擁護他的)法國金融家作有關氣候變化的講座。我們見面的時候,我問他,到目前爲止,這個講座作了多少次。他想了想說:「我想,大約有1200次。」他瞪著眼,狂躁地盯著我,嘆氣說:「我現在滿腦子都是那些東西。」
我們此刻正在巴黎,坐在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漂亮的辦公大樓裏。該行是氣候變化機構投資者團體(Institutional Investors Group on Climate Change)會議的主辦方,而戈爾是這次會議的明星人物。因爲我們的會面安排在早餐後不久,餐廳給我們留了一盤甜麪包。我們拿了一些,我又喝了點兒咖啡。我想給他也倒上一杯咖啡,但他想喝健怡可樂(Diet Coke),於是派了一名服務生去找。(我感覺到,他們不常遇到這種要求——畢竟,這裏是巴黎第16區。)戈爾脫掉他的深藍色西裝夾克,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褲角微微向上提起,露出黑色的牛仔靴。
曾被描述爲「木頭人」
這與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大不相同。那時,他被描述爲「木頭人」,甚至被比喻爲木偶匹諾曹(Pinocchio)。這和他的競選對手——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的「好男兒」(good ol' boy)形象形成鮮明對比。在那次痛苦的失敗之後,「匹諾曹」這幾年又活躍了起來。他似乎重新找回了自己:自在而放鬆,坐在椅子上肢體舒展,需要強調要點的時候身子前傾。他的身體也更加強壯了,現在的體格更爲結實,頭髮中散佈著絲絲灰白。
一定程度上講,他現在更爲開朗的個性,與他作爲環保運動者日漸取得的成功密不可分。他已經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說服世界相信全球變暖的威脅迫在眉睫。他似乎有了一些進展:上週,他同意擔任英國政府氣候變化顧問。同時,他那標誌性的全球變暖演講,已拍成電影《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該片已成爲迄今全球票房排名第三的紀錄片——僅次於《華氏911》(Fahrenheit 9/11)和《帝企鵝日記》(March of the Penguins)。
服務生端上一罐健怡可樂,倒在戈爾的杯中。戈爾微笑著對服務生說:「謝謝。Merci(法語:謝謝)」他一邊喫著羊角麪包,一邊告訴我,他一直都對氣候變化感興趣。「這是地球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不願面對的真相》將戈爾這種興趣的起源,追溯至他在哈佛(Harvard)的大學時代。當時,他是羅傑•雷維爾(Roger Revelle)的學生,而雷維爾正是首批進行氣候變化研究的科學家之一。1976年代表田納西州當選衆議員後,戈爾發起運動,呼籲社會嚴肅對待該問題,但得到的回應寥寥。議員同僚們要麼對此興趣索然,要麼充滿敵意。這一點在美國前總統喬治•H•W•布希(George H.W. Bush)後來的總統競選中得到體現。
「美國人的態度終於開始改變」
戈爾認爲,美國人的態度終於開始改變。儘管歐洲公衆對氣候變化的看法更爲一致,但他表示,美國和歐洲觀衆對他的電影的反應,「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那麼不同」。「我認爲,這基本上是個道德問題,」他表示。「它呼應了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其它宗教、佛教——所有宗教都非常明確地宣揚,我們應承擔保護世界的道德責任。」他引用《聖經》的話:「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於耶和華。上帝會敗壞那些敗壞世界的人。」這令我想起他在田納西州接受的南方浸信會(Baptist)教育——他的父親老艾伯特•戈爾(Albert Gore Senior)擔任田納西州民主黨參議員近20年。
的確,一些人將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視爲聖經預言的懲罰。但戈爾感覺,美國聯邦政府對這場災難的反應,纔是問題最重要的方面:「政府忽視了一些明確的警告,這令人們感到震撼。」他繼續自己的主題:「因爲,如果這些警告都被忽視的話,那(布希)忽略有關全球變暖的警告,你又奈他如何呢?他努力塑造的形象,特別是在9/11之後苦心經營的形象,其基礎就是『我將保護你'的承諾。但紐爾良就沒得到保護。」
「一度將要成爲下一任美國總統」
雖然感覺有點不太禮貌,但我覺得有必要提出這個問題:對於2000年美國大選的失敗,他作何感想。在公開場合演講時,戈爾面對觀衆,克服了這種尷尬,稱自己是「一度將要成爲下一任美國總統」的人。這句巧妙的自嘲話語,常常引發一陣笑聲。
我決定努力表現出一些反對。我告訴他,對某些人而言,看他的電影是一種折磨。他猛然抬起雙手,模仿驚恐的神情,盯著我。我繼續說,「折磨」是因爲觀衆在想,如果這個人贏了大選,世界將會怎樣。他謙虛地笑了笑:「謝謝,這妙極了,非常妙。」但他對輸掉大選是怎麼想的呢?
「我已經不想它了,」他嚴肅地說,隨後用手捂住臉幾秒鐘,假裝哭泣。「我關注的是未來,而不是過去。」
儘管戈爾現在對氣候變化充滿熱情,但在柯林頓(Clinton)執政期間,他在環境問題上並沒有什麼建樹。「首先,我不是總統,而是副總統,」他立刻表示。「我對柯林頓總統在這個問題上對我的回應沒有抱怨。但關鍵是我並沒有統領全域性。能有一種夥伴關係,我很知足,我確實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現在很顯然的是,最高領導充分關注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他又咬了一口麪包。「我給你舉個例子。我在擔任副總統時,打算立法徵收碳排放稅。柯林頓否決經濟顧問小組的建議,讓我這麼做……衆議院透過了這部法案,但在參議院以1票之差未獲透過。最後,這部法案被弱化,僅剩下針對每加侖汽油的可憐的5美分稅。」即便如此,對某些人而言也還是走得太遠了:「這部分導致我們在兩年後把國會控制權輸給了紐特•金裏奇(Newt Gingrich)。」
「你沒喫什麼東西啊,」滿口羊角麪包的戈爾,指著幾乎沒動的一盤法式蛋糕提醒我。我挑了帶杏醬的羊角麪包喫了一口,後來我在自己的筆記型電腦上發現了它的汙跡。
我們還能搭乘廉價航班嗎?
談話回到更有分量的問題上。飛機排放的溫室氣體,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曾經數年乘坐空軍一號(Air Force One)出訪世界各地的戈爾,會剝奪普通人選擇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自由嗎?
這似乎讓他有些爲難。他轉過身,安靜地想了大約1分鐘的時間。「我認爲,立即停止所有與二氧化碳有關的活動,以此作爲解決氣候變化危機的方法,是錯誤的,」他表示。「我們需要做的,是迅速採取更好的技術,這些技術能讓我們在不造成全球變暖汙染的情況下,改善生活質量。航空旅行是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目前不包含在《京都議定書》的範圍內。李察•布萊信(Richard Branson,英國維珍集團董事長——譯者注)正試圖找出解決辦法。我確實認爲,在某些情況下,許多人會減少出行。」
有什麼理由不讓中國人享受現代生活?
那麼,那些涉及面更廣的問題呢?中國和印度等發展迅速的國家,在溫室氣體排放量上正在快速追趕發達國家。目前,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僅次於美國。而且,隨著這些國家越來越多的人享受到各種生活便利設備——汽車、空調、電器商品等發達世界人們習以爲常的東西——溫室氣體排放量將進一步增加。西方人享受較高的生活水準已有數十年之久,他們有什麼權利讓那些剛買得起這些奢侈品的人,放棄享受呢——即便出於拯救地球的名義?
戈爾考慮了一下如何回答。「我們使用那些陳舊技術造成了這種問題,而這些國家有跳過這些技術的機會,」他表示。「你知道,人均擁有光伏(太陽能)電池最多的國家是肯亞。我提這一點是因爲它表明:對於還沒有電網、電話網路和其它設施的國家來說,跳過這些技術,直接使用太陽能之類的東西,其實更經濟。」
除了技術,還有一個兩難問題仍難以解決——戈爾在美國政界的未來角色。美國的下一位民主黨總統,會更易於在氣候變化方面採取行動嗎?「我正在做的,就是保證這一點。」那麼,總統會是他嗎?戈爾又喝了一大口健怡可樂。「我不打算再競選總統。」他立刻補充道:「我沒有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我不希望再次成爲一位候選者。這是個毒化的過程,而且幾年來越來越如此,尤其是關係到像這樣的問題時。」
一位助手進來了,提醒戈爾要赴下一個約會了,他站起身準備走,穿上他的夾克,捋了捋頭髮,爲在走廊裏等著跟他打招呼的人們,現出了一個爽朗的公衆微笑。他與幾個人握了手,隨後要迅速趕赴他下一個公開露面的活動,那是在德國,這是他歐洲之行的最後幾站之一,隨後他將去巴西作講座。
我走出來,走上克雷貝爾大道,向凱旋門走去,那裏記錄著拿破崙(Napoleon)的所有戰役。惟有滑鐵盧除外。
譯者/何黎
巴黎克雷貝爾大道5號
1份奶咖
1罐健怡可樂
1份奶油羊角麪包
1份杏桃羊角麪包

泰國過去從未出現過形象問題。拋開偶爾出現的有關性旅遊和走私海洛因等負面報導,該國一直很成功地將自己推銷爲理想的東方樂土:帶有異域風情、美麗、溫暖、熱情且安寧。
但近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去年11月,一羣政治抗議者佔領並關閉了曼谷機場,將泰國從旅遊宣傳冊中所標榜的「微笑之國」,變成了束手無措的度假者的傷心之地。國際人權組織正批評該國虐待難民,並利用「對君王不敬」法,折磨並監禁抨擊泰國君主制的人士。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該國爆發了經濟危機。
因此,泰國聰慧而年輕的新任總理、44歲的阿披實•維乍集瓦(Abhisit Vejjajiva)一月份出現在瑞士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爲他的祖國做一些緊急推廣活動。
阿披實去年12月當選泰國總理,由於年輕、英俊並受過良好教育,他不可避免地被稱爲「泰國的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但與美國總統不同,阿披實以前並非無名之輩。
1992年至1995年,我在泰國生活。當時阿披實是曼谷一位新當選的下院議員,已擔任著民主黨發言人這一高調職務,當時已有傳聞稱他可能成爲未來的國家領袖。
實際上,阿披實的履歷讓他聽上去更像是一位英國首相的潛在人選,而非泰國。1964年,他出生於英格蘭北部泰恩河畔的紐卡斯爾。他嘆息道,「這讓我不得不支援紐卡斯爾聯隊(Newcastle United)」,這是一支長期以來戰績糟糕的球隊。他出生於一個顯貴的中泰混血家庭,父親曾在倫敦的蓋斯醫院(Guy's Hospital)攻讀醫學,後來成爲泰國衛生部長。阿披實曾被送往英國最高級的學校伊頓公學(Eton College),那裏一向是英國首相的搖籃。
阿披實後來進入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他在那裏獲得了政治、哲學和經濟學的一流學位,而後繼續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後來他返回泰國,在全心投身政治之前,曾在泰國一所頂尖大學教授經濟學。2005年,他成爲泰國民主黨主席。
在達佛斯一家當地泰餐廳,與阿披實共享泰式菜餚本來會非常不錯。爲了慶祝他出席此次達沃斯論壇,這家餐廳特意披上了泰國的紅白藍色國旗,並掛出一條大大的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我們的總理。」
但總理們的日程排得太緊,我們只得在達佛斯會議中心(Congress Centre)一間消過毒的地下室享用小點心。該論壇疲倦的媒體員工竭盡所能,讓這裏的氣氛變得歡快些。他們給我們準備了兩把蛋黃色皮椅、一盤盆栽和一張咖啡桌,上面擺著些小點心。
阿披實的衣著堪稱完美,灰色馬甲西裝套裝,淡藍色襯衫,黑色白條紋領帶,他似乎對面前擺著的那些面目可憎的糕餅以及蜷縮的三明治有些疑惑。我解釋道,我們的訪談需要在餐飲的環境下進行。他說道:「好的,我會照做。」但他沒有對這些食物有所動作。
阿披實已婚,育有兩子,在泰國他被視爲「主婦殺手」。瘦削英俊的臉龐、大眼睛,看上去有點像男生樂團的主唱。實際上,當他的手機響起時,鈴聲是那種大氣的吉他和絃。聽上去有點兒像U2,但這位總理糾正了我。他堅定地說道:「王子(Prince)。」
泰國政治有時候看起來鬧劇百出,有時又險惡無比,兩種情況交替出現。說到鬧劇百出,阿披實最近的前任之一沙馬•順達衛(Samak Sundaravej)被迫辭職,是因爲他先前在一個電視烹飪節目上擔任嘉賓而收取酬勞。說到險惡無比,人權組織指責阿披實的最大政敵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稱,2003年,作爲「禁毒戰爭」的一部分,他曾允許進行大規模未經司法程式的殺戮行爲。他信是一位電信業大亨,曾擔任泰國總理。(在2006年的一次政變中,他信被推翻。2007年,他再次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當時他收購了曼城足球俱樂部(Manchester City),並在一年後轉手賣出)。
長期以來,阿披實一直爲使泰國政治更爲乾淨、合法而奔走。上世紀90年代末,他曾負責政府反腐委員會。但他是在艱難而混亂的形勢下上臺的。一個名爲人民民主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的組織指責上屆政府受他信代理人的控制。去年11月,正是該組織的支持者製造了混亂,他們佔領了曼谷機場和政府辦公大樓。阿披實對這些示威者進行了譴責,但實際上是他們導致當時的政府陷入癱瘓,併爲阿披實被議會選爲泰國總理創造了條件。批評者們還指出,泰國軍隊曾操縱事態,爲阿披實上臺創造條件。整個事件使他的民主紀錄蒙上了汙點。
泰國還因爲對待羅興亞(Rohingya)難民的問題而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洛興雅人是來自鄰國緬甸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有數百人不顧危險,乘坐搖搖晃晃的小船前往泰國。泰國軍隊被指逼迫這些難民在沒有引擎和足夠供給的情況返航,可能由此造成了數百人死亡。雖然許多此類事許都發生在阿披實上臺前,但最近一批難民是上月被人從海上救起的。阿披實已承諾展開全面調查,但輿論一直對此猛烈抨擊。我的公文包裏就有一篇當天《經濟學家》(Economist)雜誌上的社評,指責泰國「駭人聽聞的冷酷」行爲。
而最大的挑戰是,阿披實上任之際恰逢重大的經濟危機。既然我們是在世界經濟論壇上會面的,我就從論壇談起。這位總理並沒有試圖淡化形勢的嚴峻程度。「這個世界遭遇的前幾次金融危機,都發生在特定地區或特定國家,這意味著你可以從其它主要經濟體獲取資源,幫助消除危機,讓世界經濟安然度過。現在你能向誰求救呢?」
他表示,泰國正面臨著一場「雙重危機」。這個國家「陷入政治危機已有兩三年之久,如今又碰上了經濟危機」。
泰國對於經濟動盪並不陌生。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泰國是最早的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經常實現8%至9%的經濟成長率。但在1997年,投資者喪失了信心,泰銖遭遇擠兌,泰國成了亞洲經濟危機的第一個受害者。
阿披實在牛津的畢業論文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救援計劃爲題,現在他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泰國政府求助於IMF,以拯救泰國經濟。作爲不得不實施救援的政府官員,他對IMF的表現並不以爲然。他的論文曾指出,IMF往往會堅持採用過高的利率,而且他覺得自己的批評得到了充分證實。「我們經歷了太多不必要的痛苦,」他悲嘆道。
那麼,既然現在出現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世界能從泰國以往的經歷中得到什麼教訓嗎?
「當然。我認爲有一些教訓絕對是至關重要的。首先是你必須行動迅速,我知道當你不得不決定動用納稅人的錢時,總會面臨政治上的困難。但如果你動作慢了,就無法完成任務,就還得再來一遍。而且當你進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嘗試時,政治上的困難就更大了。」
總理先生說話輕柔而急切,越講越起勁。儘管他保證會喫一塊世界經濟論壇的點心,但是還是沒有對食物動手的意思。爲了鼓勵他,我嚐了口乳酪三明治。阿披實聚精會神、眉頭緊鎖,開始闡述他關於經濟的第二個觀點。
「人們將對如何清理金融體系給予很大的關注,但如果到最後實體經濟出現衰退的話,清理什麼都沒有用。另一個教訓是,即便你把銀行清理好了,它們也未必會恢復放貸。因此,你需要額外的機制與措施,以確保那些本質良好的業務能夠獲得流動性。但是,如果你中斷流動性供應,那麼幾乎所有業務都會出問題。」
這些關於流動性的討論,提醒我給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我用一個不太明顯的手勢,指了指鍍銀的膳魔師(Thermos)保溫瓶,但阿披實沒有理會。
「不能忽視發展中國家,[這]非常重要。所有的發展中經濟體目前都受到了影響。我明白,主要經濟體必須首先顧自己。但是如果它們忘了爲發展中國家做些事情,那麼政治與社會緊張局勢都有可能抬頭。那是十分危險的。」
他語速很快,而且很奇怪,他似乎對我輕輕推給他的杏味丹麥酥沒有絲毫興趣。我問他對於泰國城鄉差距、以及他有力的競爭對手他信的看法。他信深受大多數農民的擁戴,不過作爲民主黨核心支持者的城市精英大多不喜歡他。「你認識他肯定有很多很多年了吧?」我試探道。「你覺得他有什麼好的地方嗎?」
確切地說,阿披實沒有露出喫驚的表情,但看上去有些疑慮,還略有點喜色。這讓我想起,自己離開泰國已經很長時間了。這可能是一個非常愚蠢的問題——就像是讓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羅列出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一些優點。
然而,這個問題卻暫時打破了阿披實的鎮定。他第一次低頭看了看桌上的食物,說道:「我來點咖啡。」他喝了一口,然後勇敢地努力作答,「哦,他的樣子很現代,因此他給人的感覺是他很現代,他出身於通訊和IT領域,這會給人那種感覺。他行動迅速……但我一直說,儘管他的樣子很現代,但他的確不認同如今這個時代的真正價值觀,這完全關乎人權、參與、真正民主、透明度和良好治理。」
我把話題轉向他在伊頓公學的老校友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強森與他的性格更爲相似,目前擔任倫敦市長。在從伊頓公學畢業到上大學前的那段時間,強森曾與阿披實一起呆在泰國,兩人關係一直很親密。我問道,他們兩人是否一直都懷有政治抱負?阿披實回答:「我預計到鮑里斯會投身政治,但他很有個性,因此對他來說,從政絕不會是條坦途。但令人稱道的是,他利用他的個性,堅持做真實的自己,走到了目前的位置。」強森曾誇口稱,自己是英國唯一知道如何拼寫「維乍集瓦」的政治家。在伊頓公學,這位未來的總理常常被簡稱爲「維集(英文意思是素食者)」。
無論管理倫敦有多麼困難,公平地說,阿披實面對的政治挑戰似乎遠大於他的老校友。在我們交談時,阿披實的助手正監控著曼谷反政府示威的動態。
阿披實必須找出一種方法,在不激起背後掌權勢力的對抗或不讓泰國陷入新政治危機的情況下,保持對於自己民主和法制信念的忠誠。當被問及泰國軍方權力時,他回答得相當謹慎。
而當我問到難民待遇問題時,他的話語中第一次流露出了鋼鐵般的堅定。「讓我們把事情說清楚吧——他們不是難民,他們只是非法移民。」不過他堅稱,不能容忍侵犯人權的行徑,他補充道:「軍隊總司令已表示,如果有任何軍官牽涉其中,他們應受到懲罰。我認爲,這是相當重大的變化。」當我問道,他是否認爲泰國在減少軍隊在政治中的權力方面仍有一些工作要做時,他平靜地答道:「是的,確實如此。每次當我所在的政黨(民主黨)掌權時,我們都會在這方面努力。」
在爲泰國有權起訴批評君主制人士進行辯護時,他的態度也很強硬。他將泰國「對君王不敬」的法律與英國的蔑視法庭法進行了比較,這些法律旨在保護「政治中立和本應超越衝突」的制度。但這也是有限制的。阿披實說道:「有時,我意識到,法律被濫用了。我們可能也會面臨壓力:該法必須得到公平的解讀。我會努力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他表示,自己已與相關機構談過此事。然而,目前並不清楚,「相關機構」是否會聽這位新總理的話,這是對他權威的初步考驗。
我們的午餐即將結束,但我的部分使命還沒有完成。阿披實還沒有動過他的三明治。但他的助手很想催他快點。他還要接受更多采訪,會見更多全球領袖,當晚他將飛回曼谷——踏入泰國政治的漩渦。
本文作者爲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專欄作家
譯者/何黎
達佛斯,瑞士
杏味丹麥酥(未動)
蘋果餡餅(被忽視)
火腿三明治(被遺忘)
乳酪三明治(還剩一半)
2杯咖啡
免費

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Prince Andrew, Duke of York)再有15分鐘就該到了,而我此刻正爲一件嚴重違反禮儀的事情煩惱。公爵的新聞祕書事先打電話來說,他本人、公爵的私人祕書以及英國駐紐約總領事將陪同公爵一道前來。考慮到就餐人數意外增加,白金漢宮願爲這頓飯買單。與英國《金融時報》共進午餐或晚餐的規則很明確:我們買單。但他們不該隻字不提會有5個人一起就餐。
幸運的是,哈里•奇普里亞尼(Harry Cipriani)餐廳的員工們已習慣於在最後一刻仍爲苛求的客人提供方便。餐廳領班答應,他們可以準備兩份賬單:一份開給《金融時報》和英國王位第四順位繼承人;一份開給後者的隨從。
奇普里亞尼餐廳坐落在紐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的東南角,服務對象是曼哈頓的精英階層。緊湊而開放的用餐空間,似乎專爲到此處炫耀的出版商、交易撮合人和廣告商設計。我聽人說,公爵不喜歡華麗的餐廳,所以我以爲他們訂了一間不顯眼的包間。結果卻相反,我們的餐桌是張貴賓桌,正好處在人頭攢動的餐廳中央。這裏的每個人都在彰顯自己的存在:一位男士笨拙的拍了拍另一位男士的後背以示問候;打過肉毒素的臉頰被親來親去;餐廳領班也在和他的常客們拉家常。
餐廳裏面沒多少地方可待,因此我走到門外。恰在這時,我看到領事館一輛帶有有色車窗的雪佛蘭凱雷德(Chevy Escalade)停在了第五大道(Fifth Avenue)上。公爵從車裏探出身,快步走進餐廳。他的幾位保鏢則消失在人羣中。公爵在桌前坐下,但隨即認定這張桌子太大了。由於總領事留在領事館沒來,因此我們只有4個人就餐。公爵建議我們選擇旁邊一張較小的桌子。我們在那張桌子前擠坐下來,膝蓋幾乎挨着膝蓋,一臉困惑的侍者們很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公爵目前正在紐約對多家金融公司和監管機構作旋風式巡訪,身份是英國國際貿易和投資特別代表。這一角色一半是大使,一半是旅行推銷員,你在商界或政府的其它領域找不到明顯與之類似的崗位。因此,我首先問的就是他如何定義這一角色。
公爵說:「它代表著王室對商界的支援。」正如溫莎家族(The House of Windsor)的其他成員可能會對芭蕾舞團或無家可歸者伸出援手一樣,「商界也需要有人來關注」。
公爵是在2001年走馬上任的。先前,他曾在英國皇家海軍服役22年。福克蘭羣島戰爭期間,他執行過多次直升機飛行任務。他承認自己當時是被「拉去充數」的,因爲他認爲自己在海軍的工作也可由一名非王室軍官來承擔。另一方面,特別代表的角色卻爲他提供了機會,去做一些只有王室成員可以做的事情。
他得意的說道:「遺憾的是,軍官是具有進取精神的。因此,我們更喜歡在接受既定議程後,把它推進到超出我們最初設想、或我們曾認爲有些過分的程度。」
去年,他的工作日程包括628項公務活動,比他在2005年參加的多一倍。他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爲英國石油(BP)、國際電力(International Power)、倫敦勞合社(Lloyd's of London)和力拓(Rio Tinto)之類的公司敲開大門,從阿爾及利亞到烏蘭巴托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對於「軍事與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概念,這位前海軍軍官給出了獨特的、英國式的詮釋。
一位侍者走近前來問我們喝點什麼,滴酒不沾的公爵點了杯蒸餾水。雖然奇普里亞尼餐廳的標識是以一位搖雞尾酒的酒保爲主題,但公爵和我都不打算點該餐廳的招牌酒——20美元一杯的貝里尼酒(Bellinis)。
我問他,過去管理飛行中隊的經歷對他現在的工作有多大幫助?「哦,毫無疑問會有幫助,但這是從非商業導向的角度來看。在我駕駛直升機把武器送往目的地時,我有這樣一種感覺:我是在從事最精英的職業。明白嗎?」他在結尾多問了一句,以示強調。公爵的話風乾脆有力,這也許並不令人意外,因爲他是從女王那裏學的標準英語(Queen's English)。
他繼續說道:「我們[海軍]注意到,90%的國際貿易都是透過海上進行。不過,直到我離開海軍、接觸商界並開始瞭解那些集裝箱裏裝的東西時,我才更加清楚的認識到,商業是繁榮之船的『輪機艙'。」
公爵說,在走上新崗位後的頭三年,他要花部分時間來學習商業基礎知識。但如今他發現,已有數位貿易部長和貿易部官員先後離職,而他卻仍然在任。在仔細斟酌措辭後,他大膽的說道:「我現在的商業智慧可以說比他們略高一些,所以我才能在這個位子上連任。」
我又問道,如今人們對商界和政府的信任度都處在歷史低點,那麼公爵既非商人又非政客的事實,是否是他的另一項優勢?他頓了一下,再次斟酌了下措辭。「我對此的回答是,『沒錯'。就現階段發生的許多事情而言,人們更願意來尋求我的幫助,而不是別人。」他又頓了頓。「可以說,人們依然更信任我們,而不是更信任政府。我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意願和願望。我的願望就是盡我所能爲英國服務、爲英國爭取最大利益。」
公爵今年49歲,頭髮已經斑白,但他身上那套極爲合身的深色西裝,令坐在桌前的他顯得英氣逼人。他叉起一個黃油卷,填在麪包卷裏,然後詳細談起他的這一「自僱」崗位。他說:「我不是在爲別人打工。」他稱自己的工作是幫助英國商界提升綜合實力,以便與背後有遊說集團支援的國際對手展開競爭。
「透過摸清他們想要達成的目標、並在合適的時間出現在合適的地點,我就能夠遊說他們,讓他們感受到羅爾斯•羅伊斯(Rolls-Royce)的優勢。這是爲了敲開大門,方便羅爾斯•羅伊斯進入。奇異公司(GE)的遊說者同我們一樣高效,甚至做得更好……」他頓了頓,然後用軍事行爲打了個比方,來闡明自己的觀點。「比方說你正與美國交戰,他們能夠帶的槍枝要比我們多一、兩支,那麼我們就必須打得聰明一些。明白嗎?所以說,這是一門關於智慧的藝術。」
他在談話中頻頻引用海軍的事情來作類比:「一艘已經靠港的船是根本不需要船長的」,「我的作用體現在白金漢宮之外,體現在我起航出海之時」。
我建議他,或許可以寫一本商業指南,收錄這諸多帶有航海色彩的智語,使它能夠像莎士比亞領導力課程或《聖女貞德》(Joan of Arc)等同類書籍一樣,出現在機場的書架上。公爵說:「我無需寫這樣的書。」他向我透露,在他多年的商旅生涯中,《孫子兵法》一直陪伴著他,「而且,這本書應該出現在每一位商人的公文包裏」。
侍者再次走到桌前,於是我們把目光轉到了菜單上。公爵要與相關方面近距離會面,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若是不小心點到一隻難以下嘴的對蝦,就有可能錯過會面時間;大蒜和貝類自然也不屬公爵當點的食物。作爲一位王子,他的口味似乎清淡得令人失望。
他點了一份「火腿鋦Tagliolini」(Tagliolini是一種義大利扁平細麪條)。侍者問他要選擇綠色的麪條還是白色的麪條。「無所謂。我想我們選綠色的,可以嗎?哪種顏色的在你們這裏最受歡迎?」白色的,侍者答道。「那我就選白色的。」
他轉身問我:「你需要點三道菜嗎?因爲,如果你要點的話……」我沒有選擇開胃菜,只是點了一道蘑菇燴飯。
我認爲,紐約對他來說是與衆不同的一站。因爲在他多年來所到過的其它地方,他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幫助英國公司敲開大門。他承認道:「這裏幾乎不需要我的干預。」作爲阿布扎比王儲(the crown prince of Abu Dhabi)等人的朋友,他可以說對中東和亞洲更爲熟悉。在今年8月蘇格蘭方面釋放洛克比空難製造者一事引發爭議前,安德魯王子曾被考慮作爲英國的代表,出席利比亞方面的慶祝活動。這些活動是爲了紀念40年前促成穆阿邁爾•卡扎菲上校(Colonel Muammar Gaddafi)上臺的那次政變。
令他頗感得意的是,對於某些英國外交官可能都需要撓頭的國家,自己卻應付得遊刃有餘。他指的是2008年前往薩哈林島(即庫頁島)參加一家俄羅斯液化天然氣工廠的開張儀式。與俄羅斯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的「五分鐘會晤」,對說服後者參加20國集團(G20)倫敦峯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安德魯王子表示:「他是位年輕人,毫無應對此類環境的經驗……能讓他在進門後看到一張熟悉的笑臉,會讓事情徹底改觀。」
他此番來紐約是爲了強調英國企業共僱傭了100萬美國人,並主張兩國就金融監管進行跨大西洋協作。他表示,「爲了金融體系的穩定」,兩國金融中心「必須致力於保持步調一致」。
在上次達佛斯會議上,安德魯王子就大膽斷言,伯尼•馬多夫(Bernie Madoff)的龐氏騙局「不可能發生在倫敦」,現如今,他再一次對倫敦金融城推崇的「以原則爲基礎」的監管辯護。在消滅了最後一個麪包圈以後,他開始和我討論自由浮動匯率和保護主義的威脅,並當著我這個金融記者的面,班門弄斧地對銀行都如何處置儲戶的錢進行了追根溯源的解釋。
當我們的食物端上來時,我正在詢問他的例行公事——每年出訪100至120天,有時兩天的行程中要擠進16場會議。他一邊用叉子切開食物,一邊說,關鍵是要在每一次出訪前做足準備工作。他補充道,「這種使命」可能就流淌在他家族的血液中。
「你可以換個角度來看,」他說道。「你對此無能爲力,只得隨波逐流。你只消把它想像成一條輸送帶,你是一件行李,而航空公司將盡其所能,讓這段旅途儘可能地舒適。這超出了你的掌控範圍。那不如坐下來,習慣就好了。」
這是幅令人匪夷所思的畫面:英國王子化作一隻遺失的手提箱。我問他是否喜歡這份工作,但隨即意識到,這個問題在他聽來該有多麼愚蠢——儘管熱愛高爾夫,但他天生就擔負著的使命,讓他無暇享受工作與生活平衡之類的美好事物。
他遲疑了一會兒纔回答,「是——的。有時候,的確令人神經高度緊張,因爲如果你是與某位國家元首會談,就只有我們兩個人。誰也指望不上。」
英國王室被稱爲「公司」,就連王室成員自己也這麼說。我問道,這種類比是否準確?職責和策略從一開始就明確嗎?
「慈善等事情完全是一種個人選擇。我們唯一算得上合作的經歷,就是英國王太后(Queen Elizabeth the Queen Mother)和瑪格麗特(Margaret)公主去世的時候。有一陣子,什麼事都未發生,接著每個人都拿到了一張清單,所有人都坐到一起,『現在我們必須把這件事安排妥當。'」
「每個人都明白,自己必須擁護女王,無論她做什麼,支援什麼。實際上,我們都是分公司,有自己的董事會和管理體系。但完全沒有明確的指示。」
那你有沒有什麼接班人計劃呢,我問道。他簡短的回答顯示,我冒犯到了這位王子。「我們只有一種接班人計劃。眼下我看不到有誰能夠接手,主要原因是他們看到我的工作有多麼努力。」
將王室比作公司很有說服力,大約18個月前,公爵的辦公室找到普華永道(PwC),試圖確定他的特別代表身份創造了多少價值。「我們試圖創造一種模型,但我不確定它是否管用。我很樂意宣稱,我的幫助價值100億英鎊,或者爲英國創造了250個就業崗位,(但有時候)那些公司自己並不知道,」他承認。
一談到損益賬戶成本線,他的語氣就更加堅決起來。他知道長期以來英國小報一直在開銷問題上嘲諷王室。「我沒有收取任何公共資金。女王是自掏腰包資助我的辦公室的,」他表示。「有一點必須說明,我們拿不到任何報銷單。私下裏講,在審計決算之前,都是由我來承擔風險,之後我才能領取報酬。可是我分文不取。」
我說道,這麼說,你這份工作沒有報酬,沒有升職空間,也沒有希望退休。當我還沒有問道,那會是什麼在激發他的熱情時,一陣大笑打斷了我。「答案很簡單,這就是我的人生。這就是我所期待的,不是嗎?我的出身、我所成長的家庭,決定了我只能如此。所以,在我看來,這種生活狀態並無特別之處。對於王室以外的人而言,他們會認爲我神經錯亂了!但這就是我們的職責。」
他一邊表示下一個會面已經遲到20分鐘了,一邊起身,留下我們支付兩份賬單。他轉向兩位祕書說:「回倫敦見。我會起得比你們晚。」在踏上下一段航程、或者說下一條輸送帶之前,他會先享受一頓雞蛋和燻肉——無論在世界哪個角落,他的每一頓早餐都是這兩樣。他的保鏢來了,「我們會根據牀的舒適程度,還有他們做早餐的水準,來給不同地方打分,」他說道。
安德魯•埃奇克利夫-強森爲英國《金融時報》媒體編輯
..................................................
安德魯王子的王室年曆:「花花王子」的一生
威爾•哈洛威(Will Holloway)編寫
1960年 2月19日出生於白金漢宮,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次子,也是自1857年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幼女比阿特麗斯(Beatrice)出生以來,第一位由英國在位君主所生的子女。
1973-1979年 就讀於蘇格蘭北部的高登斯頓學校(Gordonstoun),與父親愛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和兄長查爾斯王子(Prince Charles)均爲校友。有關他風流韻事的傳聞不斷,致使小報媒體戲稱他爲「好色安迪」和「花花王子」。
1979年 決定棄讀大學,加入英國皇家海軍
1980年 從達特茅斯(Dartmouth)的不列顛皇家海軍學院(Britannia Royal Naval College)畢業,隨後接受皇家海軍的初級飛行培訓。
1981年 愛丁堡公爵爲其頒發飛行章,榮獲年度最佳飛行員獎
1982年 加入特遣部隊,搭乘「無敵」號航母,參加收復福克蘭羣島戰爭
1983年 結束前線服役,被皇家海軍航空兵第820中隊指揮官尼戈爾•夏奇•沃德(Nigel 「Sharkey」 Ward)譽爲「一位優秀的飛行員、非常有前途的軍官」。因美國影星女友科•斯塔克(Koo Stark)若干年前曾半裸出現在一部電影中,而結束兩者的關係。
1986年 7月23日與薩拉•福格森(Sarah Ferguson)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結爲伉儷,夫婦二人獲約克公爵和公爵夫人頭銜
1988-1990年 長女比阿特麗斯(Beatrice)出生,兩年後,次女歐仁尼(Eugenie)出生
1992年 約克公爵和公爵夫人宣佈分居
1996年 雙方宣佈離婚,但仍保持友好關係,並共享對兩個女兒的監護權
2001年 正式從海軍退役,就任英國貿易投資總署(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特別代表。到處出訪的工作讓諷刺者爲其發明了一個新綽號:「空中飛人安迪」。
2009年 多年的高爾夫練習終於獲得回報,據傳他的水準足以成爲一名職業球手。人們還誤傳他在自己溫莎城堡的花園裏修建了一座九洞高爾夫球場。
譯者/何黎
紐約第五大道
火腿焗義大利扁麪條,28.95美元
義大利蘑菇燴飯,33.95美元
聖沛黎洛礦泉水(大瓶),11.00美元
共計(包括服務費)94.09美元

眼下,邀中國官員飯局,是越來越難了。約部長級的高官,更是非份之想。習大大反腐,讓中國官員對應酬退避三舍。三個多月前,我約傅瑩午餐,碰碰運氣,畢竟她曾經與FT喫過午餐。那次餐桌上的採訪,是2009年,她行將卸任中國駐英大使、告別倫敦之際。這次約她,她的身份已變: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會議的官方發言人。三月中旬,「兩會」落幕,她答應了這個飯局。
北京崇文門內大街上,立著一幢內蒙古大廈,裏邊是內蒙古駐京辦事處。傅瑩是蒙族,推薦了那裏的蒙餐廳。在首都,每個省份都設有駐京辦,各立門戶,像一塊飛地,伏在中南海眼皮底下,小心呵護與中央的聯繫。每個駐京辦內,有京城最正宗的本省餐館,打拼舌尖上的競爭力。
我提早到了內蒙古大廈。走廊上,出奇地冷落,可能時間還太早,兩旁一溜包房,大門敞開,似無人跡。背景是曠遠的蒙古音樂,我找到「胡楊秋色」。包間不大,中間一圓桌,背後有個沙發區,正中一幅吳冠中水彩畫,地毯的色彩熱烈,有大塊橘色。兩名年輕女服務員正彎腰趴在餐桌上,擺放著三頭羊、一匹馬、一個白色蒙古包。當然,都是玩具,只是讓客人有些蒙古的聯想。
中午11點整,不遠處的長安街上,電報大樓上的大自鳴鐘緩緩敲擊出東方紅的旋律。再熟悉不過的曲子,已敲了半個多世紀。聽到的一剎那,彷彿毛主席走來,有時空錯位的恍惚。緊跟著東方紅漫溢的尾音,鐺鐺的撞鐘聲在空氣中迴盪。窗外,一小片紅灰磚色的老民居,雜亂而破敗。路旁停著不少新的私家車,恍然兩個時代。
傅瑩在車裏發來微信說,她堵在路上,會遲到幾分鐘。在北京,人們已習慣一天辦一件亊的節奏。遲到,是老常態。準時,纔是非常態。推進門的一刻,傅瑩再爲遲到道歉。她穿了件灰色細格西裝外套,白襯衣,一條紫色灰底的圍巾,閒適而不失莊重。與她結識是她出使倫敦期間,一直稱她「傅大使」,再難改口。駐京五年多,我仍不適應王總、李局、周處的官場熱乎。
事先約定,既然是她的家鄉菜,點菜就由她包了。坐定後,我問她,是不是此地常客。她點頭說,常在這家請客,雖然有點貴。平時她與家人去得更多的,是那家呼市辦事處小館子,正宗但便宜。我開玩笑說,爲了這頓蒙古菜,把早餐都省了。她喊過男服務員,神速地報了一長串菜名,好像有奶茶、老額吉奶皮子、奶豆腐、羊排手把肉、蒙古饊子、巴盟酸菜。她說,她喫素,我多喫肉。
服務員輕聲問她,要點酒嗎?傅瑩沒徵求我意見,擺擺手,單方面否決了。聽說,當下官場紀律嚴明。自中紀委公佈「八項規定」後,官員因公餐敘, 除了外事,一律禁止點酒。我喊住服務員,對傅瑩說,今天你是FT的客人, 我做東 。喝點你們老家蒙古酒,總可以吧?傅瑩倒也爽快,那就喝點吧。問我,低度的,還是高度的?想到蒙古人的豪氣,我說,高度的吧!服務員拿來一瓶 「蒙古王」,烈酒,53度。一看產地,內蒙通遼,傅瑩的老家。
前年基辛格訪華,傅瑩在這裏宴請了他全家。她說,那是基辛格第一次喫蒙古菜。服務員向他敬酒,獻哈達,肉食一道道地上桌,他喫得盡興。我說,在釣魚臺今年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剛見過93歲的基辛格。他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前駐美大使張業遂對話後,被一批VlP粉絲圍住,動彈不得,最後還是傅瑩上臺挽著他走下講臺,成功營救。我看到,基辛格滿臉父輩的滿足。
我問她,1971年,基辛格祕密訪華,之後四十多年,訪華上百次。他對中國的看法有大的修正嗎?
「我認爲他比較穩定。這並不是說他的觀點沒變,而是沒有脫離中國的實際。當別人覺得中國不行的時候,他沒有對中國失去信心。當別人覺得中國可怕的時候,他也不會跟著那股風走。每次來中國,他要跟中國領導人談話,也要接觸普通中國百姓。你看他評論中國,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講中國人民的生活,這是他親眼看到的。對中國,他從來沒有迷失過。那麼多研究中國的人都會有恍惚和搖擺的時候,對中國的預言錯了或者沒看準的時候,他很少有這種情況。」 對這位中國的老朋友,她顯然頗有好感。
一大鍋羊排湯上桌。服務員爲我們衝滿奶茶,斟上一小杯「蒙古王」。傅瑩催我下筷。我把話題引到剛去世的新加坡開國之父、與基辛格同齡的李光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年輕的女外交官傅瑩曾是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中國領導人去新加坡訪問。有時候李光耀會設家宴,就在他家後院裏,很溫馨,燈光、燭光。他挺關心人的。翻譯沒有那麼多時間喫飯。有時甚至沒有桌牌,不上桌的。他就把紅毛丹剝了,遞給我,讓我趕緊喫。」
傅瑩最後一次見到李光耀,是去年在獅城的香格里拉對話。我很好奇,李光耀與幾代中國領導人交往,一直很直率,常常醜話在先,風格強悍。從鄧小平、趙紫陽到江澤民,倒都能接受他的風格?
你說,中國領導人不接受誰的風格?傅瑩反問我。
「我在外交這個行業幹了一輩子,從當翻譯到直接參與。中國領導人和外國領導人的交往,一直是有交鋒的。外交這個東西,就是有來有往,是有事要談。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不同,相互間肯定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毛澤東、周恩來這代人奠定的外交理念特別好: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平等對待。能幫你的,幫你。辦不了的,也告訴你爲什麼。我想讓你辦事,也會有你幹得了和幹不了的。利益問題上,各國都有自己的位置......李光耀最大的貢獻,是他從新加坡的利益考慮。有的人批評他,認爲他這樣或那樣。你不可能指望他從中國的利益出發......」
我們開始喫手抓羊排。看傅瑩優雅地處理羊排。我暗忖,手抓的美食,看來很難進入國宴的菜單。如果兩國領導人能在國宴上一起喫手抓羊排或大閘蟹,雙邊關係一定鐵得牢不可破。
「對外交往當中,不能說什麼事都自己拿著,需要在得失之間權衡。有必要的話,該放手就要放手......這裏頭,還是要有是非觀的。」
服務員又斟上一杯「蒙古王」。
「近代以來,中國外交從哪兒開始的?西方國家的外交,源自戰爭,需要停火、談判,包括劃分殖民地。中國外交,是從改變屈辱地位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始的。鴉片戰爭後相當長時期,中國的外交是被別人強加來的。我在英國當大使時,瞭解過19世紀、20世紀這段歷史。中國的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怎麼去的?是被英國人逼著去那兒,租給你一幢房子,請你來看看大英帝國是什麼樣子,要你接受他們的很多要求。清王朝被迫在英國開了公使館。多年後,1942年民國政府的外長宋子文赴英,要求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而不只是宗主權,被拒絕。直到2008年,英國人還只是承認中國對西藏有宗主權,而不是主權。2008年我作爲中國大使與英國人就這個事談了多少個回合。時任總理溫家寶和來華訪問的英國首相布朗在釣魚臺喫晚飯,一直講這個事,講「西藏問題」的由來。最後,英國明確承認了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1949年以前的中國積貧積弱,在國際上沒有地位,個體的外交官再出色,也難有作爲。」
現年62歲的傅瑩,是幸運的。文革中,她在內蒙插隊三年,做過廣播員,放過露天電影,後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學英語。進入外交部後,再到英國留學攻讀國際關係。她出使的第一個國家是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她是中國的第一位蒙古族大使、第一個派駐要國大使,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外交部第一位女性副部長。文革中,毛澤東的外甥女、文靜的王海容,曾曇花一現,出任外交部副部長。
傅瑩很想多聊聊她現在的工作:中國人大。我告訴她,我連續跑了五、六年「兩會」,仍很困惑。一些代表坦承,人大的功能至今仍是一枚橡皮圖章。我說,每年「兩會」,搭出租車去天安門,司機都不願去,都怕那個地方,擔心被罰,警察要趕。他們不覺得人民大會堂裏發生的事情跟他們有什麼干係,帶來的只是麻煩,也不知道誰是他們的人大代表。
她顯然不滿意我的說法,喝了口奶茶:「在英國,每年議會開會,第一次女王演講,也是打不到車的吧?沒有哪個計程車司機會往西敏寺那兒跑,進不去出不來的,這種情況在哪兒都一樣。交通不方便,司機肯定不願意去,這完全可以理解,要尊重他們。」她就我對中國人大制度的責疑,作了一個有關交通管制的解讀。
2013年傅瑩轉任中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之前,一輩子的歷練和積累,都在外交。如果讓她選,她會去政協。她的先生、民族學家郝時遠在那兒,很多資深的大使也在那兒。現在她倒喜歡人大這份工作了。她說,如果年輕時有選擇,或許會選讀法律。在她看來,法律與外交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她更心儀確定的東西:「法律很嚴謹,是非很清楚。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沒有那麼多灰色地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潛意識裏,她或許想在法律中尋求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在她早年的動盪生活中顯然不存在:「我是經過文革的,知道無法無天是什麼概念。突然有一天,有人把父親拉走了;突然有一天,母親不能按時回來了; 突然有一天,學校不上課了;突然有一天,別人可以當兵你就是不行,別人可以進工廠你就不行。社會的規則和秩序都沒有了,這是很可怕的。」 文革中,時任內蒙古軍區宣傳部副部長的父親、一位有書卷氣的軍人,遭受迫害。
我已喝空了第三杯奶茶。傅瑩顯然已感覺到了我對中國人大制度的深度疑慮。
「人大制度需要不斷完善,很多法律可能不是很完美,執行也不一定很完美,肯定要有一個過程。但是,老百姓的感覺也不可能超越現實。如果沒有做得那麼好、沒有做到,你想讓老百姓覺得做得特別好也不可能。老百姓有不滿意,我覺得挺自然的。可能外國人看到中國老百姓有這個不滿意、那個不滿意,好像就證明中國怎麼了!其實我在英國、澳洲時,看到人們不滿意的地方多去了。對中國的決策層和立法機構來講,知道老百姓有什麼不滿意是很重要的,要知道老百姓哪兒不滿意,搞清楚爲什麼,怎麼解決。」
一大鍋羊排,停在桌上。對她的解釋,我有所保留。FT的餐桌上,總得有點茶杯裏的風暴吧。
我說,人民大會堂裏,中國人大開會的方式幾乎與五十年前一樣,仍是蘇聯時代的。當然,現在配備了表決器,是個進步。不過領導人坐檯上,代表坐檯下。很多代表只是在舉手和拍手。中國人大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太慢了?
「人的期望,永遠比現實要高,否則就沒有意思了。但是,對外國記者來講,我也比較理解。因爲你們看到的只是表面、外在的東西。對裏面的東西,你們能看到的就比較少!人大有責任依法監督政府,有時我們提出的意見也是很尖銳的,但是目的不是讓政府難堪,而是希望政府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好,告訴他們哪裏有問題,希望改進。所以,人大不監督有責任,政府不改進也有責任。」傅瑩回答得很坦率。
我說,外國記者確實看不到啊!
「你們可能看到,我們人大的報告很少有被否決掉的,雖然否決票在上升。我們人大常委會開會,每個法律基本上都能透過。這是因爲我們在審議和溝透過程中,花了很長時間去尋求共識。比如立法法修正案,已經過了二審,也向社會公佈過,經過專家們的千錘百煉,再拿到會上。將近三千代表討論,一千多人發言。根據這些意見,做了七十多處修改。如果不改,硬扛著,投票的結果就不一定了!」
她又提到英國,她最後出使的國家。她說,這種情形下,估計英國國會不會改,只要能透過就行。中國則是連夜開會,晚上討論修改,甚至作很重大的修改。再解決不了,還要到代表團一個個去解釋和說明。表決時,雖然有人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但是大部分代表會投贊成票。
我決定與中國人大發言人抬扛:「兩會」加起來,會期長達15天。坦率地說,旁聽兩會,相當一部分議程並非議政,不少代表更有興趣的是拍照留念。不少省份,人大代表的發言還要事先審查把關。審議報告時,更像是向領導同志彙報工作或表功。 如果連人大代表都信不過,他們如何議政?
「如果你們記者在,肯定要小心。要是我,也會小心講話。你們記者多厲害,到時候如果報不準,說歪了,現在這個時代,資訊傳播很厲害。」
傅瑩半開著玩笑,夾起一塊奶皮子,作出反擊: 「話說回來,英國議會里,有時議員念稿子那麼長時間,下面一個人都沒有,電視上誰看?!政治裏肯定要有些程式性的東西。」
我夾起一條羊排,繼續發問。我說,每年採訪「兩會」的中外記者,多至三千人。那麼多記者,總得有事情讓他們報導吧。除了聽李克強總理花兩小時,一口氣唸完長達40頁的政府工作報告,記者能採訪的人和事極其有限。
「西方媒體看中國,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層是對這個制度是否認可,再一層是這個制度運作得怎麼樣。比如我有時候跟一些歐洲記者辯論,準備記者會之前我要開好幾次圓桌會,辯論非常激烈。他們根本上就不認可中國的制度......你橫說豎說都認爲你們不對。他們的參照系數就是自己的制度。德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英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美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我只能耐心地跟他們講,我是幹這行的,已經講了三十年。有這個耐心,繼續講!」
聽得出,素來談吐溫婉的傅瑩,語調裏已有一絲不悅:「他們從根本上不認可你這個制度,所以看不懂,也不可能看懂,甚至是拒絕看懂。」
每年「兩會」都爆出不少「雷人」提案。你對人大代表的產生機制和議政能力,印象如何?
奶茶再添一壺,午餐已過半。我接連喫了幾條蒙古饊子,補充能量。她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她解釋說,批評不是壞事。中國的人大制度是有效的。聽到此,我耳邊響起人民大會堂內數千代表聆聽報告時,檔案翻頁時整齊劃一掠過全場的聲響。
傅瑩當然清楚,中國的人大制度不乏批評者。作爲發言人,她當然相信這個制度:「人大制度的好處,在於它有方方面面的人,帶來方方面面的資訊,讓這個國家沒有死角......外界特別看不懂的是,爲什麼中國13億人口能夠治理得這麼好,總能不斷往前走,總能解決問題?!」
我說,是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取得了決策的高效率吧!很多西方領導人到中國訪問,一方面覺得北京的制度有問題,另一方面又很羨慕,覺得這個制度至少有效率,能辦成事情。
「你說中國集權?……西方說我們集權,所以有效率。我認爲這是一種偷懶的說法。他們的制度走到今天,有它的道理……誰跟誰比較,不太好說。你解決不了問題,是你的事。我能不能解決問題,是我的事。西方人容易一會兒說中國多好多好,一會兒說中國多差多差。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好,也沒那麼差。」
這段話,我曾在另一個場合聽她說過,是她的直覺,也是深思熟慮的判斷。即便輕聲細語道出,骨子裏仍有點咄咄逼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高收入國家元氣大傷,效率滯緩,對自己制度的自信似乎打了折扣。他們開始羨慕中國的效率、成長與速度。他們不再責疑,而是尋找「中國模式」的合理性。他們高調地向中國領導人伸出大姆指。我明白傅瑩這番話的底氣。
我換了個話題,問她,可否請張德江委員長向李克強總理建議一下,政府工作報告能否簡短一些,也不用全文通讀?
「過去也有較短的政府工作報告。凡事都有它的原因。你說哪個領域的事兒能漏了?水利不說?農業不說?工業不說?都得說!誰重要?誰不重要?!中國這麼大,發生這麼多事,讓總理去取捨也很不容易……政府報告有動員人民的任務。你在這兒聽兩小時,感覺時間長。但在很偏遠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決策怎麼回事。聽上兩小時,就可以把過去一年的事弄明白了。」
中國的事情,越來越多。看來政府工作報告只會越來越長。我說。
「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前人沒有經歷過,想都想不到。就像霧霾。在英國,一個時期是煙霧,一個時期是工業汙染, 一個時期是汽車尾氣,是遞進的。而在中國,全都一起發生,結果就產生了新的化學反應,形成一個新的東西。」
出任人大會議發言人兩年,平時低調的傅瑩已成公衆明星。過去兩年,媒體和民間對她記者發佈會的表現稱讚有加。我問她,有沒有聽到過激烈、刺耳的批評?
「能聽到批評!家裏人的批評更直截了當。我先生就關心我的語病。去年,他就批評我講話時 『這個這個』太多了。今年發佈會前那個晚上,他在政協開會,特地跑回家一趟。見我正焦頭爛額地背詞,就給我寫了一張紙。早上我看到了:在『呃』旁邊打了X, 『這個』旁邊寫了X,意思是不要說這幾個字。發佈會那天,我在臺上,就把這張紙放在檔案夾的左手,一低頭就能看見,提醒我克服語病。他認爲,這些語病讓我的講話顯得鬆散,反正他不喜歡。」
很少有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自嘲,或表露內心的不安全感。傅瑩是例外。她說,直到現在還沒有看過自己新聞發佈會的影片。 她不敢看。「看到有毛病,我會後悔死了。 」
今年「兩會」,作爲人大代表的傅瑩,她的提案仍是有關中國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河流如何維護、界河泥沙如何及時處理、錢從哪兒來,邊境道路維護,沒有路怎麼辦。「我咬住一件事,能辦好就不錯了。」
你覺得媒體可怕嗎?我問她。外界向來覺得傅瑩很會與媒體打交道。
「挺可怕的!」 她說,她對媒體的戒備, 因於她的慘痛教訓。在菲律賓和英國當大使時,媒體採訪時,挖了很多坑,不留神就掉進去了。
我把話題挪到當下熱到發燙的話題-「一帶一路」。我問她,對中國,是不是過早了?
「九十年代,歐亞大陸橋曾經談得很熱火,但一直是紙上談兵。二十年後,中國條件有了,資金也有了,可以付諸實施了,怎麼就成問題了呢?我們現在幫著大家實現歐亞大陸橋。歐洲以外可能沒有人記得了? 也許他們換代了!」
傅瑩說話,很少提高聲調。雖然她已遠離外交圈子的談判桌,她的直覺與反應仍是外交官的。該機敏時機敏。該尖銳時尖銳。該溫情時溫情。所有的註腳背後,都在國家利益。
午餐,快臨近尾聲。在領導人習慣統一染烏亮黑髮的中國,有人問過我,一頭銀髮的傅瑩,是不是有意染白的?我問了多年來一直想問的問題。傅大使,你的一頭白髮,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頭頂有白頭髮比較早。後來白得更多,就開始染髮。在英國生活期間,我看很多人頭髮白了都不染,我也就放開,不染了。」
你平時怎麼放鬆呢?
「走路、散步。」 她答。
我說,北京好像已經不太適合散步吧。
「只要天好,還可以。我在家裏,可以在跑步機上走路。 我還是喜歡看書。書是另一個天地。」
我問她,一年裏,她的先生能喫上幾頓她做的菜?我知道,在家中,她是很享受的。她先生是主廚,廚房是他的領地,不放心太太動油鹽醬醋。傅瑩只有洗碗的份兒。談起家裏的事,她從剛纔討論地緣政治的緊張中解放出來。她的臉上,寫著小小的得意與滿足。
午餐已過兩個半小時。最後, 我們又滿上一杯「蒙古王」,算是收尾。她小喝一口,笑著說,有點微醺。我說,今年「兩會」,據說習大大在會見一個省市代表團時問道,代表們聚餐喫得很乾淨,是不是最近油水少了?
「中國這一段時間,大力度反腐敗,大家都挺有感觸,揭露出來的事情觸目驚心。十年前,都無法想像,不能理解。有的官員,貪的錢一輩子都花不掉。這個國家、這個制度、這個黨,確實應該解決腐敗問題。」
她站起,披上搭在椅背上的紫色圍巾,匆匆告別。
桌上好幾碟菜,沒怎麼動。與FT午餐,喫飯好像永遠是個美麗的藉口。這頓午餐,按中國官方標準顯然有些「超標」。看了賬單,這瓶「蒙古王」要價頗高,近人民幣600元。我趕緊讓服務員把剩下的半瓶酒打包,帶回編輯部。
菜單
北京崇文門大街,內蒙古大廈
醇香奶茶 1份
香酥炒米 1份
老額吉奶皮子 1份
醇香奶豆腐 1份
蒙古饊子 1份
金帳手把肉 2份
巴盟燴酸菜 1份
莜麪窩窩 2份
熱湯 2份
蒜蓉西蘭花 1份
拔絲奶皮子 1份
活性阿爾山500ML 1份
經典燒麥 1份
經典大帳蒙古王 2份
服務費:228元
消費總計:1746元

陸克文(他出任過澳洲總理)從小生活在昆士蘭州(Queensland)的農場,常用奶牛飼料堆築城堡。「你明確自己的人生方向了嗎?」每當陸克文因陷入憧憬而耽擱了放牛活的時候,暴跳如雷的父親總會這樣問瘦弱的陸克文:「是打算養肉牛還是養奶牛?」
陸克文說起這段往事時笑了,但笑聲中帶著淡淡的哀傷。早在他出任總理前,在他學習中文併成爲外交官前,甚至在他還不滿12歲時,父親伯特(Bert)就因車禍而撒手人寰。父親的離世深深影響了陸克文以後的人生道路,也讓他在內心深處立下了終生宏願:改善澳洲的醫療制度,他認爲它對自己父親的死難辭其咎。「父親是個非常不錯的人,」陸克文在之後的會談中總這樣告訴我。「我想人人都這樣評價自己的父親。」
但陸克文的童年相當不幸。他父親過世後,母親馬格里特(Margaret)及全家老小(陸克文是家中四個孩子中的老小)被趕出了農場,他們原本是農場的佃農。陸克文記得被趕出農場時「農場主的種種非難」——具體細節頗具爭議——全家被迫暫時棲身於一輛車內卻是不爭的事實。陸克文成了某天主教寄宿學校的「全額資助生」,他很討厭這兒的生活,不久他轉至本地一所學校學習,成績優秀的他開始嶄露頭角,並透過學習開始了自我救贖之路。
我約好與53歲的陸克文在他布里斯班郊區的格里菲斯(Griffith, Brisbane)選區會面。他如今是朱莉婭•吉拉德(Julia Gillard)內閣的外交部長:他的一位顧問告誡我陸克文不願談及「6月24日的事變」。
就在去年6月24日那天,在一場無情的政治伏擊戰中,吉拉德宣佈她將透過黨內投票挑戰領導權後,陸克文短暫(從某些程度說不俗的)的總理生涯戛然而止。看到鐵定的敗局,陸克文宣佈辭職。
2007年陸克文作爲工黨領袖以壓倒性勝利擊敗連續執政長達11年的保守派領袖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後,曾在國際社會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他上臺採取了一連串動作中,他首先批准了《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完全推翻了其前任對氣候變暖理論的對立政策——而且向該國原住民作了感人肺腑的道歉,這個歷史了斷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澳洲本土。能說一口流利漢語的陸克文把自己定位爲能自如應對中國的首位西方領導人。
民調錶明他是澳洲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總理。然而,2年半後,他被那些一直不喜歡他的本黨黨員拉下馬,當其名望開始急劇下跌時,他們拋棄了他。
裏弗茶室(Riverbend Teahouse)在書店外的木質陽臺擺了十來張桌子,顯得樸實無華。雖然布里斯班一直遭滔天洪水肆虐,但南半球今天這個夏日的天氣不錯。
陸克文來時,周圍有人認出了他,互相竊竊私語。他的身材比我想像中要高,黑色西服裏面穿著白襯衣,濃濃的白髮與他那張天使般的臉顯得不太相稱。他翻看酒水單時神情顯得很放鬆。「我看咱們就來個獼猴桃汁,」他對服務員說。「哦,這位記者是英國人,所以就給他來個瓶裝的,」 他挪揄道。
他說起話來語調溫和,幾乎發人逗笑。他說自己一上午都在布里斯班板球場,雖說今天是週六,但輪他值班。「我早上的工作就是向來訪的中國代表團介紹板球比賽的精妙之處,」他說。陸克文不得不用上他出衆的漢語,他在澳洲的大學主修的是漢語,曾到臺灣學過漢語,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駐北京使館任外交官。我問他如何用漢語解釋板球比賽中擊球員違犯規則用腿截球(leg-before-wicket)。「就好比你站在三根竹竿前,」陸克文給我示範他是如何解釋這高難度規則的。
服務員端來了我們點的Rapaura Springs,這種白蘇維翁葡萄酒(Sauvignon Blanc)最適合夏日裏飲。「那麼,你想採訪點啥?」他直奔《金融時報》午餐會採訪主題。但我感覺他的輕鬆神情是裝出來的。(我曾對他的顧問說自己想了解作爲普通人的陸克文,而不是政治老學究的陸克文。)「我想點蒜末烤麪包(bruschetta),」他正色道,嚴肅得就如同在音樂廳一般。「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就是喜歡蒜末烤麪包這道古老的澳洲菜,得稍微帶點義大利風味。然後嘛,我再來點義大利燻火腿沙拉,始終不離義大利主題。」雖說不情願,但還是順著他的意點了蒜末烤麪包,主菜則點了壽司大拼盤,點完後才意識到這種搭配顯得不倫不類。
我把話題轉向他的先祖托馬斯•路德(Thomas Rudd),他在1789年從倫敦被流放至澳洲。「我的先祖是個普通人,」他說,給這個頗具傳奇的故事開了個奇怪的開場白。「他當時17歲,在倫敦當清潔工,一個廚房女傭指控他躲在房子樓梯後在一雙鞋上劃痕。」托馬斯沒趕上押解囚犯到澳洲、待遇相對人道些的「第一艦隊」(First Fleet)。相反,他被押送上被稱爲「死亡艦隊」(the Death Fleet)的「第二艦隊」。爲節省費用船隊改由私人經營,並按每位囚犯付給承運者費用,而不按押到澳洲之後每個活人計算費用。「當時最奇怪的競標狀況是船上剩下的食物歸最後的競標者,事後對方可以出售,」陸克文說:「《金融時報》的讀者都能理解。」承運商是個西非奴隸販子,適度削減每個囚犯的定量食物。所有犯人在船艙底下手腳被鎖鏈銬著,最後(到澳洲時)約有四分之一的人被餓死。
「我的先祖僥倖活下來了,」陸克文繼續說,又給我講了他先祖托馬斯在澳洲服滿7年刑期後,如何一路打工繞道中國回到英國。他再次被判有罪,這次的罪名是偷了一袋糖。「據我所知,這是唯一一個兩次被判刑,又兩次流放澳洲的囚犯。」第二次刑滿釋放後,因寬大處理政策,托馬斯獲賜雪梨城外一塊地。他去世時70歲,最終成爲受人尊重的良民,更活生生地體現了公共政策如何支配人的生殺大權,先是由於一個小罪名把他流放澳洲,並透過給他自力更生的手段讓其最終改過自新。
服務員端上用長長的薄盤子盛的四塊蒜末烤麪包,它上面蓋著意式乳清乾酪(ricotta cheese),又堆了多汁的紅黃色番茄,還用新鮮的紫羅裝點,看來這道菜點對了!我邊喫邊聽,當陸克文說到2008年二月他向 「被偷掉的一代」(lost generations)原住民孩子(他們被強制從自己家中擄走)道歉時,我舉著滿叉子的食物停在半空中,聽得入神。
「我從小在澳洲鄉下的農場長大,與原住民基本沒啥接觸。當然,隨著年齡的成長,我越來越清晰地覺得只有對過去有個交待,整個國家方能向前發展。陸克文自己撰寫了演講稿,又擯棄了好多稿,因爲覺得不是矯揉造作就是太具情緒化。他說得字正腔圓。「因爲這是我作爲澳洲總理發自內心的心聲,事後也達到了應有的效果,因爲我所說的一切全是事實,」他說。「出乎所有澳洲人意料的是全世界目睹這一事件後的反應。我認爲澳洲人(包括我本人)沒有意識到的事實是:我們粗暴對待原住民這一段歷史,全世界一直頗有微詞。
服務員過來把盤子端走。「這位記者話太多,」陸克文朝我點頭示意,開玩笑說道。事實上,從頭至尾滔滔不絕的是他,喫起東西來也是狼吞虎嚥。
我想了解他對中國的看法。很多澳洲國民對這樣一位漢語流利、但又明顯缺乏西方背景的總理頗爲失望。就在我們午餐會後不久,據維基解密(WikiLeaks)透露,在對華政策上,陸克文稱自己是「無情的現實主義者」 (brutal realist on China),並向華盛頓建議如有可能,應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倘若不行,就應對華強硬。他對我這樣說:「中國是全球之希望所在,而有些人則是持極度悲觀看法。總而言之,我仍屬樂觀陣營。」但他對人權仍抱有「契約式的信念」,此舉必然會使其與北京發生衝突,他說道,所指就是他願意就人權問題對中國領導層進行公開說教。
他給我倒了點水,當意識到是把水倒進了我酒中後,連聲說對不起。我們要的第二道菜端上來了,他要的是由搗碎的義大利燻火腿、蘋果、核桃以及藍色乾酪調料(Blue Cheese Dressing)的沙拉拼盤,我要的則是各式加州麪包卷。中國扼殺了他在哥本哈根氣候峯會達成協議的夢想,爲此是否有被出賣的感覺?他曾告訴澳洲記者,說到底,自己被北京愚弄了。他露出一絲疲倦的笑容。「我覺得中國應該能做得更多,我認爲他們不熟悉高層談判這一套,」他說。雖然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峯會上是個蓄意阻撓者,但他不認爲峯會是個失敗。「若用地震學上的里氏1至10級來衡量的話,我認爲此次峯會相當於震級6級。」
但澳洲國民可不這樣看待問題。正是在哥本哈根氣候峯會後,他與澳洲國民的親密關係開始惡化。在他撤回本國排放交易計劃的提案後,他的民意支援度掉到了谷底。國民普遍認爲他擯棄了原則立場。在參議院兩次否決該提案後,他還堅持認爲自己只是作戰術性退卻。「在公關戰(我承認自己這次失敗了)中,它只是視爲沒有決心而已。」
一直以來,相比自己的政黨工黨,陸克文與公衆的關係更爲融洽,工黨認爲他不合羣,是披著政客外衣的政治老學究。我先從他試圖徵收「資源附加稅」說起,委婉地追問他突然辭職的原因。在這件事上,他未付諸努力去達成政治共識,甚至事先都未告知礦業部長。「這些事爭議較大,在本次會談或其它任何場合,我都不想再對我稱之爲6月24日事變詳細闡述,」他嘆說道,所指的就是那次不同凡響的所謂黨內政變。
我另起話題,這次提及的是《雪梨晨鋒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澳洲本國記者大衛•瑪爾(David Marr)對他大肆炮轟之事,此事廣爲人知,他說陸克文缺乏政治智慧,疏遠政治顧問與同事。陸克文給人的形象是粗魯、難以親近——「見教皇都比見陸克文要容易」——自以爲是、狂妄自大、做事偷偷摸摸、冷漠,是個控制狂。那您認識到上述問題了嗎?「這是你企圖委婉地再次引出6月24日事變的話題,」他說,這一次有點生氣。「我不會改變我的做事習慣:再不在公開場合反思那些我認爲於事無補的因素(雖說原因很簡單)。」然後他又補充道,語氣稍爲舒緩了些:「我和所有的凡人一樣,難免有缺點,也會做錯事。」
我一直小口吃我點的壽司,米飯有點硬。他則努力喫著沙拉。陸克文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告訴我一個故事:在羅馬,他有位聰明絕頂的耶穌會(Jesuit)朋友,對方的主要工作就是做他所謂的「膚淺問題全球化」。陸克文說人類以前很少面臨如此錯綜複雜的問題。「對政治人物的要求越來越高,但我們身心卻毫無準備。」
其中一項要求是:現代政客就得先有強健的體力,他們得24小時全天候關注層出不窮的國內新聞,還得跨越多個時區去參與處理全球事務。他記得2009年4月的倫敦G20峯會,世界領袖們當時圍坐在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國宴桌時,滿眼所視是「無盡的深淵」。「我們當時坐在那裏,筋疲力盡,都不知從何著手,都知道只有齊心協力共同採取行動……否則全球市場將會崩盤。」很顯然,不該任由亂局如此發展下去。
陸克文又叫來了服務員。「這位大英帝國的子民想要點茶,」他說。「我喝咖啡。」然後作了總結性發言:「我篤信政治,因爲它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是:『你代表何方利益,什麼原因?』其二是:你明白自己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從孩提時代埋頭擺弄牛飼料起,陸克文這位有執著信念的政治家就一直在思索這些問題,他也能夠問心無愧地做出肯定的答覆。潛臺詞是:這個世界上,我們不得不硬著頭皮打交道的很多領導人是做不到的。
戴維皮林是《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裏弗茶室:布里斯班布林巴(Bulimba, Brisbane)
2份小西紅柿義大利乳清乾酪蒜末烤麪包:22澳元
義大利燻火腿沙拉:16澳元
壽司拼盤:15澳元
Rapaura Springs白蘇維翁葡萄酒:38澳元
茶:6澳元
咖啡:3.5澳元
總計(包括小費):122澳元(約76英鎊)

53歲的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擔任盧安達總統已經10年,之前還擔任過七年副總統——實際意義上的領導人。但即便多年執掌權力以及擔任軍事領導人,他仍然與當年36歲擔任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 RPF)游擊隊領導人時一樣身材瘦削與不苟言笑,反政府武裝RPF結束了20世紀曆時最短的大屠殺——1994年4月至7月間,約有80萬圖西族(Tutsis)與胡圖族(Hutu)的支持者慘遭殺戮。
卡加梅執政後,我們曾見過幾次面,但這是我倆第一次共進午餐:他正在倫敦出訪,於是就提議在切爾西港溫德姆至尊酒店(Wyndham Grand in Chelsea Harbour)會面,這是一家價位高但又不起眼的酒店,它的餐廳並不知名。我們的午餐由總統出訪代表團的隨行廚師烹製。卡加梅的助手事先向我保證說這一切並非出於擔心投毒,而是方便整個團隊的安排——可以給全部隨行人員做飯,以及過去住酒店時餐飲老是變來變去——對此我算是半信半疑。卡加梅政府如果不是組織得力,還用以前一門心思打游擊戰的策略處理國家的發展問題的話,將一事無成。
卡加梅接手的國家已經潰不成國,大屠殺期間,政府機構遭摧毀,人民被殺戮。在接下來的幾年,盧安達政府讓幾百萬在衝突中流離失所的民衆回國;幾十萬件大屠殺罪行也已由村民委員會進行審判(參閱下面的表格)。
而且近幾年來在國際社會的援助下(目前政府預算差不多有50%仍依賴於外來援助),盧安達取得了非洲大陸最快的經濟增速。然而卡加梅卻是非洲領導人中最具爭議,也是最具兩面性的政治人物:一方面,這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力圖在一片廢墟上建設一個富裕的國家,而且義無反顧地突破非洲大陸的諸多禁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雙手沾滿鮮血的暴君。國際社會指控他犯有戰爭罪及濫用人權罪,指控的次數絲毫不亞於其獲授的榮譽博士與全球傑出領袖獎的次數。
下此結論的依據是卡加梅過去幾年貶褒不一的從政經歷。與其他非洲領導人不一樣的是,卡加梅百折不撓地追求結果,旨在把盧安達這個封閉保守的山地國家變成該地區服務業、農產品加工、旅遊以及交通運輸的中心。但他又被授予了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巨大權力,基加利(Kigali)政治精英的財富至少有部分來自透過對鄰國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發動侵略戰爭、掠奪礦產資源得來的。
根據聯合國(United Nations)的報告,爲了解決現存圖西族所面臨的與日俱增的威脅,卡加梅著手確立權威,同時確保邊境安全,導致成千上萬的盧安達人與剛果人死於其軍隊之手。政治反對派與記者的結局仍然不是流亡就是關進監獄,有些情況下甚至遭到活埋。
然而,在國際社會的支持者中,卡加梅仍然不乏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美國福音教會牧師華理克(Rick Warren)、以及星巴克創辦人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 of Starbucks)這些西方有頭有臉人物的支援。他的擁躉往往對其統治中出現的殘暴行爲視而不見,轉而支援這樣的理念:卡加梅所做的一切對於恢復國家安定,奠定發展基礎是必需的。
在溫德姆至尊酒店這間匿名、略顯苦行僧式的會客室,廚師給我們上了胡蘿蔔番茄湯。卡加梅說,「我無愧於自己,無愧於我爲祖國與人民所做的一切,我無怨無悔。」我倆喫飯的圓桌鋪著白布,上面擺著銀餐具,有點象鋪著空地毯的沙漠中的綠洲。
更爲廣闊的國際社會更加引人關注:卡加梅雖然很放鬆,但絕非閒聊之輩,我們的會談很快就轉向了象牙海岸(Ivory Coast)衝突、席捲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運動以及在撒哈拉以南國家的衝突與革命。「這並非昨天才冒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大家過去並不關注,因爲視而不見符合其自身利益,」他的看法是貪腐、社會不公以及鎮壓反對派引發了阿拉伯社會的動盪。
這樣的言論也許會激怒他的詆譭者,因爲它真真切切出自一位國家元首之口,卡加梅不允許出現強有力的對手來挑戰他的權威。他在2001年囚禁了前任總統巴斯德•比齊蒙古(Pasteur Bizimungu),原因就是對方組建了反對黨。但卡加梅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基本以農業爲主),使本國經濟元氣大爲恢復(只要去過盧安達的人都可親眼目睹),而卡加梅的詆譭者幾乎做不到這些,所以這一點讓他極爲憤怒。
卡加梅竭力爲自己所踞的道德制高點辯護,於是毫不留情地抨擊西方社會的罪責:在盧安達最危難的時候卻袖手旁觀。「我覺得媒體、聯合國以及人權組織沒有任何道義權利指責我本人或者盧安達。因爲一談到盧安達以及剛果面臨的問題,他們都是口惠而實不至,」說著就慢慢地喝完了碗裏的湯。
卡加梅很反感成爲國際援助受惠國後所牽扯的問題——從施贈國那種以恩人自居、盛氣凌人的做法到對待非洲政策反覆無常的本性——他對西方社會的謊話連篇與雙重標準極度敏感。他說話諷刺味很濃,他暗示西方政府過去由於關注阿拉伯世界的穩定勝於其自由與良治,從而引發社會動盪實屬因果報應,言語之中帶著譏笑。「西方社會必須正視本人所指出的現狀,他們絕不能視而不見……」
卡加梅繼續說,要說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對撒哈拉以南國家有何深刻啓示,那就是警示那些不爲民謀利的執政者如若不然的下場。「你可以高高在上,誇誇其談,滿世界遊山玩水,讓國內百姓對你歌功頌德。但政府如果辜負民衆期望,不密切聯繫羣衆……最終結果是聲名掃地,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菜單上的下一道菜是卡加梅的廚師爲我們準備的用豆子、青椒、米飯以及土豆做的牛排。看他說話滴水不漏,於是我就作了一個不太恰當的比較。我提到了巴林國(Bahrain),它由人口占少數的遜尼派(Sunni)統治,而對人口占多數的什葉派(Shia,目前公開起來反抗)並不信任,我覺得它可以與盧安達作個比較,因爲盧安達政府也是由少數派的圖西族控制,圖西族只大約佔全國人口的14%,是1994年大屠殺的受害者。與巴林國一樣,盧安達的統治階層也擔心若切實落實民主會導致多數派胡圖族人上臺,鑑於人口占多數的胡圖族以往所犯下的種種極端行徑,此舉肯定會引發國家陷入混亂。
卡加梅對我的這個比方反應劇烈。他說,首先,與巴林國王哈馬德•本•阿勒哈利法(King Hamad bin Isa al-Khalifa)不一樣的是,他自己不是君主。但是,我低聲嘟囔:你去年是在沒有真正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才以93%的得票率當選。
「盧安達有憲法,有任期限制,有議會,有選舉。我只能說作此比較者純屬無知,」他堅持道,並辯解說鑑於盧安達以往不尋常的血腥史,自己去年以近乎全票當選正是表明國家很穩定。
然而,國際社會越發關注:在政治體制依然嚴控的情況下,盧安達所取得的社會和平與經濟發展是否可以持續?
卡加梅仍沿用非洲國家元首常用的策略回應,但這一次似乎有點言不由衷:他喋喋不休地說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期望值過高,連西方國家通常自己都難以企及如此苛刻的標準。「爲何多數發達國家不是基於種族、膚色或者部落來詮釋呢?是啥原因呢?那你能否告訴我: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是來自哪個人口占多數的民族?」他問我。
我倆算是就以下這點假設取得了共識:如果盧安達與利比亞(Libya)一樣是個產油國,1994年大屠殺發生時,聯合國的觀察員就不會袖手旁觀(而事實上他們當時袖手旁觀)。我倆還就象牙海岸問題取得了共識:引發今年武裝衝突的選舉考慮欠成熟,這表明向非洲國家施壓,逼迫其引進不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制度是錯誤的。
「選舉必須舉行。但何時進行?絕不能草率地、在任何情況下都舉行選舉,」他說,話鋒直指去年11月聯合國監督下的象牙海岸大選造成國家分裂的事實,結果導致反政府軍控制國家北部,政府軍控制南部。「似乎把選舉或政治進程看作是工廠定製的東西……這些東西不可能由英國定製出來,也無法由美國定製出來。行不通的,若強意爲之,結果只會問題纏身。」
服務員端走了空盤子,換上了裝有橙子、菠蘿以及黑莓的水果沙拉碗。我們又找到一個共同點:「非洲任何地方的水果都要比英國的甜。「這兒的菠蘿味很淡,」卡加梅說。「香蕉味也怪怪的。」
咖啡端上來後,我問了卡加梅一個困擾已久的問題:他巧妙地爭取到了美國福音教會的基督教社團的支援,我聽說這是把布希政府(Bush administration)爭取到他這邊的因素之一,儘管一開始舉步維艱。那你自己是個信徒嗎?「既是又不是,」他說。「我慫恿有信仰的人相信。」
盧安達大屠殺中,天主教(Catholic church)信徒爲虎作倀,這部分解答了我的疑問。參與屠殺的人中就有天主教的牧師。「我親眼目睹宗教犯錯誤,瞧瞧天主教會在盧安達都幹了些什麼,這些事至今讓我心神不寧,」他說。「你都看到天主教會因爲旗下牧師與主教戀童事件向世人道歉,教宗(Pope)本人也屈尊向美國人道歉,然後他又跑到澳洲去道歉。但天主教會永遠不會爲自己在盧安達大屠殺中的行徑道歉。」
爲了把過去混亂的全部罪責一投腦推到外界身上,他最近修改了自己的大部分措辭,以迎合當今時代需要。比方說,他強烈地意識到只有非洲人自己腳踏實地去做,非洲大陸才能迎頭趕上。他特意把衣索比亞(Ethiopia)、加彭(Gabon)及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的領導人挑選出來作爲志同道合者。「別人會給我們施援,但最終得明白這是我們自己的事,」他說。「非洲不應該等著被人剝削或者利用。不能這樣,我們應該參與到談判進程中,應該提高話語權,在談判中能夠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條款,因爲我們提供了大量資源。」
他繼續說道,部分原因正是由於盧安達資源貧乏,所以若要與鄰國競爭,採用不同的治國方略、根除哪怕微小的貪腐,改善商業環境顯得刻不容緩。在聯合國經商便捷指數排名表(World Bank』s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ankings) 上178個國家中,盧安達成爲銳意改革進步最神速的國家(升至第66名)。「我們是內陸國家,國土面積狹小,位於非洲大陸中部位置。我們有些鄰國資源比我們豐富,往往能吸引更多的投資客,所以我們必須把創造獨特性置於戰略的高度。」
獨特的還包括執政的盧安達愛國陣線,它發軔於卡加梅所領導的反政府運動,從流亡鄰國烏干達(Uganda)發展至最後上臺執政。盧安達愛國陣線是全球獲取捐贈最多的政治運動組織,它的基金控制了盧安達主要經濟部門的命脈,包括電信、銀行、房地產與能源,當RPF還在打游擊戰時,就已經進行了大量海外投資。卡加梅控制的RPF資金達好幾億美元。「我們不想到處乞討。比方說,我們沒有接受過卡扎菲(Gaddafi)的任何選舉獻金……原因就在於我們真正希望在任何時候,做任何事時都能保持獨立自主。」
這就是盧安達自相矛盾的地方。1994年大屠殺後,國家依靠外來捐助得以重建,然而與所有依賴援助的非洲國家一樣,它關注的還是力求做到自力更生。雖然盧安達還欠許多外國盟友的外債,但其領導人從不搖尾乞憐,而是堅持獨立自主。「我們按照非常規的方式處理問題,因爲我們必須得這樣做,」他說——並補充說此舉經常惹惱援助方,對方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所以任何時候都得抗爭。」
威廉•沃里斯是《金融時報》非洲部主編
譯者:常和
保羅•卡加梅的廚師所準備的菜單:
2份胡蘿蔔番茄湯
2份牛排
混合蔬菜
蘇打水
小圓麪包
總計(附小費)83英鎊

當蜜雪兒•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走進曼哈頓Cibo餐廳時,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身上那件鮮豔的粉色夾克衫。這並不是一件特別優雅的服裝:看上去廉價的面料,過時的剪裁——至少依照紐約嚴格的剪裁標準來說是這樣。但是,這種活潑的顏色分外適合她,她使得整個義大利餐廳都熠熠生輝。此外,相對她的工作而言,這種風格似乎也相當合適。
在去年秋天之前,現年59歲的巴切萊特最知名之處就是智利第一位女總統。而這只是她非凡人生中的最新一次轉折:青年時期的巴切萊特是一個左翼行動分子,其家庭曾飽受20世紀70年代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獨裁統治的折磨;她曾流亡國外並學習醫學,最終回到智利躋身政壇。在2006年2月她當選爲總統並執政長達四年,在擔任總統之前她還擔任過部長。
去年秋天,在卸任總統一職6個月後,她被任命爲聯合國婦女署副祕書長級執行主任。聯合國婦女署是一個著名的聯合國組織,試圖將婦女問題落實到全球決策層面。
等她坐下,我問起她是如何適應在聯合國工作的。我得承認,在關於她新職務的理想主義觀點和犬儒主義觀點之間,我有些左右爲難:我一方面很高興聯合國終於開始著手協調女性問題,尤其是在世界貧困、飽受戰爭摧殘地區的問題;但是憑藉我過去在聯合國擔任記者和人類學家的經歷,常常困擾聯合國的官僚主義以及華而不實的說辭仍然讓我疑慮叢生。
巴切萊特傾聽著,並露出平靜、燦爛的笑容。她的一舉一動毫不彰顯她不平凡的人生經歷;整潔的衣服,雖然有點土裏土氣,一頭幹練的短髮;她的臉上塗抹著紫色眼影,但仍有輕微的皺紋。這張臉由於其「正常」而引人注目:在紐約,50歲以上的女強人常常透過外科手術來保持青春;而在拉丁美洲,女政治家們往往看起來倍加迷人——因爲她們經過了周到的「特殊護理」。
「如果我認爲自己不能有所作爲,我就不會接受這份工作,」她說。她還解釋道,新職位的目標是協調聯合國機構內各類不同計劃與措施。她希望這將激勵各國政府改善婦女狀況,這不僅僅針對她們處於受害者的地方(比如在戰爭中),而且針對更廣泛的層面。「我想爲聯合國婦女署找到一個強有力的理由,爲何婦女問題事關重大的理由,爲何改善婦女的生活是一種良好投資的理由……」她的英語相當流利,不過她採用的語法迷人而獨特,並且她常常需要字斟句酌。
我問道,聯合國的官僚主義做派是不是讓她有抓狂的感覺?在我們共進午餐的前幾天,當我主持一項關於世界各地貧困寡婦境況的聯合國活動時,我第一次見到巴切萊特。那次活動中有兩個細節特別引人注意:一是負責監督本次活動的加彭第一夫人的參會,她穿著一件格外華麗的服裝(顯然也很昂貴);第二個就是巴切萊特對活動的影響(她看起來有點邋遢),在不冒犯加彭主持人的情況下,悄悄的略施妙計,使活動變得不那麼枯燥。這件事凸顯出巴切萊特在聯合國將面臨的種種外交挑戰。
她笑了笑說:「這裏有一些每個機構都有的、我們應尊重的程式。但我試著使其更具互動性、更有活力……如果事情能夠合理化,並能以一種好的方式來解釋,情況就可以改變。你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理由。這正是我想爲聯合國婦女署構建的,一個(改變婦女地位的)有力的理由。」
這時侍者出現了。這個餐廳很有味道,但並不奢華,菜單甚至有些卷角。巴切萊特說,她選擇這家餐廳是因爲方便,但是我注意到這家餐廳也很平價。「嗯,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她驚訝的說道。「不過這家餐廳不錯。它很正規,並且食物都很好喫。」經過一番討論,我點了芝麻菜沙拉和軟殼蟹,巴切萊特選擇了兩道開胃菜:又一份芝麻菜沙拉和蒸貽貝。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喝酒。
「你在減肥嗎?」我問。想保持苗條的紐約女性常常只點兩個開胃菜。巴切萊特有著中年發福的跡象——事實上在她擔任總統期間,一些智利媒體曾戲稱她爲「胖子」。「沒有減肥,我應該減並且也嘗試過,但是……」她說她不知道紐約女性用了什麼方法來保持如此苗條的身材:「她們居然喝酒!我親眼見過!我每天早起但我不鍛鍊,因爲我總在準備檔案之類的東西。爲每個會議做準備……我經常散步,但這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就像她並不在意平價餐廳一樣,隨性的點菜方式是巴切萊特不拘小節的另一個標誌。考慮到她的生命中曾面臨的挑戰,也許這不足爲奇。
1951年,巴切萊特出生於聖地牙哥的一個中產家庭,是兩兄妹中的一個(她的哥哥已經去世)。她的父親是一名高級軍官,母親是名考古學家。 「從我還是個孩子起,我的母親就一直告誡我,婚姻不是女人活著的目的……你可以做到的遠不止於此,」她回憶說。「即使是我的父親,雖然他在軍隊裏……(但)他也非常支援進步運動。」
她早年的家庭生活如同田園詩般恬靜,雖然也受到嚴格的軍事紀律和責任觀念的束縛。在學校,她夢想成爲一名科學家來「幫助改善世界」。但後來她決定學醫。「我的家非常溫馨……我能感受到父母的愛,即便我很羞澀,我仍覺得這對我幫助非常大。」
但在1973年,隨著皮諾切特發動政變並奪取政權,這個溫馨的世界便土崩瓦解了。她的父親由於反抗而被逮捕入獄,最後被折磨致死。之後巴切萊特和母親也遭到軍政府拘捕數月。
「你也受折磨了嗎?」我小心地問。我的本意並不是將這視爲一個問題。
她沉默了。她從來沒有公開詳細的談論過這段時期的生活。「很多人經歷過比我更糟糕的時期,」她回答道,並果斷的把話題轉移到她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出獄後,她和她的母親前往澳洲,之後她們定居在原東德,在那裏人們很同情她的左派觀點。在德國她成爲了一名醫生,嫁給了一位智利左翼活動家同胞,繼續支援反抗皮諾切特的活動,並開始生兒育女。
侍者的上菜中斷了我們的談話:兩個芝麻菜沙拉,整齊的排列成金字塔的形狀,很不起眼但是非常美味。她開始心不在焉的喫了起來,並繼續給我講她的傳奇生涯。
1979年,她回到智利希望能推進民主進程。她是一名合格的外科醫生 ——但是當她申請在公共衛生領域工作時,卻由於她的左翼觀點而遭到拒絕。於是她轉而加入了一個非政府團體。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政治大環境有了改善。她終於得以加入公共衛生體系,負責聖地牙哥一個關於艾滋病以及流行病的項目。她表現出衆,並於1996年被智利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推舉參選市議會。 2000年,她被任命爲衛生部長。接著在2002年,她成爲國防部長。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任命。在拉丁美洲,先前從未有過女國防部長;此外,她回到智利後便與丈夫離婚,成爲了一名單身母親。皮諾切特對她家庭的迫害也影響了她的情感。她堅持認爲,正是因爲她過去的經歷才使得她如此熱心於這份工作。「我一直認爲,智利政變的問題之一就在於,政府官員和軍隊之間缺乏政治對話或是相互理解,」她說。「我(小的時候)住在部隊。正如他們所說,我出身於一個軍官家庭。所以,我認爲我懂得溝通的話語,我可以爲二者搭建橋樑。」
當她擔任總統時,她可曾嘗試找出折磨她家人的罪魁禍首?或是尋求復仇? 「不,沒有,」她驚訝的說。 「在我的人生中曾有過一段充滿憤怒的時期,但是……這只是一個過程。這並不是意味著我不在乎此事,而是……」她卡殼了,忘記了想說的英語單詞。「我只是想建立一個人們能夠兼容幷包的國家,人們不會將對面的人視爲敵人,而是可能有所不同的人。」
她停頓了一下,然後講起一次經歷:她在聖地牙哥的一家五金商店裏,碰見了她父親生前的朋友,一個首先開始折磨她家人的人。當她講述這段經歷時,她的聲音沒有任何自憐或是苦痛;她熱愛生活,喜歡向前看——而不是糾纏於過去。她不想以一個受害者的身份生活。
我們面前的餐盤被靜靜的撤走了,接著我問起了她2006至2010年執政的經歷。關於她執政業績的評價譭譽參半:一些左翼政治家對她提出指責,因爲在她的領導下社會民主黨在這麼多年內首次失去執政權。其他人則認爲在全球經濟動盪期間她的領導穩定、有效,並且強調,民意調查顯示她仍舊是該地區最受歡迎的政治家。
對於這段時間,巴切萊特本人顯得有些矛盾。「做一個總統非常孤獨,因爲即便你有很多顧問,但最終的決策者只能是你自己,」她說。但是她表示她爲自己能夠推進社會最貧困人羣的「社會保障」工作而驕傲。她也爲自己對婦女事業做出的貢獻而欣喜不已——一家報紙上說,在她卸職之後,智利的年輕女孩表示,她們長大後想當總統,而不是護士。而她所厭煩的是這也使她成了智利的名人。「昨天有人問我,(當我在紐約生活時)你想念智利的什麼。我答道,『我想念我的家人,但是我也喜歡在這裏做一個無名之輩——爲自己保留一些私隱。』」
對於她成爲聯合國職務的候選人也曾有過爭議。一些聯合國的成員傾向來自非洲的候選人,其它一些成員則不喜歡巴切萊特處理「婦女問題」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她一直強調,女權主義不應該只是試圖保護婦女——應該在更積極的意義上,「授予她們權力」。正如在她自己的人生中一樣,她不喜歡糾結於被迫害的經歷。「賦予婦女權力,意味著讓更多的女性置身決策者地位……擔任政府官員或是國會議員,」她說。最終,她贏得了這一職位並搬至紐約。
她喜歡紐約嗎?當侍者端上主菜時,我問道。對於她那份分量很足、熱氣騰騰的蒸貽貝她現出驚喜的神色。而我的那份軟殼蟹略微炸的有些過頭了。她平時有什麼愛好呢?
「愛好?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工作、讀書、旅遊、準備會議。我應該喜歡……,那個詞你們怎麼說……?」她喃喃自語的說了一個西班牙語片語,我猜測大概是「品味」。
「是的!細細品味紐約。散步,與朋友會面,逛博物館、劇院等。我很想回去看望我的孫子。」她的兩個女兒還在拉丁美洲讀大學;而她的長子在智利工作,並已有兩個孩子,她十分想念他們。
「對了,我還喜歡跳舞,跳舞!」她突然補充道。
跳舞?我驚訝的問。
「我說的不是探戈舞。那太專業了。但我很喜歡梅倫格舞和莎莎舞... 」她變得活躍起來並解釋說,就在她離開聖地牙哥之前,「朋友們爲我舉辦了歡送會及生日派對。我跳舞了!」
我問她在紐約是否還做其他的事情。「我也得做一些日常瑣事——打掃屋子,洗衣服。我週末做這些。」
「你沒有請清潔工嗎?」我喫驚的問。她堅定的搖了搖頭。「我不是大明星之類的人。我想這歸結爲我從小受到的家教,同時也因爲那場政變。當你失去朋友,失去親人,你會捫心自問什麼纔是你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東西,然後你會明白人類的侷限性。這會使你更謙卑、更理性也更具野心——不是說試圖達到極限,或是得到權力——而是試著爲其他人改變世界。」她苦澀的笑了笑,說她的女兒 (她們非常親密)曾嘲笑她對公共服務事業「上癮」,諸如管理一個國家、建立一個慈善基金會或試圖幫助婦女等。
主菜已經撤掉了。她點了綠茶,我點了黑咖啡。結過賬後,她靜靜的收起手包,朝餐廳後面昏暗的側門走去。「這是一條回聯合國辦公室的近道,要快一些,」她一邊說,一邊穿著粉色的夾克衫消失在我眼前——大概是去參加另一場會議了。在聯合國,這樣的導航能力遲早會派上用場的,我在心中默唸。希望她能克服在聯合國的各種阻礙,一如她克服人生中諸般困難一樣有力。
吉蓮•邰蒂是英國《金融時報》美國執行主編。
譯者/功文

託比•楊格(Toby Young)對拋頭露面壓根不緊張,我與他首次結識是在去年的英國保守黨伯明翰(Birmingham)大會上。在酒吧裏,這位記者與作家來到我跟前,假意用手指戳了我幾下肚子,爾後又抬起頭來詰問我:「您爲何至今還不報導本人興辦的學校?」
今年47歲的楊格是位於漢莫史密斯(Hammersmith)的西倫敦「免費」學校(West London Free School )董事會主席,這是一所新式中學,今年正式迎來首批120名、年齡爲11歲的孩子就讀。這個倍受矚目的項目讓楊格成了參加英國教育辯論會的常客。
這所學校是首波「免費學校」,由國家出資、但由教會或社團(楊格的學校由當地的家長)這樣的私立團體成立,旨在給現有的教育體系注入新的教育模式。
讓西倫敦免費學校與衆不同的原因就是這位校董事會主席的知名度。楊格引人注目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他是《現代評論》(Modern Review)自命不凡的合夥創辦人兼主編,之後他移居美國紐約,擔任《名利場》雜誌(Vanity Fair)的特約編輯,但在那兒工作並不順利,還與主編格雷登•卡特(Graydon Carter)鬧翻,後來楊格把這段經驗寫成了一本名爲《如何衆叛親離》(How to Lose Friends and Alienate People)的暢銷書,並把它改編成了話劇與電影。
楊格現在仍是記者,但他的新角色是爲興辦新式免費學校奔走疾呼,讓他這位原本工作四平八穩的文化評論員一下子躍至前臺,在英國教育問題上不斷與人發生衝突。
我讓他在倫敦選用餐地,曾當過食評與電視節目《超級大廚》(Top Chef)嘉賓的楊格在諸多頂級餐館中左挑右選,最終選定耀西壽司(Yoshi Sushi)這家位於其新建學校旁的普通餐館。他是這兒的常客,我前腳剛到,他後腳就趕到了,就坐他的「定點」包間——四周用木板與紙隔成。楊格外穿黑羊毛衫,裏穿藍色襯衣,手裏拿著自行車頭盔,把布朗登(Brompton)自行車摺疊後擱至桌下。我提議由他來點菜,他則憑記憶嘰裏呱啦點了一大堆,快得連服務員都來不及記。
除了壽司卷與生魚片,他還點了一碗鹽毛豆、軟殼蟹、天婦羅蝦(Prawn tempura)。不一會兒菜就上來了,我倆邊喫邊聊,喝著罐裝可樂,聊到了英國教育部最近的一連串動作。
楊格沒有政客或者理論家的那種派頭,他說起話異常嚴肅,但仍然臉帶苦笑,自嘲不斷。無論是在媒體報導中還是面對面坐著,他給人總的感覺是對啥事都無所謂。我問他是否曾努力讓人看重自己。「我在紐約打拼並不成功,於是我就想,自貶該是苦中找樂的好辦法,但沒想到從此之後我就一直難以擺脫『事業無成』的形象。」
去年我首次採談他時,來自達勒姆(Durham)的一位保守黨激進黨員走到他跟前,問他興辦學校的用意是否想辦砸,好有充足的寫作素材,我問他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對此指控,他當時就怒氣沖天地回敬了對方。如今,這事差不多過去一年時間了。我倆用餐時,他對此事仍顯得一頭霧水。
「有些人指責我動機不良。本人的目的當然不是想要把學校辦砸,以便獲取好的寫作素材。我覺得這是本人有生之年最上心的事,我喜歡自己興辦新式免費學校積極分子的這個角色,」他對我說。
我們三下五去二就把蟹喫光了。待到喫生魚片時,盤子裏只剩了一片蝦。菜的味道棒極了,旅居倫敦的日本人都愛到這家餐館來喫午飯。
楊格說,西倫敦免費學校並非形象工程,但覺得自我宣傳是成功的重要環節。「從辦學伊始我就認定大張其鼓宣揚,成功的把握性會更大。」
他的算計看似沒錯:學校很快就初具雛形,立法機構允許招生的批覆去年七月就下來了。「原因是興辦免費學校的提案中,屬我們最爲高調,政府也樂見其成。所以,這一切對我們幫助很大。」
高知名度還帶來了其它好處。「招生輕而易舉。比方說,說服家長讓孩子就讀本校,學校的知名度就起了不小的作用。今年招生指標120名,光申請者就大約有500名。」
報名者如雲可能意味著楊格自己的四個孩子(他與妻子卡洛琳(Caroline)育有四個孩子——薩莎(Sasha)、羅朵(Ludo)、弗雷迪以及查理,均不滿9歲)到上初中年齡時,可能無法入讀本校。「我最大的孩子屆時肯定會申請入讀;但她不一定就能錄取,每四個申請者纔能有一人入讀。」
楊格成了免費學校反對者的攻擊目標。教師聯合會的反對理由是:免費學校的老師無需正式教師資格證。地方政府官員、管理大多數其它學校的市府機構不希望因新式免費學校而出現辦學競爭,使情況變得複雜化。
楊格也不受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待見。他一邊在小碗裏和著芥末與醬油享用生魚片,一邊說,「憑直覺,我要是個工薪階層的黑人女性,那些掌權者可能就會支援我辦學。」
但他說,自己的張揚減輕了更多不願拋頭露面、不願吱聲者的壓力。況且即便自己再低調,西倫敦免費學校還仍會是攻擊的目標。可以這麼說,要不是自己的張揚,教育部門答應花在新校舍的1500萬英鎊可能就會花到維修或擴建原有校舍了。
學校公然設置古典課程同樣引起了爭議。「我認爲所有孩子能夠從學拉丁文、瞭解英國歷史以及閱讀莎士比亞著作中獲益,以這些東西屬於中產階級家庭孩子的學習內容爲由剝奪全體孩子這樣的機會純屬另一種勢利眼,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明顯不公。
「如果窮孩子只得去媒體研究班學習電視節目製作,而讓富人家的孩子入讀一流學校、培養思考與寫作的能力,那我們永遠也無法破除英國社會的等級制度,這樣做有違社會正義,是社會種族隔離。」
他說過時的那些課程「對工薪階層家長及移民很有吸引力……這一點一目瞭然。」但初期的跡象表明,相比那些附近公立學校的學生,新式免費學校的學生基本來自較爲富裕的家庭。初步估計顯示大約17%的新生符合享用免費午餐的條件——比例高低是衡量家境的指標,而本地其它公立中學享用免費午餐學生的比例是31%。
楊格同樣遭到左派勢力的攻擊,原因就是他所謂的「變節工黨分子」身份。他父親、已故楊格勳爵(Lord Young)是工黨頂禮膜拜的人物,是思想家及熱心社會的企業家,他的思想推動了戰後英國社會的構建——楊格對父親感到非常自豪。
邁克爾•楊格(Michael Young)是1945年《工黨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創造了「英才教育」這個新詞,提倡保護消費者權益;他是開放式大學的始建者,於1971年成立了遠距大學,楊格勳爵於2002年去世,其成就深深地影響了兒子的一生。
我暗示楊格,興辦新式學校或許是他試圖東山再起(他老父親肯定也會贊同他這樣做)。對此楊格並不認可,雖說他覺得父親可能會支援他,理解他的酸甜苦辣:「當年我父親想方設法成立開放式大學時,的確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那時,真是一場硬仗。」
當我暗示他可能辜負了其父之期望時,他略顯不悅(或許只是對我稚嫩的精神分析不高興),楊格說興辦新式學校前,自己一直努力在「做正經事」,包括創辦《現代評論》以及短暫從事哲學與政治學教職工作。「本人一向嚴肅認真。離開哈佛(當時我是講師)後,我去讀了博(未完成),還在劍橋大學教了兩年書。」
他還竭力爲自己隨後的一些不正經行徑辯護:「舉辦學校的動因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想還格雷登•卡特以顏色。我實在受夠了遭人指手劃腳,不願意接受位高權重者安排好的命運。」他說自己的這種性格屬於「典型的英國式倔強,不願任人擺佈」。但隨即又轉回溫和的自嘲,並借用莎士比亞筆下亨利五世(Henry V,繼位後成了大英雄)的一生來說事:「我喜歡把自己比作哈爾王子(Prince Hal),他之前一直與福斯塔夫(Falstaff)混在一起,過著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生活。但時勢造英雄……他繼位後,憑自己的能力建立了豐功偉績。」
楊格說前前後後投身於興辦免費學校的經歷,讓自己很支援保守黨領導的本屆聯合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表明立場,鑑於本屆聯合政府支援該項政策(興辦新興免費學校)…..我感覺自己有責任支援它,爲它的政策辯解,做縮頭烏龜有點不像男人。」
午餐最後端上來的是檸檬片。我結完了帳,走到大街上,想去看他興辦的新學校,但隨後我倆又溜到隔壁的咖啡屋去喝咖啡,到這兒楊格纔給我說實話:自己的學校纔剛剛有點眉目。
「我的長遠目標是照西倫敦免費學校的模式至少建25所學校。」目前他正在找尋興建六年級(the sixth form,英國中學裏最高年級)的校址,打算建所小學,計劃每年就近招60名學生,他如今正在籌建一家商業公司,給現有的以及成立不久的新式免費學校提供「政治、法律以及公關方面的諮詢服務」。
看來,楊格先生興辦學校的癖好真是頗有淵藪、代代相傳。
克里斯•庫克是FT教育記者
譯者:常和
倫敦國王街 210號
2份可樂:3英鎊
鹽毛豆:3.50英鎊
軟殼蟹:13.00英鎊
天婦羅蝦:13.00英鎊
加州壽司卷:4.00英鎊
鹽漬飛魚卵卷(Flying fish roe rolls):4.00英鎊
生魚片(鰻、金槍魚、大麻哈魚):15.00英鎊
總計(包括小費):63.00英鎊

走在我身邊的是胡利安•卡斯特羅(Julián Castro),美國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長。我們剛從他的辦公室出來,步行前往幾個街區以外、位於該市西班牙使館舊址的Acenar餐廳。那家餐廳是德克薩斯墨西哥風味餐廳中最受歡迎的。一路上,不斷有騎摩托車或步行經過的市民友好地跟卡斯特羅打招呼。卡斯特羅很好認:36歲,英俊,身材高大,像個明星,舉手投足泰然自若,筆挺的西裝、一塵不染的深色皮鞋更增添了他的魅力。此外,他的臉上似乎時刻都掛著微笑。
他確實沒有理由不開心。2009年5月,卡斯特羅當選聖安東尼奧市長。他告訴我,如今,市長的角色更像市政廳董事會的主席,而非首席執行長。不過,美國大城市的市長們享有很高的聲望。在過去10年間,聖安東尼奧市逐漸發展爲美國第七大城市。該市總人口130萬,約三分之二爲拉美裔,因此,卡斯特羅的市長位置是個絕佳的跳板,有望助他成爲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的明日之星(拉美裔選民大部分支援民主黨——譯者注)。
看到我們經過,在人行道上閒晃的一名滿臉胡茬、破衣爛衫的男子衝卡斯特羅喊:「嘿!」看到市長的左手,這名男子彷彿破解了一個祕密,說:「啊,你有婚戒。」說完他看了我們一眼,目光意味深長,然後表示一定要與「胡利安」市長約個時間談談。(卡斯特羅按照西班牙語發音把自己的名字唸作胡利安,而非朱利安。)市長笑了笑,邊往前走,邊衝那名男子揮了揮手,告訴他與市長辦公室聯繫、預約個時間。
市長的婚戒(他的妻子叫埃麗卡,兩人有一個2歲的女兒)出賣了他,這個婚戒是區分他和雙胞胎兄弟華金(Joaquín)的標誌。華金未婚,也從政,在德克薩斯州議會任職,正準備競選明年的國會議員。
在卡斯特羅兩兄弟身上,體現了拉美裔在美國政治地位的上升。儘管美國自建國以來一直極力防止政客拿種族問題做文章,但面對選民嚴重分化的形勢,美國兩大政黨爲了奪取優勢地位,只有瞄準最後一塊戰場——龐大的拉丁裔族羣。
到目前爲止,拉丁裔是美國人口成長最快的族羣。本世紀頭10年,美國人口總共成長273萬人,其中,拉丁裔佔一半以上;而在德克薩斯州,拉丁裔佔全州10年人口總成長的近90%。拉丁裔將很快成爲加州和德克薩斯州最大的族羣,而這兩個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兩個州。
40%至60%的拉丁裔選民支援民主黨。正是因爲這一點,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在2012年大選中可能連任,卡斯特羅(或像他這樣的拉丁裔從政者)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入主白宮。
1974年9月,胡利安和華金兩兄弟出生於聖安東尼奧市。他們的母親羅茜•卡斯特羅(Rosie Castro)當年是位著名的奇卡納(Chicana,墨西哥裔美國人)活動者,是一個名爲「種族聯盟黨」(La Raza Unida)的團體的負責人之一,鼓吹拉丁裔族羣權利和身份認同。她基本上是作爲單身媽媽、一個人把兩個孩子帶大的。
卡斯特羅兄弟的故事或許會讓人聯想到歐巴馬——代表自己的族類,歐巴馬實現了黑人的政治夢。跟歐巴馬一樣,卡斯特羅兄弟也有常春藤名校的文憑,兩人一起從史丹佛(Stanford)畢業(胡利安主修傳媒與政治學),然後又一起上了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因爲非常想回到聖安東尼奧市從政,胡利安畢業前就開始競選市議員了,這樣他一畢業就能進入市政廳任職。2001年,胡利安順利當選。而華西則在2002年進入德克薩斯州議會。
更貼切的聯想可能是英國的戴維•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和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兩兄弟,不過,與米利班德兄弟不同的是,到目前爲止,兄弟相爭的戲劇化場面還沒有在卡斯特羅兩兄弟身上出現。2010年,米利班德兄弟倆爭奪工黨領袖的位置。米利班德兄弟的父親是位馬克思主義學者,而兩兄弟卻進入了英國政治的中心,這種經歷與成長於草根政治環境的卡斯特羅兄弟一樣。
到達餐廳的時候,我問胡利安:有沒有在即將到來的國會選舉民主黨初選中支援自己的兄弟?他抬了抬眉毛,說:「當然有了。」胡利安說,華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卡斯特羅的到來沒有在餐廳員工中引發騷動。他是這裏的常客,大家顯然已經習慣在這裏看到他了。侍者淡定地把我們領到了餐廳中間的一張桌子旁,沒有大張旗鼓地歡迎。
Acenar的宣傳海報上號稱有「火熱的墨西哥菜餚、冰酷的飲品」(HotMex, CoolBar)。餐廳建在聖安東尼奧市的「河濱小道」(River Walk)上,很久以前,那裏有一條洩洪河,而如今,河邊建起了一家家餐館和娛樂場所,改建後的河道變得魅力十足。市長告訴我:「(河濱小道)是德克薩斯州第二大熱門旅遊景點。」說這話的時候,他語氣平靜,與普通市民無異。第一大熱門旅遊景點是1836年阿拉莫之圍遺址(Alamo siege of 1836),沿河邊再走5分鐘就到了。對於大多數遊客來說,阿拉莫之圍象徵着自由,在那裏,英勇的戰士們與強大的墨西哥部隊激戰13天,這一戰役是德克薩斯革命(也稱德克薩斯獨立戰爭——譯者注)中的關鍵一戰。然而,對於墨西哥人、以及一些墨西哥裔美國人來說,阿拉莫之圍象徵着恥辱和失敗。
這家餐廳的裝修閃亮、新式,菜品的風格也與此類似,廚師將粗糲的墨西哥菜餚重新包裝,做出了一點現代的味道。我們都不想點那些花哨的,於是點了巧克力辣醬肉卷(enchiladas de mole)、雞肉餡玉米粉圓餅、配青豆和米飯。卡斯特羅點了冰茶,我要了百事可樂,餐廳還上了冰水——這是所有美國餐廳的「標配」。
桌上的冰水讓卡斯特羅想起了自己唯一一次去倫敦度假的經歷。那是在2007年12月。卡斯特羅說,在倫敦,讓他感到彆扭的是一些「細節」。「靠左邊開車當然挺彆扭的,不過更彆扭的是沒有冰塊,大家都不往飲料裏放冰塊。」我說,這可能是因爲氣候不同,聖安東尼奧常年陽光充足,而倫敦多數時候是陰天,這或許造就了倫敦人這種「奇特」的習俗。
坊間常常議論卡斯特羅可能問鼎白宮,在他的家鄉德克薩斯州,有的人已經聽厭了這種話。在線雜誌《德克薩斯論壇》(Texas Tribune)在2010年曾指出,卡斯特羅「參加大選的可能性已經被討論得太多了,變成了一個令人打哈欠的話題」。
卡斯特羅並非聖安東尼奧市第一位可能有所成就的拉丁裔從政者。曾任該市市長的亨利•西斯內羅斯(Henry Cisneros)曾進入柯林頓政府內閣,然而在上世紀90年代末,他的政治生涯因性醜聞而終結。儘管如此,我還是在想,揹負全市人民的期待對於卡斯特羅而言是否沉重的負擔?
「年輕的好處之一是,不會想那麼多。」卡斯特羅說,「我感到非常榮幸,(如果我說)從不想這件事,那是撒謊。但政治上的一些困難會讓人清醒過來。」
首先,德克薩斯是個「深紅(紅指支援共和黨)州」。在該州選舉產生的29個職位中,自1994年以來沒有一個民主黨人當選。卡斯特羅表示,他的目標是連任4個市長任期(每個任期爲兩年),也就是到2017年。
屆時,卡斯特羅將準備好競選美國最令人垂涎的職位——德克薩斯州長。這個職位的現任者裏克•佩裏(Rick Perry)是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前任則是小布什(George W Bush)。即便不考慮這個職位是往上爬、通往華盛頓的重要一步,民主黨現在也不可能贏得這個職位。不過,卡斯特羅是否認爲,到2017年,拉丁裔選民數量的增加將意味著德克薩斯州將變「藍」(即變得支援民主黨)呢?「我認爲,或許到那時德克薩斯會變紫,」卡斯特羅笑著說,「沒有變藍,但紅藍雙方都有可能在這裏取勝。」
依賴拉丁裔選民的問題之一是,他們的參選率很低。2010年,拉丁裔佔美國人口的16%(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數據),但只佔有投票資格選民的10%,因爲拉丁裔族羣相對年輕,且很多屬非法居留。拉丁裔只佔實際投票選民的7%。儘管拉丁裔族羣如今已在美國立足,且大部分已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但該族羣仍然比較貧困,受教育程度也比較低。
德克薩斯州的拉丁裔中,有約40%高中沒畢業。卡斯特羅說,這意味著,到2040年,「有高中文憑和學士學位的人數比例必然比現在少,因爲教育程度低下的人羣在成長」。
卡斯特羅費力地向我解釋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拉丁裔家長非常愛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也非常希望孩子有出息,但他們卻不大搞得清楚該如何透過教育體系培養孩子。」卡斯特羅說,「有時候,他們感覺老師最懂,因此放棄了自己作爲家長應該參與的部分。」
我們的菜上來了。侍者提醒我們盤子很燙(hot)。我不知怎麼的沒有在意,拿起盤子時差點燙傷了。卡斯特羅故作一本正經地說:「他們說很燙的時候,指的是溫度。」
卡斯特羅認爲,拉丁裔低投票率的局面將會改變,即便僅因爲該族羣投票的重要性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他宣稱,保守黨故意設置了一些障礙、阻止拉丁裔選民投票,比如規定投票要出示身份證。保守黨也對非洲裔選民設置了類似的障礙。
不過,拉丁裔族羣的社會觀點保守,宗教信仰虔誠。上世紀90年代,小布什擔任州長期間,曾試圖博取該族羣的好感,這件事非常著名。「如今看來,那好像是800年前的事情了。」卡斯特羅說,「整個保守黨的立場向右移了很多。」他想起今年在紐約參加的一場有關移民的辯論會。在會上,他的對手談論拉丁裔移民的語氣,「彷彿他們比之前的幾波移民地位更低」。「我們不要你們的苦力、你們的窮人和過剩的人口」——辯論中的這個論點,凸顯出美國人的一種情緒:拉丁裔移民對於美國沒有益處。
「他們沒有說得這麼直白,但基本上,他們的意思是,我們是下等人。」卡斯特羅說,「人們通常不會在公開場合表達這個觀點,但這是主流共和黨的論調,拉丁裔族羣已經非常熟悉了。當然,這會影響拉丁裔對保守黨的看法。」他自信地補充道:「這也確實影響了他們對保守黨的看法,我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
卡斯特羅承認,他有意讓自己的語氣不帶有憤怒的情緒。歐巴馬也一直遵守類似的原則。一個憤怒的黑人或拉丁裔候選人在全體選民中選情不佳,這似乎是美國政治中的規律。
卡斯特羅的母親年輕時有所不同。卡斯特羅表示:「她年輕時非常活躍,緊跟時代步伐,爲拉丁裔羣體的利益大聲疾呼。但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一代人看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美國在過去40年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卡斯特羅的母親今年64歲,目前在一所地方社區大學工作。他表示,她認識到美國有能力取得進步。「她對美國取得的進步表現很平靜,並樂於看到這些進步。她不再像23歲那樣激情洋溢了」。
但我問道,她是否真的與許多墨西哥裔美國人一樣,仍然不喜歡阿拉莫事件?
卡斯特羅微笑著說:「我肯定她仍然不喜歡阿拉莫事件。她的成長經歷與我們兄弟倆完全不同。這顯然影響了她對阿拉莫等事件的世界觀。我們在一個壓力不那麼大的時代長大。」
那麼你們在成長時沒有感到憤怒和被剝奪了公民權?「是的,我們沒有」。
當卡斯特羅談到時隔已久的美國政府預算紛爭和共和黨削減醫療支出和養老金的要求的時候,他聽起來很沉著,而不是憤怒。
卡斯特羅表示,預算紛爭日益加劇。「我認爲美國人沒有到不願爲聯邦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和社會保障買單的地步,不過這個觀點有些強人所難」。
隨著午餐接近結束,卡斯特羅再次談起了自己目前的工作,吹噓聖安東尼奧是個取得成功的拉丁裔城市,在安然度過經濟低迷後的狀況遠好於其它城市。與德克薩斯州的其它城市相比,聖安東尼奧沒有遭遇房地產市場崩盤,並且還受益於高油價。「它並非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如果一個城市擁有龐大的拉丁裔人口,那麼它將非常貧窮。事實並非如此」。
說著這些話,他搶過賬單,堅持要爲此次午餐買單。鑑於英國《金融時報》有著客人不應買單的嚴格規定,我強烈反對他這樣做。結果沒有什麼用,最終他買了單,這是他一天來做的唯一不禮貌的事情。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華盛頓分社社長
譯者/何黎

安瓦爾•易卜拉欣遲到了,他肯定困在孟買無可救藥的交通裏,動彈不得。但在我坐定等他時想到,他今天能來,就已經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了。僅僅幾天前,這位馬來西亞反對派領袖似乎還有可能第二次身陷囹圄。過去11個月中,安瓦爾因爲被指控雞姦一名男性助手,一直在吉隆坡受審。這起案件在他的祖國造成了分裂,也破壞了他在海外的形象。然而1月9日,馬來西亞高級法院(Malaysian High Court)判決安瓦爾獲勝。在無罪釋放的當晚,64歲的安瓦爾飛往印度,準備在一場關於亞洲民主的會議上發言,會議的組織者拉傑莫漢•甘地(Rajmohan Gandhi)是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孫子。
我在莫臥兒風格的白沙瓦里(Peshawri)餐廳裏比較昏暗的位置等待安瓦爾。這家餐廳緊鄰孟買機場,位於一家華麗的酒店的背後。餐館外的廣告牌上寫道,在這家「世界最好的印度菜餐館」,食客們能「盡情享用美味」,餐廳內部低低的天花板,粗糙的木製傢俱和牆上的掛毯,意在讓食客想起莫臥兒帝國時代印度的西北邊陲,只有入口處高聳的白色前廳、旁邊點綴的棕櫚樹和伊斯蘭風格的窗戶才稍稍沖淡了這種感覺。
安瓦爾的政治許諾即使在自己的崇拜者當中都可能引起分歧。一些人堅信他還是最初時的面目:一個自由派改革者;一位有才能的技術官僚,他曾讓馬來西亞躲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最嚴峻挑戰;他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曾在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任教;他或許還有能力將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精神引入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是亞洲最大的以穆斯林爲主體的國家之一。
然而,儘管安瓦爾有醒目的履歷,但人們對他能否兌現承諾仍然心存懷疑。批評人士指出,他早年曾是一名伊斯蘭派學生激進分子,並且在20世紀90年代,安瓦爾還曾長期處在馬來西亞統治精英階層的核心。這個時期他在政壇崛起,晉升爲專制領袖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的副總理。最終他與執政當局決裂,1998年因爲其它莫須有的腐敗和雞姦指控鋃鐺入獄。另一些人則指出,他所領導的馬來西亞反對派存在內部分裂,還有人抱怨他在西方說的比唱的都好聽,可是在國內卻與伊斯蘭派眉目傳情。
安瓦爾遲到了半個小時,按孟買的標準應該算可以接受,不過他還是禮貌地道歉。他面目斯文,穿著入時的白色開領襯衫和黑色燈芯絨西裝,頭髮梳得一絲不苟,鬍鬚也修剪得整整齊齊。在他來之前,我檢視了一下他的 Twitter 頁面(有12萬名關注者),最新的一條推文中發佈了一張照片,照片上顯示的是法院判決後,他被攝影機和照相機團團圍住,還附上一句話,評論這張照片「像好萊塢」。我向他詢問當時的情況,和過去48小時裏發生的事件。
對於能夠勝訴,他似乎真心感到驚訝。「和家人早早地喫了早餐,孩子們,女婿、兒媳都來了,」他告訴我。「我說『我們祈禱能有最好的結果,我們可以說還有希望』,不過,現實地考慮……」說到這裏他的聲音降低了下來,然後平靜地補充了一句:「我準備好了要隨身帶的藥和洗漱用品。」
我們的對話稍停片刻時,侍者送來了用樹葉形狀的大木板做成的菜單。食物是用粘土竈烹調的,這種烹調方法的靈感來源於白沙瓦市周邊的地區,白沙瓦現在屬於巴基斯坦。實際上這種烹調方法就意味著,菜品的種類很多都是烤肉。安瓦爾點了用酸奶和大蒜醃漬的白沙瓦烤羔羊肉。我點了唐杜裏土豆(Tandoori aloo),點綴了葡萄乾和腰果的烤土豆。
在侍者的建議下,我們還點了一份小扁豆湯(dal bukhara),菜單上形容它是用小扁豆、番茄、姜和大蒜「和諧調製」而成,用小火慢燉了整整一夜。安瓦爾還點了一份芒果拉西 (mango lassi) 和一些蒲迪納烤餅 (pudina paratha)。
他認可地說道「蒲迪納葉子對健康有好處」,儘管我隨後失望地發現原來所謂的「蒲迪納」與薄荷別無二致。點完菜後,一個禮節問題讓我思忖了片刻,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我多半天——午飯期間,應該在哪個時間點提出雞姦案的問題?單刀直入似乎不夠優雅,不過先把問題解決,最後喫布丁時聊些輕鬆的話題或許更好。
謝天謝地,安瓦爾讓我不用再猶豫不決,開門見山地談到了那個話題。他是夾雜在案件審理的大量細節裏講述的。他飛快地談到案件的漏洞和政府的串通,他說,檢方指控他曾實施性侵的那名男助手,接受法醫鑑定後出具的報告顯示沒有「臨牀證據表明有過插入」。儘管這個話題十分嚴峻,但他還是表現得十分從容,這讓我很驚訝。他用同謀般親密的語氣講話,闡述觀點時身體前傾,講完後又仰靠回去。他會時常講兩句諷刺的笑話,然後兀自笑出聲來。
最近的審判中,也上演了這樣的戲劇性場景,他告訴我,他曾嘗試引用《哈姆雷特》(Hamlet)的臺詞贏得法官的認同(「let us once again assail your ears, that are so fortified against our story」),還提到了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1963年至1964年審判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多名領導人的瑞弗尼亞審判(Rivonia Trial)。原來莎翁正是安瓦爾的一個專長,2006年他還曾在世界莎士比亞大會(World Shakespeare Congress)宣讀過一份論文。而在獄中與他相伴的則是一部《莎士比亞全集》。
他認爲自己獲釋得益於美國和土耳其盟友公開施加的壓力,而英國的角色卻並未得到同樣積極的承認。他不滿地說:「戴維•卡梅倫完全一言不發。」他也提到了其他朋友,包括阿爾•戈爾(Al Gore)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安瓦爾說他和後者首次會面是在20世紀80年代,至今都和他有聯繫。他在談到這些人時表現得如此親密,真的不像是在用大人物的名字裝點門面;這個花招很不錯。
菜上來了,食物稀疏地擺放在土黃色的盤子上。安瓦爾盤中有四大塊羔羊肉,我的盤中看起來則像是一堆脆生生的香腸,沾上了一層發綠的細碎粉末。起先我稍稍感覺有點失望,但剛拿起一根,它就開始在我指尖愉悅地碎裂,在一勺濃稠的棕色小扁豆醬中蘸一蘸,口感豐富、厚重,令人喜悅。
安瓦爾似乎尤其喜歡他的蒲迪納烤餅,他再一次提到了對健康可能有的好處。我問他,在審判期間是如何維持身體狀況的,我知道在已經服刑六年,到2004年案件才終於撤銷從監獄釋放後,他曾因遭到反覆毆打而飛往德國接受手術。他嘆了口氣後,說:「一直很艱難,十分艱難。」他承認自己的後背可能需要再接受治療。
儘管如此艱難,他還是令人驚訝地沒有表現出怨恨。馬來西亞檢方或許會對安瓦爾無罪開釋提出上訴,但眼下他似乎仍在對恢復自由人的狀態感到愉悅。關於前老闆馬哈蒂爾,他說的最尖銳的話是,馬哈蒂爾代表著「亞洲領導人和亞洲價值觀過去的面貌……對公民居高臨下地和藹,而民主和自由則被認爲本質上是西方的觀念。」馬哈蒂爾曾領導馬來西亞二十多年,一直到2003年才卸任。
他用纖細的手指把烤餅捲起,包裹住羊肉和小豆時,他告訴我,已經沒有什麼理由認爲伊斯蘭教和民主之間存在矛盾了。他說:「絕大多數的穆斯林要麼處在民主統治下,要麼正在選擇民主道路,比如埃及。」老派的領導人,無論是馬哈蒂爾還是被推翻的阿拉伯獨裁者,抑或安瓦爾暗指的馬來西亞現任民選總理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都脫離了他所說的新一波穆斯林民主化浪潮。
他會成爲哪種領袖呢?安瓦爾提出土耳其是一個範本。這個提法值得玩味,畢竟土耳其總理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也被指責有專制的傾向,並在建立可能損害該國世俗政體的宗教聯盟。安瓦爾說,他們兩人對伊斯蘭民主有相似的期望,還曾經探討過最近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帶來的更廣闊的機遇。「我提過馬來西亞之春,不過我們的途徑是選舉。」安瓦爾揮動著手勢說。「很快就能發生!」
然而即使你對安瓦爾口中講出的自由主義觀點不加懷疑地接受,他也仍然需要直面國內問題的掣肘,尤其是他領導的反對派運動十分尷尬,而且在意識形態方面尚不成熟。反對派運動由三個分別代表自由派、華人和伊斯蘭教正統立場的政黨結合而成。
他告訴我,如果他能透過可能在今年舉行的大選當權,他的目標會是改善經濟。爲這個目標,他也挑選了一個西方知識界給出的模式,哈佛大學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平等主義觀點。我難以想像羅爾斯成了他領導的政治聯盟裏,得到廣泛認同的參照點,不過同樣難以想像的是,這個有思想的人同時也是一個隱祕的伊斯蘭主義者。
與更加正統的伊斯蘭派盟友打交道容易嗎?安瓦爾苦悶地微笑說:「他們時不時地會反對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來馬來西亞,譴責碧昂絲(Beyoncé)穿著太性感。」不過他表示,除此之外,三個反對派政黨都認同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的需求。幫助塑造共識的是他本人的信仰,他說:「如果是某個非穆斯林的話,他們就會覺得我太糊塗,太軟弱。可是我是穆斯林,所以如果有人問我『你信仰《古蘭經》嗎?』我就可以說『我信』。」
我又緊追一步,問他會不會允許在馬來西亞引入伊斯蘭刑法(hudud)。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中這種備受爭議的形式,涉及對某些罪行處以肉體刑罰。他表情痛苦,緩緩地嘆了一口氣後,承認這是「我需要處理的比較棘手的問題之一。」緊接著他長篇大論地艱難解釋,但始終沒有排除引入的可能性,不過他說伊斯蘭刑法不能與其它權利相牴觸,而且需要得到廣泛的公衆支援。「我們必須達成共識,這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可能出現的。但是如果面臨所有馬來西亞人都同意的情況,我個人怎麼有能力反對呢?」他的解釋符合邏輯,可是並不能令人滿意。
安瓦爾此時已經喫完,把手指浸到了溫水裏。我問他對午餐的感覺如何,他回答說:「菜量很大,但十分可口。」然後還專門讚揚了拉西。我們的時間快用完了,所以開始喫布丁,還點了咖啡。安瓦爾點的咖啡裏要了蜂蜜。
我提了一個自始至終都在我頭腦裏縈繞的問題,引用羅爾斯和莎士比亞的名言,會不會僅僅是爲了吸引外國崇拜者而拿出的作秀道具罷了?安瓦爾第一次顯得惱怒。他說:「我在吉隆坡會引用莎士比亞,在穆斯林村子裏會引用《古蘭經》,可是傳達的資訊是一致的,是連貫相通的。」這是他最富有激情的回答,手也揮舞得比平常更猛烈。
他說,他雙重的世界觀產生了負面的結果。他與外國人的友誼,尤其是外國猶太人,受到了反對者的攻擊。「過去13年裏,他們一直指責我是猶太人的代理人,或者與猶太人爲伍,」他說。「競選期間,在每個村子裏,這些人都會舉起我和保羅•沃爾福威茨的合影。」
但是,他繼續談論農村選民:「如果你把《古蘭經》闡述爲自由的本質,就能和他們凝聚在一起。『你們都生而自由,你們都是阿丹的孩子,爲什麼還要因爲種族、宗教或膚色的差異而侮辱別人呢?』」這樣的態度在正統的宗教體制內並不流行,但是他表示,辯論是健康的。安瓦爾總結道:「他們說:『可是你這種解釋和別人不一樣啊。』好啊,讓別的謝赫來反駁我吧!」爲了強調,他邊說邊敲打著旁邊礦泉水瓶的側面。
安瓦爾公開演說時措辭猛烈,這一點爲人熟知。我們準備離開時,我問他是否期待回國開始競選造勢。他回答說是,我相信他。儘管我情不自禁地覺得,他一定很希望在自己的祖國不必這樣或那樣拐彎抹角地辯解,不必努力將西方和東方結合在一起。分別時,我祝願他無論行走的道路還是政治前途,都能一路順風。不過我懷疑這大概是他在一段時間裏,最後一次引用莎士比亞。
詹姆斯•克拉布特裏是英國《金融時報》駐孟買記者
譯者/何黎
白沙瓦里餐廳 (Peshawri)
地址:Sahar Andheri (E), Mumbai 400 099
2份拉西:680.00 盧比
白沙瓦烤羔羊肉:1900.00 盧比
唐杜裏土豆:1750.00 盧比
小扁豆湯:700.00 盧比
2份蒲迪納烤餅:450.00 盧比
拿鐵咖啡:275.00 盧比
咖啡:275.00 盧比
礦泉水:200.00 盧比
軟飲料:200.00 盧比
總計(含服務費):6447.51 盧比(合81.90英鎊)

大雪已連下了超過24小時,給哥本哈根鋪上了一張白色地毯。克里斯蒂安堡宮(Christiansborg Palace)外,一名工人正在剷雪。這座新巴洛克風格的建築既是丹麥國會大廈,又是首相辦公室所在地,被簡稱做「城堡」(Borgen)。
它的入口跟唐寧街10號的風格迥然不同。走進不起眼的大門後,訪客被一部狹窄的電梯載到首相辦公室。屋子裏安靜得讓人不安,寬敞的走廊上,只有一名臨時工慢悠悠地走著。
就在我拜訪過三天後,丹麥政府陷入了一場危機。由於高盛(Goldman Sachs)對丹麥國有能源公司Dong Energy的80億克朗(14億美元)投資激起民衆抗議,少數黨執政聯盟中的三政黨之一宣佈退出聯盟。這場風波導致這個中左翼政府再次改組,這已是該政府自2011年9月上臺以來所進行的第七次改組。
不過在我到訪時還一片祥和。我被帶領著從一位祕書身邊走過,來到一間寬敞的辦公室門前。在門口站著的,正是丹麥首相赫勒•託寧-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她在任已兩年半。
託寧-施密特今年47歲,她出名的地方有很多:在歐洲一大片中右翼政府首腦中,她是少有的社會民主黨人,而且很大程度上基於這一原因,她被視作布魯塞爾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主席人選之一。國際方面,隨著去年12月她與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和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在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追悼會上「自拍」事件的迅速傳播,她的知名度也急速竄升。
在流行文化方面,她還有更多軼事可講。引發收視熱的丹麥電視連續劇《權利的堡壘》(Borgen,以一位女首相爲主人公)的女主人公與她有很多相似之處。她是前英國工黨領袖尼爾•基諾克(Neil Kinnock)的兒媳。她的外號是「古馳赫勒」(Gucci Helle)。託寧-施密特在國際上頗富魅力。
她作了決定,我們午餐就去內部餐廳把菜端回到她辦公室喫。跟在一位安保人員身後,我們走下大階梯,經過一間貌似儲藏室的房間,裏面擺著一臺桌上足球(「沒人玩這個」,託寧-施密特說)和廢棄的廚房設施。餐廳很小,菜餚種類也相當有限,但看上去很可口。
我倆都選了對蝦當前菜,熱菜我選的咖哩飯,在我盛菜的時候,首相跟一位廚師聊到了她喫過的某種美味的魚肉。(我猜測的。託寧-施密特跟我交談時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我們回到樓上,在她辦公室裏一張大會議桌上用餐。託寧-施密特興致勃勃地宣佈:「我真餓了。」我倆在數秒內就剝去蝦殼,期間隨口聊了幾句天氣。她說:「一開始下雪,這兒就會有點亂。」當週晚些時候,一場政治風暴席捲了哥本哈根,我想起了她這句話。
託寧-施密特脫下灰色外套,挽起紫色套頭衫的袖子。言外之意很明白:開始幹正事吧。午餐前我已想好提問先從流行文化入手,然後再層層推進到嚴肅話題。
她非常驚訝「自拍」事件引起的風波吧?她受到種種譴責,包括在追悼會上作出與政府首腦身份不相符的舉動,以及對歐巴馬賣弄風情。「我非常驚訝。」她嚥下一口咖哩飯說道,「當時現場有人載歌載舞,氣氛相當好。各國政府首腦並沒被安排固定座位,我們到了以後都是自己找的座位。所以一切都有點隨意,很輕鬆,然後大家聚集到我那個角落,但不是因爲我,而是衝着我旁邊坐的那位。
「我們拍了不少照片,但主要是爲了好玩,因爲這種拍照方式把人們湊到一塊,非常有趣,而且人們在自拍相片裏總顯得很可笑。所以我喜歡自拍。」她又喫了一大口飯。
有些人辯白這些照片說明政治家也可以不拘禮節,上鏡的託寧-施密特強烈傾向這種說法。「我是個嚴肅的人,我工作勤奮,打交道的人也都非常嚴肅,但我也喜歡開懷大笑。」
但有些評論卻頗爲毒舌,比如《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的安德烈婭•佩澤(Andrea Peyser)用「丹麥放蕩女」(Danish tart)來指稱託寧-施密特。「我覺得這種說法更多說明了他們的爲人,而不是我們。」她字斟句酌地回答道。「我不太覺得他們是在針對我,所以對我完全沒影響。」
那麼,人們的反應是否說明了女人從政會面臨的困難,以及傳媒的雙重標準?「女人和男人從政當然有很大區別,如果我是個男的,有些評論壓根不會出現。不過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現實就是如此,我也不打算花時間去琢磨這些事情。 」
. . .
託寧-施密特向來卓然不羣。她的父親是商學院的數學和經濟學教授,她在哥本哈根市郊高中唸書時就是風雲學生。她在大學攻讀政治學專業,畢業後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爲丹麥社會民主黨(Danish Social Democrats)工作,接著擔任了丹麥工會聯合會(Danish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國際顧問,後於1999年當選歐洲議會議員(MEP)。
除了託寧-施密特本人之外,她的家庭成員都是保守派選民,她是這個家庭中的第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2005年,她成爲歷史悠久的丹麥社會民主黨的首位女黨魁,接著又在2011年成爲丹麥第一位女首相。
就像昔日的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託寧-施密特也不得不承受著媒體對她手提包的大量關注。當時同爲社會民主黨歐洲議會議員的弗雷迪•布萊克(Freddy Blak)給她取了個外號「古馳赫勒」——她有個古馳的手袋——結果就傳開了。「如果別人給你取了個好玩的外號,就會傳開,這很正常。」當我問及她對此事的感受時,她簡單回答道。
根據丹麥記者雅各布•尼爾森(Jakob Nielsen)的書中所言,託寧-施密特一開始對這個外號的反應很激烈。他寫道,她衝進布萊克的辦公室說:「你他媽憑什麼在外面叫我古馳,就因爲我沒跟你一樣穿得跟屎似的到處走嗎?」
兩位政治家後來成了好友,如今她談起這件事時表示:「這說明我做人坦率。我會跟同事說出來,也說明我不愧是從哥本哈根南郊來的。」
在即將擔任首相前,託寧-施密特去利比亞看望丹麥駐軍,結果被拍到她身著迷彩防彈背心,足蹬高跟鞋,手上拎著個大紅色的手提包。丹麥最嚴肅的報紙《貝林時報》(Berlingske)給這篇報導起的標題是,「赫勒帶著她的名牌包前往戰場」。
當我們聊到北歐國家公職人員裏有相當多女性,而且挪威(我居住的地方)就有女首相和女財政部長時,她放下了叉子,而她的主菜才喫了一半。我決定重提剛纔的話題,再問最後一個關於自拍的問題。爲什麼這件事在世界各地都引起熱議,但在丹麥人們的反應卻平靜得多呢?
她直視著我說:「說實話,我不想談論這個話題。我認爲採訪女性政治家時,如果前半段時間的訪問都在女性從政上打轉,是件很失禮的事。這對被採訪對象不尊重。」
我自然樂意聽命,但難免感到一陣尷尬,我發現自己竟懷念起餐館裏嘈雜的背景聲。我迅速轉開話題:考慮到歐洲近年來的緊縮議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中沒有幾個同爲中左翼政黨執政的政府,身爲一位社會民主黨人,日子想來不輕鬆吧?
「是的,確實不輕鬆。」她同意道。她說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金融危機,在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裏,丹麥受創最重,因此極左派「我們憎恨所有形式的市場經濟」的主張變得更有吸引力,而社會民主黨不肯堅決譴責這種觀點。第二個原因,她認爲 「普通工人階層」,即她所在政黨長期以來傳統支援陣營,不再是天生的社會民主黨人。
「市場是一個糟糕的主人,卻是一個優秀的僕人,今天依然是這樣,也就意味著我們依然要搞市場經濟,但我們必須透過調控來讓它造福每個人。這依然是我的行動綱領,也依然是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解。」
託寧-施密特接任首相時,在金融危機中受創的丹麥正處於恢復階段。數家丹斯克銀行倒閉,丹麥家庭債務水準居世界第一。在此背景下,新一屆政府推出了讓中左翼選民深感失望的改革政策,比如與中右翼反對黨合作透過稅收改革方案,以犧牲養老和失業救濟福利爲代價,讓部分高收入者受益。稅改措施,再加上一系列沒有兌現的競選承諾,讓社會民主黨的民調支援率跌到至少一百年來的最低點。
「這一切當然不容易,而且可以說異常艱難,但又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有一個觀點,社會民主黨的議程核心應該始終是竭力成立平衡的經濟。這就意味著改革。」她說。
. . .
她推開面前的盤子,接著說到了中右翼反對黨希望利用這場危機來削弱政府的重要作用。她強調說這一幕不該發生。
「那又能怎樣呢?現在唯一該做的,就是拼力改革國家。如果人們繳納著高額稅費(丹麥的所得稅率居世界前茅),他們自然期待得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衛生服務。」她說。
雖然她的改革在丹麥中左翼陣營中不太受歡迎,但國外卻相當看好。布魯塞爾的知情人士甚至提到,託寧-施密特有希望作爲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執掌歐洲議會。
但託寧-施密特完全沒有過這方面打算:「我非常榮幸能擔任這個偉大國家的首相。我還有太多事要做。而且,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以首相身份繼續努力爲丹麥人民服務。」
自從她組建政府以來,對本屆政府壽命的擔憂就從未中斷,而今三個少數黨執政聯盟成了更脆弱的兩黨聯合政府。只剩下了社會民主黨和社會自由黨(Social Liberals)。
我問起關於少數黨政府(現在只佔議會三分之一席位)所必然奉行的實用主義。「如果你想執政,就必須與其他政黨共同執政。如果你是少數黨聯盟,就必須爲你的政策爭取多數支援。這可能非常難,因爲需要經過漫長的討論。不過從很多方面來看,務實創新,兼聽各方意見並擇優採納,這難道不好嗎?」
這是非常北歐式的行事風格。我提起似乎讓全世界著迷不已的北歐社會模式,她用明顯的個人化表達回應道:「對常人而言,這是非常令人感興趣的模式,因爲在我們所創造的社會里,一個像我這樣來自哥本哈根南郊離異家庭的孩子,不用家裏掏一分錢,也能拿到學位,上好學校,還可以當上首相。」
她繼續道:「我覺得,我可能是全世界過著最平凡生活的首相。我要洗自己和孩子們的衣服。」
她問我要不要咖啡。當我請求換成茶時,我被招待了一杯我迄今在北歐地區所見識過的最棒的茶(在北歐國家,茶被可悲地等同於格雷伯爵茶)。
這種英式茶讓我聯想起她的公公,基諾克勳爵給過她許多政治建議嗎?「他給過我建議,但是我從他,以及我出色的婆婆(基諾克男爵夫人,前歐洲議會議員)那兒感受最深是,他們總是很坦率,從不過度操心,而且倆個人相互支援。」
託寧-施密特在比利時歐洲學院(College of Europe)就讀時,遇到了同在此求學的史蒂芬•基諾克(Stephen Kinnock),二人於1996年結婚。他在倫敦工作,週一到週五就由她獨力照顧兩個十幾歲的女兒(他們沒請保姆)。「我充分意識到自己需要貼近日常生活,在許許多多的事情上都和所有人一樣。我會跟孩子同學的家長聊天,我要參加家長會,我得去商店買生活用品,我要做飯,跟鄰居交流 。」(當天夜裏,她被拍到在自家屋外人行道上剷雪,再度印證她有著普通人的一面。)
她的丈夫正謀求成爲工黨候選人競選亞伯拉昂議員,這個威爾士選區以重工業聞名,比如塔爾伯特港(Port Talbot)鍊鋼廠。她會給他建議嗎?「我們什麼都聊,我對此很感興趣。而且我覺得,正因爲我和他都瞭解政治,所以聊起這類事來更輕鬆。」
一個小時的談話漸入尾聲。訪談結束時,她幽默地提起自己沒喫完的午餐。「我們喫得太快了。我沒辦法邊喫邊聊,結果連菜都沒顧上喫,這顯然要怪你啦。不過我喫了一些巧克力,但你沒喫,我看到了啊。」我及時進行了補救。
當我們一起走向門口時,我想起還有一件事要做:一起自拍。「哦,當然。這對我可是件大事。」她應道。
理查德•米爾恩(Richard Milne)爲《金融時報》駐北歐記者
-------------------------------------------
哥本哈根
克里斯蒂安堡宮
首相辦公室餐廳
對蝦兩份
咖哩飯兩份
乳酪
咖啡
茶
巧克力
全部免費
譯者/曲雯雯

當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落座準備開始午餐時,我還在手忙腳亂地搗鼓自己的錄音機——我帶了兩臺錄音機,以防其中一臺出問題。李顯龍微笑著說:「美國國家安全域性(NSA)會給你一份談話記錄的。」
這是一句讓人意外、具有顛覆作用的話,我本以爲李顯龍是位典型的嚴肅人物。這位總理先生有著理性技術專家的美名,全身上下就沒有一根輕浮的骨頭。他甚至連外表看起來都很嚴謹樸素——瘦高身材,灰色的頭髮,穿著深色西裝,打著領帶。因此在我們共進午餐期間,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李顯龍經常面帶笑容。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裏,面對一系列尖銳話題,李顯龍常常不是低聲輕笑就是滿面微笑,和話題本身顯得有點不太協調——這些話題包括二戰期間日本對新加坡的佔領,西方對於烏克蘭革命的處置失當,中國對於分離主義運動的擔憂,以及冰島的破產。我的感覺是,笑著談論這些話題,並不代表這位新加坡總理先生是位鐵石心腸的人。這只不過是他讓一些棘手話題顯得不那麼尖銳的一種方式——邊笑邊討論問題。
上午11點我們在倫敦皇家花園酒店(Royal Garden Hotel)的公園露臺(Park Terrace)餐廳碰面。這個時間對於午餐來說有些早,但這一個小時的時間是他手下工作人員在他訪歐期間各項活動的間隙中擠出來的:他要參加在荷蘭舉行的核安全峯會,發表多個演講,和商界人士以及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會面。當天晚些時候,他還要去倫敦東部的一個公園參加一場慶祝新加坡日(Singapore Day)的活動,登記參加此次活動的新加坡僑民多達一萬人。李顯龍手下的工作人員在我們會面幾天前就將餐廳菜單用電子郵件發給了我,並記下了我點的菜,這體現出了新加坡人典型的縝密精神。我們被帶到了位於餐廳一角的一張餐桌,能夠俯瞰肯辛頓花園(Kensington Gardens),並享受透過窗戶傾灑下來的陽光。我們的第一道菜——三文魚蟹肉醬——很快就端了上來。由於時間尚早,我們仍繼續喝水——李顯龍的身材偏於瘦削,看起來頗爲健康,我覺得他不太可能是一個好酒之人。
. . .
今年62歲的李顯龍於2004年成爲新加坡第三任總理,他的早年生活爲他擔任這個職位做好了極其周密的準備。他的父親是李光耀(Lee Kuan Yew),新加坡的首任總理和國父。李顯龍接受的是中文普通話和英文的雙語教育。和他的雙親一樣,李顯龍入讀了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並於1974年獲得了數學一等榮譽學位以及電腦科學文憑。在此後的十多年時間裏,他一直在新加坡軍隊效力,並升至准將軍銜。隨後他步入了政界。雖然有著鍍金般耀眼的職業生涯,李顯龍同樣遭受過人世滄桑的打擊。他的第一任妻子於1982年去世,當時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剛出生不久。而他自己也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接受過癌症治療。
在劍橋期間,他曾被建議繼續深造,完成研究生學業。我問他,當時是否動過心?他的臉上露出了眷戀的表情,答道:「那將是一件極好的事,但你不可能真正去做,不是嗎?我在劍橋求學是用獎學金,而且我在祖國還有責任。」
我問他,是否一直以來都深知自己將會繼承家族事業,進入政界?他的聲音中略有一絲鋒芒,回答道:「不,我並不知道。這不是什麼家族事業。」我腦中隱隱敲響了一記警鐘,我想起了這位總理先生曾經成功地迫使包括英國《金融時報》在內的媒體機構做出道歉和賠償,這些媒體暗示李氏家族透過裙帶關係獲利。
在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期間,他不斷強調新加坡的不安全處境——以此鞭策本國公民努力工作,保持警惕。由於新加坡是一個僅有530萬人口的城邦國家——1965年新加坡在非自願情況下獨立,因其當時被驅逐出了馬來西亞聯邦——這種警惕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那以來,新加坡實現了長期和平,繁榮景象蒸蒸日上,如今新加坡已是全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國家之一。因此我問李顯龍,新加坡人是否仍然需要保持不安全感?
他說:「如今新加坡人普遍更有安全感了。」但他隨後略微皺眉補充稱:「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提醒國人,當前的局面是在意志支撐下不斷奮鬥的結果,適度的不安全感還是很有幫助的。你不用變成一個偏執狂,但你確有必要非常嚴肅地對待風險。」他說,把眼光放長遠有助於提醒新加坡人繼續保持警惕。「沒有多少小型城邦國家能夠長期存續,不過威尼斯是個例外,這座城邦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存續了900年。」
確保安全的一個重要方式,是與鄰近大國保持友好關係。新加坡同時被中美兩國看成是值得信賴的夥伴,這種情況非常罕見。新加坡人很早就對中國的經濟奇蹟充滿信心,並且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投資者,中國官員也常向新加坡借鑑經濟和政治思路。但新加坡同樣定期會迎來美國海軍進駐。我問李顯龍,中國對於新加坡口頭支援美國軍方在太平洋地區繼續保持存在有何看法?他淡然地答道:「中方對此並不高興,不過他們能夠理解。」
只要國際環境繼續保持和平,與所有大國都保持友好關係對新加坡而言是一項明智的戰略。但近來亞洲地區內部的緊張態勢持續加劇,特別是中日兩國因領土爭端更是劍拔弩張。很多西方觀察家將局勢愈發緊張的原因單純歸結於中國的崛起。但在李顯龍看來,日本也在發生變化,該國政府正在維護其所認爲的「日本民族主義者的權利」,這主要體現在對歷史的闡釋上。「有人對如何定義侵略行爲提出了質疑,因此,鑑於沒有相關定義,日本在戰爭期間又是否犯下過侵略罪行呢?」
新加坡在戰爭期間曾被日本佔領。因此我問道,新加坡人「是否普遍認爲日本犯下了侵略罪行?」
總理先生的語調突然變得不那麼平靜了。他在椅子上將身體前傾,並提高了嗓音,聽起來似乎對我的問題感到難以置信。「是的,當然,他們侵略了新加坡,殘殺了數萬民衆,我的父親也險些送命,幸運的是他活了下來,不然今天我也不會坐在這裏了!」他大笑道。「但我的叔叔被抓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李光耀的領導風格屬於被二戰的血雨腥風塑造的那一代人。他的兒子在一個不同的時代條件下領導新加坡,因而必須採取一種不同的領導風格。「我的父親常說,『看看戴高樂(de Gaulle),他每隔很長一段時間才發表一次公開講話,每個人都會仔細傾聽,其他時候他則保持沉默。』但那是在過去,如今的世界已經大爲不同。」李顯龍最初對社群媒體有些抗拒,現在已經轉變了態度:「我的同僚們會上網,使用Facebook,他們覺得社群媒體很有幫助,並勸我說我應當嘗試一下,於是我試了。只要你恰如其分,還是很有意思的……可以時不時地插入一條嚴肅訊息。」今天早上,總理先生髮布了一張照片,是他自己拍攝的倫敦日出。
爭取選民支援——不論是活生生的個體還是Facebook上的粉絲——是民主國家領導人會做的事。但從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來看,新加坡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民主國家——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自新加坡1959年實現自治以來一直掌權。批評人士指出,雖然新加坡定期舉行選舉,但事實上是一個一黨專政國家。在2011年舉行的上一屆大選中,反對黨總計贏得了創紀錄的約40%選票。即便如此,人民行動黨仍然贏得了議會87個席位中的81席。因此我問李顯龍,能否想像有一天人民行動黨不再執政?他溫和地答道:「這很有可能發生,我不知道這將以何種方式實現,但這是可能的。」過了一會兒,他暗示稱人民行動黨正開始考慮有朝一日組建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屆時或許不會是一幫人進去,一幫人退出,情況可能會更加複雜——你將會逐步適應比英國當前政局更加複雜的局面。」
. . .
一位侍者走了過來,端上了第二道菜。我們都選擇了當天供應的魚,端到我們面前的是一塊非常美味的烤比目魚。我大快朵頤,但總理先生幾乎沒動自己的那份。
隨著主菜端了上來,我將話題轉回了國際事務。在歐洲,每個人都高度關注烏克蘭危機,因此我想知道,這一事件在新加坡是否也產生了類似的影響。「烏克蘭危機沒有引起新加坡人的高度關注,但它和我們確有關係。事實上,我曾在Facebook上就此發表過一條評論,出乎我意料的是,這條評論吸引了大量關注。因爲新加坡是一個小國,我們依靠的是國際法、國際條約、國際協議,以及這些規則的神聖性。如果這些規則被踐踏或者無視,那麼我們將面臨嚴重問題。」他指出,早前由英國、美國以及俄羅斯簽署的一項協議保障了烏克蘭的領土完整性。
我問他,怎麼看待西方到目前爲止所做的反應,以及是否認爲西方的反應足夠有力?
「我不認爲西方還能再多做些什麼。我認爲西方應在鼓勵獨立廣場(Maidan)上的示威者之前就想到這一點。」那麼西方的做法是否不負責任?「我認爲,有些人沒有通盤思考過可能出現的各種後果。這種情感上的支援可以理解:他們和你們擁有同樣的價值觀,他們想要和你們建立聯繫……這些人是充滿熱情的理想主義革命者,在某些方面,會讓你回想起《悲慘世界》(Les Mis)。但你能否爲所產生的後果承擔責任?當悲傷的時刻來臨,你是否能去到那裏?」他回答了自己的問題:「你去不了那裏,你還有很多其他利益需要保護。」
現在我們開始品嚐布丁。我很喜歡我的這份樹莓漩渦冰淇淋,但上午這個時點喫巧克力撻似乎有點太膩了。按照我們拿到的特別印製的菜單上所寫的,端到總理先生面前的是一份開心果焦糖布蕾。但它看起來更像是一碗樹莓加草莓。不管究竟是什麼,李顯龍都沒有碰自己的甜點,雖然這份甜點看起來非常誘人。我忍住了想要伸手抓一把他的樹莓的衝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都會是一種失禮的行爲,但在一個新加坡人眼裏,這種行爲可能會格外令人反感,因爲新加坡政府花費了大量精力,設法讓本國民衆培養良好的舉止和積極的生活習慣。過去幾十年間,新加坡開展了大量的公共宣傳活動,敦促本國公民修剪頭髮,在乘坐軌道交通時不要推擠,在享用自助餐時不要將盤子裝得過滿——還有很多其他事項。
總理先生是「新加坡日行一善理事會」(Singapore Kindness Movement)的贊助人,該組織旨在倡導人們改善行爲。但他也說過要淡化新加坡的保姆國家氛圍。當我問到新加坡現在是否開始「略微放鬆一點」時,李顯龍微微一笑。「我認爲現在道路已經變得更寬闊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限制,而是表明人們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他沒有把「保姆國家」這個詞看成一種侮辱。「當人們聲稱他們不需要一個保姆國家時,他們其實處於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而不受阻撓,另一方面,如果出了問題,他們又希望得到救助。」
一名侍者走了上來。李顯龍點了早餐茶——畢竟現在還沒到中午,而我則點了一杯義大利特濃咖啡。我們接著談到了新加坡作爲一個金融中心的角色。隨著瑞士的銀行保密傳統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新加坡常常作爲國際自由流動資金的新避風港被人談起。我問到,新加坡是否注意到了資金從瑞士流入的情況?他以一種一反常態的含餬口吻答道:「我不知道資金來自哪裏。我們的私人銀行財富中心正在逐步建立。我認爲其中或有部分資金來自瑞士地區。」
作爲一個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成爲巨大財富的來源,但同樣可能帶來巨大的不穩定性。在李顯龍小口喝茶時,我問他是否擔心再爆發一場重大金融危機。他堅定的說:「在某個時候會發生一些其他的金融危機。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本質。你只能寄望於自己事前建立了足夠牢固的防火牆,以及危機本身是可控的。但事實上這非常難以做到。」
今天已經沒有時間談論金融危機了。現在已是中午,李顯龍要前往倫敦的另一邊參加活動。在我們準備結束訪談之際,我問他是否會懷念自己的私隱——並提到了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對於自己再也不能隨意逛進一家書店的感嘆。他合情合理地說道:「我並沒有處在歐巴馬的位置上。我走進一家書店,人們認識你,於是他們會走上來跟你打招呼,並和你自拍留念。但如果他們假裝不認識你,你也會感到非常不安!」我們握手告別,他準備動身前去參加新加坡日的慶祝活動。在那裏他會跟很多人見面,做出很多決定——此外還有很多自拍要拍。
本文作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國際事務專欄作家
-------------------------------------------
公園露臺餐廳
皇家花園酒店,倫敦肯辛頓高街(Kensington High Street)2-24號,郵編W8 4PT
三道菜套餐 2份 40.00英鎊
三文魚蟹肉醬 2份
比目魚配羅勒奶油汁 2份
巧克力撻配樹莓漩渦冰淇淋
開心果焦糖布蕾
Hildon牌純淨水 4.50英鎊
Hildon牌氣泡水 4.50英鎊
義大利特濃咖啡 5.50英鎊
早餐茶 4.75英鎊
總計 59.25英鎊
譯者/馬拉

圖爾基•費薩爾親王抵達前,我已經足足等了20分鐘時間,他顯得有些狼狽。「我的司機只得讓我在離這裏五個街區的地方下車,」他略帶歉意地說。「所有的街道都被警戒隔離了。」我告訴他折騰出如此大動靜是因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正造訪華府。這位沙烏地前情報機構首腦笑著說:「這只是內塔尼亞胡造成的其中一次麻煩而已。」
我倆原先約定在毗鄰白宮的高檔燒烤及海鮮餐館Occidental Grill & Seafood共進午餐。除了路障外,餐館外面還留有厚厚的積雪。69歲的費薩爾親王穿了好幾層衣服,頭戴黑色呢帽,進屋後,他就把外套與帽子交給了衣帽服務員。
爲了儘可能減少外界噪音的干擾,我預定了一個包間。這能管點用,但仍隔擋不了餐館裏播放的上世紀50年代的拙劣曲目。
費薩爾親王擔任沙烏地情報總局(General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ID)首腦長達24年,可能是這個世界上經驗最爲豐富的間諜,就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案發生前10天,他卸任該職。卸任情報主管後,他擔任沙烏地駐英國及愛爾蘭大使,而後又擔任了駐美大使。他如今在沙烏地首都利雅德(Riyadh)負責一家名爲薩爾國王伊斯蘭學術研究中心(King Fais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的智庫,同時奔走於全球各地舉辦講座以及訪親會友。我說,聽起來這是相當愜意的生活。「對我來說,這宛如人間天堂,」他這樣回答道。
圖爾基是沙烏地王室(the House of Saud)的直系後裔,是費薩爾國王(King Faisal)的么兒,費薩爾國王本人於1975年遇刺身亡。圖爾基的哥哥費薩爾親王(Saudal-Faisal)是沙烏地現任外長,他的哥哥們及堂兄弟們掌握著政府各個部門的要職。
圖爾基將在華盛頓逗留幾周時間,主要是在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講學,他曾在此求學(於1968年本科畢業)。上大學前,他曾在普林斯頓附近的勞倫斯威爾(Lawrenceville)寄宿學校就讀。我說:華盛頓就好比您的第二故鄉。「沒錯,但我有很多第二故鄉,」他這樣說道。「倫敦、巴黎都算,我經常出訪,訪親會友。我直抒胸臆,盡情享受著生活————這一切都要感謝真主。」
我暗示他:60年前,還是青少年的他初次踏上了美國國土,從此以後,美國毫無疑問是他首屈一指的第二故鄉。他點頭稱是。我倆的談話被走過來拿菜單的服務員打斷。圖爾基點了一份半熟的腰板牛排與苦苣沙拉,飲品則點了冰茶;我則要了份緬因龍蝦卷(Maine lobster roll)與副餐沙拉,飲料則選了健怡可樂(Diet Coke)。圖爾基急著繼續發表自己對美國的感想。
「美國人身上有些不變的性格特徵,」他說。「其中之一就是對外人特別有好奇心,他們希望知根知底————他們會詢問你的家庭狀況。正是這種稟性讓外人與他們拉近了距離。他們對你的一切早已瞭如指掌,如今一切盡在谷歌(Google)上。無論是作爲中學生、政府官員還是如今的垂垂老者,在我與美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莫不如此。美國人十分好客————他們隨時願意以某種方式款待來客。他們身上始終有非常可愛的品質。」我想知道的是:有此境遇,是否由於他是沙烏地王子的緣故,但我最終決定默不作聲。
. . .
我們點的兩道菜一下子端了上來後,我問他美國這些年發生了什麼變化。他一邊大快朵頤著牛排,一邊不間斷地回答我。他的行爲舉止很親切,但他的目光依然那麼犀利。看得出來,他說起美國來顯得滔滔不絕。「上世紀60年代,我在美國求學時,強森(LBJ)是當時的美國總統————他掌控著一切。他推出了偉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即對內實行社會改革,推行福利社會;對外則在越南發動了大規模的戰爭————派了50萬美軍到那兒,」他說。但如今這一切已時過境遷。美國如今處於選擇的時代,卻似乎又無法做出選擇。「在強森當政的時代(本人當時還在上大學),他很擅長讓共和黨支援自己推行各項政策,」圖爾基說。
「如今的美國社會則是嚴重兩極分化————到處瀰漫着反覆無常與心煩意亂的情緒。兩種極端不斷撕裂美國社會,卻缺乏讓其迴歸正常的中心力量。中間力量過去可以起消彌作用————過去美國社會有『減震器』。如今則不復存在了。」
我問他:美國國內問題如何影響中東局勢?一聽到我提及他自己國家所在的地區,圖爾基的語速明顯慢了下來。他提醒我: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馬上就要對沙烏地進行自2009年以來的首次國事訪問。2009年,歐巴馬總統向沙烏地國王鞠躬後,美國國內保守派指責其「屈膝卑躬」。如今已時過境遷。美沙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糟糕。沙烏地王室曾與小布什兩屆政府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但對歐巴馬政府極度不信任,尤其是歐巴馬政府致力於與伊朗進行核談判,而沙烏地卻把伊朗視作不共戴天的死敵。「坊間都在傳美國準備撤出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從中東撤軍,」圖爾基說。
「對於沙烏地來說,必須堅決反對一條路,而在過去,我們並不如此。如今唯有接受現實,勿庸置疑,世界格局已經徹底發生改變。去年9月,歐巴馬在聯大發言,明確表示美國將只關注巴勒斯坦與伊朗,而敘利亞、利比亞、蘇丹、葉門、馬利、伊拉克以及埃及等國家只能自謀出路。所以,沙烏地不管是利用自己的資源親力爲之,還是幫助本地區其它國家應對上述挑戰,都必須逐漸適應美國撤離中東的現狀。」
我很清楚圖爾基如今在西方仍是頗具爭議的人物。2004年,法國《巴黎競賽》雜誌(Paris Match)指控其早已提前知曉9.11恐怖襲擊一事,隨後,法院判決雜誌社賠償圖爾基損失費。2005年,美國法院做出裁決:圖爾基與其他沙烏地政要免受9.11恐怖襲擊相關指控(儘管該案目前仍在上訴中)。圖爾基稱基地組織(al-Qaeda)爲「邪教」。但他選擇在9.11恐怖襲擊發生前10天卸任沙烏地情報機構首腦,這一事實本身就是缺乏遠見卓識的表現。我問他:9.11恐怖襲擊屬於情報失察嗎?「沒錯,每個人都難辭其咎,」他這樣回答道。「如今回想這一切,種種跡象應該引起注意,各國情報機構應該互相分享相關情報,而事實上這些都沒有。我也知道如今各方都在竭盡全力避免此類失察行爲(無法準確研讀相關資訊)再度發生。這也正是9.11這類驚天動地的大事沒能再在美國及沙烏地重蹈覆轍的主要原因所在。」
圖爾基把盤中的牛排一掃而光,旁邊的綠色蔬菜則絲毫未動。服務員問他是否想來點甜點。一陣切磋後,他要了乾酪餅,外加一勺香草冰淇淋。有感於此,我也順勢選了焦糖奶油(crème brûlée),另外要了雙份濃縮咖啡(double espresso),圖爾基則要了普通咖啡。我很想知道他如何評價美國情報機構現在的表現。就情報收集、情報研判以及具體行動執行能力而言,我要圖爾基點評全世界最出色的情報機構。他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
「就收集原始情報而言,美國特工因在技術與財力上具有優勢,無疑是獨佔鰲頭,」他說。「就人力資源而言,我認爲英國特工在某些特定領域的專業技能最出色(在自己當沙烏地情報機構主管期間,當然是蘇聯特工最厲害,人見人怕)。英國情報分析師的第一手報告總能提供獨特視角與專業知識,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也許就行動執行力以及能力發揮而言,我覺得以色列特工最爲出色,儘管他們也曾犯很多錯誤,但總能出色完成任務。」
我問他爲何沒提到中國特工呢?「2001年以來,這是情報界變化最大之處,」他說。「我只能說中國情報機構在過去並非出類拔萃者。」
. . .
乾酪餅似乎不斷在加快圖爾基說話的語速,他講話的聲音既快又低。我突然脫口而出,你肯定喜歡喫甜食————真是典型的拜都因人(Bedouin,阿拉伯半島上的原住遊牧民)。圖爾基對我的觀察感到很困惑,並沒有理會我。我略微有些尷尬,因爲自己如此執迷於成見,進而再問他是否喜歡喫紅棗,就更顯唐突尷尬了。謝天謝地,這一回他算是正面回應了。「我喜歡喫棗,」他說。他對我說,自己取圖爾基這個名字,正是因爲他是家中八個兒子的老么。圖爾基的意思是「枝上留待日後摘取的未成熟棗」。「沒錯,本人特愛喫棗,而且每天都喫。」我完全不計後果地問他:是否爲出生在聖城麥加(Mecca)而自豪?「沒錯,這算是特權,但也沒啥太特別的,」他說。「有時告訴別人我是麥加人(Meccawi)是件很逗的事。」
. . .
喝完咖啡後,我又就國際事務提問圖爾基,問他如何評判普丁(Vladimir Putin)入侵克里米亞(Crimea)?「這老讓我想起童話故事,」圖爾基說。「大灰狼襲擊一羣羊後,狼吞虎嚥地喫著其中一隻羊,還不時招搖自己的本領,而其它羊則不斷哭訴。」說到這,他就模仿起羊咩咩的叫聲。他眨巴著眼睛。「這就是全世界的現狀。狼喫羊時,並沒有牧羊人來救羊羣。這就是我們如今面臨的窘境。」
但西方該如何應對呢?我提醒他:就在幾個月前,他曾批評歐巴馬總統,對方曾就敘利亞使用化武設定過紅線,而後又自食其言。圖爾基補充道:原先設定的敘利亞化武紅線演變成了「大肆使用」,最終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境地。歐巴馬政府對圖爾基的批評大爲不滿。「設定紅線後,就得言必行、行必果,」圖爾基現在說。「這也正是普丁最高明的地方。他一直不回應,我們既聽不到他怒髮衝冠,也聽不見他誇誇其談,啥都沒有。他就默不作聲。而全世界則哀號個沒完,整個局勢糟糕透頂。」但我問他:世界該如何正確回應?圖爾基笑著說:「你是英國人,應該知道英國輕騎兵當時衝鋒陷陣後的結果(在19世紀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中,英國輕騎兵向防守嚴密的俄軍陣地發起衝擊,結果損失慘重)。」
此問題告一段落後,我又轉向沙烏地國內的話題。沙烏地在西方社會、尤其在美國聲名狼藉,難道圖爾基爲此不擔心嗎?我提到了沙烏地禁止女性開車(當然類似不合理的情況還有很多)。「我當大使期間,與英國、愛爾蘭以及美國觀衆互動時,常被問到這樣的問題,『如今沙烏地最有價值的女性是誰?』答案是『有工作的女性』。在我小的時候,一家之長認爲讓自己的妻子或女兒去工作乃是奇恥大辱。他認爲自己才應該負起撫養家中女眷的職責。因爲教育的普及,上班的女性成爲引以爲傲者,給自己父母帶來了收入,自己也受到兄弟姐妹的尊敬,並得到求婚者的垂青。」
但我指出:女性至今仍不允許開車。他點頭稱是。「但我聽到自家的女性這麼說,開車並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在影響女性生計的繼承權、離婚,還有撫養孩子等方面,女性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女性希望國家應該優先改善這些民生問題,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允不允許女性開車方面,因爲開車問題屆時會順理成章地解決。」
服務員拿來賬單後,我對圖爾基說自己得趕去參加歐巴馬最新預算方案的通報會。他不由得笑了。「預算方案能透過嗎?」他問。我回答說不可能透過。「美國表現得像個第三世界窮國,」他說。停了一會兒後,他又補充道:「我昨晚參加了奧斯卡頒獎典禮。我轉向身邊的嘉賓說,『你知道嗎,這是美國最擅長的地方————舉辦盛典,觀衆蜂擁而至,歡呼雀躍,喫著爆米花,逍遙自在。在普通人的眼裏,這就是美國,美國人生活愜意。』」
我說自己基本贊同其看法,只有一點除外:那就是美國中產階層的生活日趨艱難。他打斷我的話後說:「但我那樣說一點沒錯,多數美國人生活富足。他們具有刨根問底以及殷勤好客的獨特稟性,他們覺得自己國家是人間天堂。但時不時地,他們的美夢被普丁這樣的人警醒,提醒他們需要直面現狀。」他笑著說。我還以爲他會模仿起狼的模樣。他戴上帽子後,我倆一起步出餐廳,外面一片銀裝素裹。
愛德華•盧斯是《金融時報》首席美國評論員
-------------------------------------------
Occidental Grill & Seafood燒烤與海鮮餐館位於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1475號,郵編:20004;
烤肉片:24美元
緬因龍蝦卷:25美元
Frisée and red endive salad $12.00
紅苦苣沙拉:12美元
副餐沙拉:3美元
乾酪餅:8美元
焦糖奶油:8美元
健怡可樂:3.5美元
冰茶:3.5美元
雙份濃縮咖啡:8美元
過濾式咖啡:8美元
總計(包括稅及小費):128美元。
譯者/常和

就在我與印度政壇嶄露頭角的平民黨(AamAadmi,「Common Man」)黨首阿爾溫德•凱傑裏瓦爾約定好的午餐時間前半個小時,我突然被通知約定取消。一天前,這位前稅務徵稽員,如今的社會活動家爲議會選舉進行宣傳造勢時,臉上被某機動三輪車司機扇了一巴掌。這是45歲的凱傑裏瓦爾遭受的最新人身攻擊,他拒絕全副武裝的安保人員爲自己保駕護航,選戰期間,這些警衛人員負責保護印度政客的安全。
爽約的凱傑裏瓦爾在媒體記者的簇擁下,來到德里地區的偏遠角落,親自看望襲擊他的三輪車司機,對方無地自容的道歉,得到了凱傑裏瓦爾的諒解,這種賺足媒體眼球的表演,凱傑裏瓦爾顯得得心應手,這讓他在印度馬拉松式的大選期間,獲得了電視媒體的免費報導。印度大選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選舉,共有8億多選民參加投票,結果於5月16日揭曉。
這種出其不意的宣傳招數對於競選經費捉襟見肘的政黨至關重要。凱傑裏瓦爾的平民黨挑戰實力雄厚的老牌政黨: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領導的執政黨國大黨(Congress party)以及莫迪(NarendraModi)領導的印度奉行民族主義的政黨人民黨(BharatiyaJanata party, BJP),印度民衆普遍對國大黨的執政表現失望至及,各界一致認爲莫迪有望奪取大選勝利。
一天後,我坐在德里高檔住宅區桑德納加爾(Sunder Nagar)某漂亮客廳裏愜意地喝著檸檬水,房屋主人(他是凱傑裏瓦爾的支持者)主動提供自己的住所,因爲只有在此處,我纔可以不受干擾地採訪平民黨黨首凱傑裏瓦爾。儘管如此,選擇在此採訪這位政治新星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爲對方總是標榜自己是「普通人」,大肆抨擊政界根深蒂固的特權文化。
房屋是印度傳統有權有勢精英階層的典型擺設:沙發、古董木式傢俱、舊的克什米爾(Kashmiri)地毯、以及各種藝術品。美術書、報紙以及雜誌堆放在一起;屋內還擺放著印度當代藝術家蘇伯德•古普塔(Subodh Gupta)的一幅齊桌高的不鏽鋼廚房餐具裝置作品。
凱傑裏瓦爾緊隨房主沿著花園小徑走過來,未見其人,已聞其聲。他穿著白色工作襯衣(口袋裏插著一支不值錢的鋼筆)、棕色褲子以及一雙舊涼鞋——典型的政府官員及中年中產白領階層的行頭。他臉帶微笑與我握手,並說道:「我對昨天的爽約深感抱歉。」
僕人給凱傑裏瓦爾端來椰子水。我對他說:您一定累壞了吧。他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說家,如今卻一聲不吭(頗讓人尷尬)。儘管如此,我仍不依不饒地問他:選戰讓您心力憔悴了嗎?
他點頭稱是。「身體疲乏之極,」他這樣回答道,「有時經受巨大挑戰,身心極度疲憊。」
他繼續道:「我接觸了數不勝數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民衆。他們目不識丁,每天在爲生計而奔波。很多人甚至不知如何填飽肚子。即便對於中產階層來說,優質教育與醫療資源也越來越難以企及。另一方面,國家政治則由少數公司、政治以及官僚利益集團操控。這並非真正的民主。」
凱傑裏瓦爾對我說起了造訪三輪車司機家的經過,他說,對方是受僱而襲擊他(儘管他不願透露幕後指使者以及動因)。「這位司機生活極度貧困,」他說。「只給幾千盧比,他就會豁出命去幹。這不是他本人的錯,而是我們這些爲政者的錯,應該把這一切歸咎於整個國家,我們的民衆只為區區幾千盧比,竟會如此鋌而走險。」(世界銀行(World Bank)統計數據估計:在全球12億赤貧者,印度就佔了4億人之多。)
. . .
批評人士(包括昔日支援凱傑裏瓦爾的中產階層)都抱怨他已失去了切實改善民衆生活的最佳時機——去年12月,他領導的誓言根除腐敗以及改革政府積弊的平民黨,在人口近1700萬的德里地區邦的選舉中初一亮相,便不同凡響。
在德里地方議會全部70個席位中,平民黨共奪得28席,組建少數派政府,凱傑裏瓦爾出任首席部長一職。他的「異軍突起」讓整個首都激動不已,成了大家茶餘飯後的談資,對兩大全國性老牌政黨不滿的選民來說,平民黨提供了很好的第三種選擇。
但民衆的激動心情很快煙消雲散。凱傑裏瓦爾無法透過立法來起訴地方行政機構的貪腐行爲,只當了49天首席部長便掛印而去。這對於平民黨的形象是個沉重打擊,我問他是否遺憾如此快放棄首席部長一職。
「我們爲政的目的就是改變現存體制,」他堅定地說道。「我們從不說『其它政黨黨員都不是好東西,我們平民黨的黨員都是好樣的;我們執政是爲了實現政清吏廉。』沒有人能做得到。所有進入體制者最終都會被體制所同化。要想改變體制,立法至關重要。如果無法讓法案在地方議會獲得透過,政府就難以爲繼。」
他繼續道:「我本可以繼續把持首席部長一職,但我最終決定辭職。這是做出某種犧牲。我們原以爲民衆會對有道德擔當的政治行徑歡欣鼓舞,沒想到事與願違,反對黨大肆開動宣傳機器,詆譭我們逃之夭夭。」
儘管許多人認爲凱傑裏瓦爾是個半途而廢者,但他說自己對平民黨的議會選舉前景充滿信心:「參加我們集會以及選戰造勢活動的選民人數翻了很多倍。」
這時房主人再次現身,把我們帶到餐廳,裏面擺著一張可坐10多個人的長條桌。兩個席位已經擺放妥當,每個人前面放著一個圓形金屬盤,裏面放著四小份印度蔬菜:青豆、菜花、咖啡茄子土豆,以及麻辣味鷹嘴豆糊(kadhi,用鷹嘴豆麪及酸奶肉汁做就),此外還有一份熱騰騰的烤肉及米飯。
身患糖尿病的凱傑裏瓦爾是素食主義者,他開始心不在焉地喫起飯來。我很想知道這位來自哈里亞納邦(Haryana,毗鄰德里)某小鎮、生性羞澀的男子是如何成長爲公衆人物的。凱傑裏瓦爾的父親是工程師,他是家中三個孩子中的長子,後來考中印度知名的哈拉格普爾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Kharagpur),畢業後到塔塔鋼鐵(Tata Steel)工作。1995後,經過競爭激烈的公務員考試後,他被印度稅務局(Indian Revenue Service)錄用。「我以前對政治與政客深惡痛絕,」他坦承道。
那麼,是什麼讓他放棄優越的中產生活、轉而投身政治呢?
凱傑裏瓦爾說:理想的破滅,就發生在自己20多歲在德里監督徵稅時:「一旦身在體制後,就意識到自己只是顆微不足道的小螺絲釘,對現狀根本無能爲力,」他說。周圍官員不斷收受賄賂後肆意對行賄者退稅,會計師曾告訴他如何賄賂其同行以謀取私利。
許多印度官員難以抵制收受賄賂的誘惑,即便拒絕貪腐者也常對身邊的貪腐行爲聽之任之。凱傑裏瓦爾則顯得與衆不同:「本人爲何對腐敗深惡痛絕,爲何別人身陷貪腐難以自拔,我不得而知,」他說。「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必須向哲學以及精神方面尋求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貪念在我內心並非根深蒂固,那麼這種定力又來自何處?」他笑著說。
他告訴我:上世紀90年代末,自己當稅務徵稽員時,曾當面聽到時任德里地區羅馬天主教大主教艾倫•巴茲爾•德•拉斯迪科(Alan Basil De Lastic)這樣談論貪腐行爲。大主教提到了「共同腐敗」(彼此簽訂大額互利合同,「行賄者與受賄者彼此都樂見其成,都不吱聲,都不說有啥問題」)以及「勒索性腐敗」——即在頒發準生證及護照等證明時索要賄賂。
「他對共同腐敗並不特別深惡痛絕,但說勒索性腐敗正把印度每個人推向腐敗境地。當全體國民(以及全體國民心態)都萌生貪腐之心時,整個國家都不可能向前發展進步。」
. . .
我邊聽他說,邊享受著美食。微辣味的蔬菜做得恰到好處,印度菜只有家庭烹製方能有此美味。主人又端來了些烤肉、米飯以及蔬菜。凱傑裏瓦爾叉了塊烤肉,但對其它菜則擺手拒絕。看到他喫飯如此有節制,我不想顯得自己是個貪喫鬼,於是對其中最簡單的菜煮青豆淺嘗就輒止了。
凱傑裏瓦爾於2000年開始投身政治,當時他幫助成立了團體,爲貧民窟居民抵制稅務及電力部門侵擾而出謀劃策。他辭去公職投身這項事業,但很快意識到這樣做既「難以複製也難以推廣」。於是他參與到利用2005年制訂的突破性法律(即公民有權獲取及瞭解官方檔案,而這些檔案之前成功逃避了公衆監督)的請願活動中。
2007年,凱傑裏瓦爾四處奔走,發起成立了揭露官員不當行爲的獨立反腐機構——「人民監察院」(Jan Lokpal)。運動於2011年達到最高潮,當時,包括商人以及寶萊塢(Bollywood)電影明星在內成千上萬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中產者加入到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中。凱傑裏瓦爾這位義憤填膺的城市「普通人」成爲整個運動的明星。當國大黨政府承諾設立相關機構解決此問題後,抗議活動很快偃旗息鼓了,但激進分子對最終出臺的「無關痛癢」法令甚是不滿。
2012年底,平民黨正式組建。「我們當時要求貪腐者透過立法,革自己的命,對方很顯然永遠不會這麼做,」凱傑裏瓦爾說,「我們於是意識到:只有自己起來改變印度的政治生態,否則一切永遠不會改變。很顯然,自己必須從政。這並非出於選擇,而成了漫漫征程的一部分,完全是水到渠成。」
. . .
僕人們端著盛放阿方索芒果(alphonso)塊的盤子走進屋來。因爲凱傑裏瓦爾是糖尿病患者,因此我問他是否可以喫。「我就喫一點,」他說。我仍覺得沒弄清楚凱傑裏瓦爾積極投身政治的確切原因,他目前有兩個學齡孩子,妻子仍在稅務部門工作。
是童年的偶像激發了他道義上的義憤填膺?「按照印度教哲學,『每個人從自己前世承繼這一切』,」他說。他是位虔誠的印度教徒,崇拜長著猴臉的印度教女神哈努曼(Hanuman)。
在大學,他成爲不可知論者,但隨著反腐運動風起雲湧,凱傑裏瓦爾重新皈依宗教信仰。「反腐運動規模越來越大,已遠遠超出我們當初的想像,我覺得這並非是我們的緣故。我們太過渺小,實在太過渺小,不可能改天換地。肯定有特別的力量、超自然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我不相信有哈努曼之類的神靈存在,但我真的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在發揮作用。如果始終秉承真理之路,那麼所有超自然的力量都會以某種方式支援你,一切慢慢開始應驗和改變。這就是我的信仰。」
他隨後提及了自己的俗世偶像——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正是甘地,向世人展示了真理及非暴力原則的非凡力量。他的生活始終秉承這些原則。其次,甘地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總是站在正義的一方。甘地完全相信人民的力量。」
在當今心智浮躁、物慾橫流的印度社會,聖雄甘地顯得格格不入。但凱傑裏瓦爾信奉的政治宣言——《印度自治》(Swaraj),曾喚起印度獨立運動領袖把國家建設成爲「自給自足鄉村共和國」的浪漫圖景。
凱傑裏瓦爾認爲政權與財權應大大下放至地方。「若以中央集權治理印度,那麼就一直會有國家分裂的危險,」他邊喝甘菊茶、邊說道。他又說:如果權力下放至各級地方,「或許老百姓會在一、二次會議上無理取鬧,但當他們知道必須依靠自己治理所轄區域後,就會表現得循規蹈矩,就會成爲有擔當的公民。」
批評家開始公開抨擊凱傑裏瓦爾,指責他是反商的民粹分子,有讓印度開歷史倒車的危險。他對此則嗤之以鼻,說這些指控純屬政治對手的「宣傳伎倆」。「只有民營企業纔是創造國家財富及就業的主力軍。印度人是天生的企業家。然而,政府一直充當個體創業的絆腳石。在印度,創辦及經營企業步履維艱,除非用錢擺平。所有法律與政策都需要簡化,另一方面,政府的職責應該是確保法律得到貫徹落實。」
他快等同於在讀印度企業組織的政策簡報了。但在一重大觀點上,凱傑裏瓦爾與公司意見相左:他堅持認爲,在大型基礎設施以及工業項目建設而流離失所的村民應該對整個開發項目有重大話語權——如是重新安置村民,其應該生活得更好。「如今的異地安置完全毫無人性。」他說。
凱傑裏瓦爾喝完杯中的茶,說自己還得趕火車。自己的政治對手乘坐直升機與私人飛機四處進行選戰,而自己只能搭乘火車進行競選活動,火車是自己偶像甘地最喜歡的交通方式。我覺得此時該提最後一個尷尬問題了:如果正如民意預測的那樣,人民黨的莫迪贏得大選(注:此文英文原文發表於5月2日,莫迪於5月16日贏得大選),平民黨只獲得寥寥几席,成立不久的平民黨能生存下去嗎?
「莫迪不會上臺執政。」他語氣堅定地說道。我重複了一遍問題。剛開始,他斥此問題純屬「假設」,最後他這樣回答道,「我們會當好反對派。」我問他將來是否仍會一如既往投身於選舉政治。「當然囉。」我問他爲自己設想的角色是啥?「我從不爲自己考慮。不管充當什麼角色,我都順其自然,坦然接受。」
凱傑裏瓦爾突然站起身來。房主再次出現在我們面前,彼此之間互相握手、互致謝意。我稍差幾步緊跟出去,只見凱傑裏瓦爾已坐在主人車上,周圍是從附近人家「現形」的安保人員,他們顯得頗爲激動。我目視著車緩緩離開時,心想凱傑裏瓦爾是否能註定改變印度的未來,抑或他只是曇花一現的耀眼流星。
艾米•卡茲明是《金融時報》南亞站記者
-------------------------------------------
平民黨支持者的住所:位於德里地區桑德納加爾高檔住宅區
咖哩茄子與土豆
煮青豆
辣味西紅柿吵菜花
洋蔥餅配鷹嘴豆糊
巴斯馬蒂(basmati)大米飯
烤肉
原味Dahi酸奶
1份檸檬水
1份椰子汁
阿方索芒果塊
新鮮甘菊茶
譯者/常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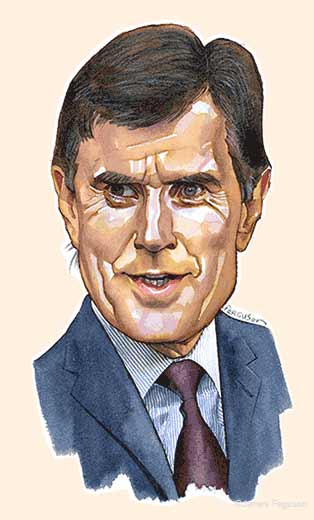
我與約翰•索厄斯爵士(Sir John Sawers)約定的會面地點位於倫敦市中心皮姆利科(Pimlico)一家名叫Gustoso的普通義大利餐館,是以我的名字預訂的:確保安全,做到人不知鬼不覺。我慢慢品著Virgin Mary雞尾酒,等待與英國祕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軍情6處局長約翰•索厄斯爵士的首次公開會面。
Gustoso餐廳裏的客人寥寥無幾,此舉著實讓人生疑,餐廳播放的糟糕義大利音樂總讓人分神。約翰•索厄斯爵士幾乎是悄無聲息地坐到我右邊的椅子上。59歲的英國情報首腦身材高挑,愛好運動的他滿頭黑髮,臉上稍有些斑點,渾身上下是伊令工作室(Ealing studio)(英國老牌影視製片機構)的行頭。與其說他像消極厭世的阿歷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倒不如說他更像追求浮華的皮爾斯•布魯斯南(Pierce Brosnan)。與他簡單交流了夏日度假情況後(他的休假因伊斯蘭聖戰組織斬首兩名美國人質而提前結束),我明知故問:爲何公然接受我的訪談?我認爲英國祕密情報局應該是神出鬼沒。
「軍情6處是保密單位,」約翰•索厄斯爵士回答道。「但公衆多瞭解一下情報工作爲何不可或缺非常重要……公衆過去常常這麼認爲:諜報機構爲大衆服務,但斯諾登(Edward Snowden,美國國安局承包商僱員,叛逃後的他如今藏身於俄羅斯)這類事件讓某些人對此開始質疑。我仍覺得公衆壓倒性支援我們的工作,但批評的聲音也甚囂塵上,質疑『情報局真的不可缺少嗎?』」
我們緊接著談論斯諾登事件,透過揭露西方社會大規模的監聽範圍,他把整個諜報界攪了個底朝天,但此時此刻,我倆仍未完全切入正題。我暗示索厄斯爵士是否喜歡這種遊走懸崖的危險生活。(1996年,他在美國西維吉尼亞的滑雪事故中嚴重受傷,傷口距頸動脈僅不到一寸。)
索厄斯咯咯地笑了:「如果本人沒有做好應對危險的準備工作,不管是個人還是單位,我就不會接受任務。軍情6處是天天與危險打交道的單位。」
他繼續說道,間諜是「凡人,是爲國家鞠躬盡瘁的公務員。」事實上,索厄斯爵士完全一副凡人的行頭。他身穿深色西服,藍色與白色條紋襯衫,紫紅色及藍色相間的領帶(後來他悄悄說這是印度情報局送給他的禮物)。他的措辭充滿自信,但聽不出持何種階級立場。他的父親在勞斯萊斯廠工作,索厄斯爵士中學就讀於巴斯(Bath)的文法學校,後來進入諾丁漢大學(Nottingham University)攻讀物理學與哲學。2009年出任軍情6處局長前,他的多數前任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
. . .
索厄斯爵士說自己在諾丁漢大學時,就得到了幸運女神的垂青————獲得英國外交部的一份工作。「我覺得原因就是我剛好知道軍情6處的聯繫方式,因爲我曾當過一年的學生會祕書……」
這事正常嗎?
「學生會與大學領導有交往,因此認識他們。當然,自己從來沒想到對方會與軍情6處有往來……當時很出乎我的意料。」
他的首份間諜工作是1980年到葉門首都薩那(Sana』a, Yemen』)赴任,這也是他的最後一份間諜工作。呆在骯髒破舊的客房苦等接頭對象,這不是一位20多歲心急火燎的小夥子喜歡做的事。「我發現自己真正喜歡的不是間諜行動,而是觀念、政治以及政策,而且這些事同樣不乏風險,我最後就職於外交部。」
他離開軍情6處後,進入外交部,一路平步青雲,先後到大馬士革、南非、華盛頓、曼谷以及紐約等地工作,最後擔任英國駐聯合國大使(2007-2009年)。在倫敦擔任幕僚工作時,尤其是1999年-2001年期間,他擔任了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的外交政策私人顧問,這讓他引起了頂頭上司們的關注。2009年,他再次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這一次的伯樂是當時年輕有爲的外長大衛•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米利班德推薦他出任「C」——軍情6處的內部人喜歡這樣稱呼其局長。坊間一直流傳:包括一位前任局長在內的傳統派對圈外人出任這一要職頗有微詞。
服務員一直在我們周圍徘徊:索厄斯爵士要了一杯Virgin Mary雞尾酒,然後挑選了乾酪茄子(aubergine with Parmesan),而後又點了菠菜海鯛;我則點了放油煎麪包塊的土豆湯,並點了劍魚。我倆都沒要葡萄酒,而是徑直要了一杯自來水。
我問他如何看待情報界對他的攻擊?「我本以爲前情報官員持保留意見……有些人這樣回應:『我們不希望外交部接管軍情6處。』當然,外交部門的回應是:『見鬼,如今將是軍情6處接手外交部……』我認爲出現問題的部分原因是軍情6處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能量驚人。」
此時的索厄斯爵士說話外交味十足。他接手伊始,叛徒金•菲爾比(Kim Philby)於冷戰高峯時期叛逃蘇聯,引發嚴重危機,當時軍情6處還尚未恢復元氣。前局長理查德•迪爾洛夫(Richard Dearlove)領導下的軍情6處曾被指控:爲了支援2003年美國發動的侵伊戰爭,提供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虛假情報。國際社會還批評軍情6處與包括中央情報局在內的美國審訊人員沆瀣一氣:嚴刑逼供恐怖分子嫌疑犯,而軍情6處對該指控據理力爭。
「軍情6處以前一直處於不利地位,因爲外界對它知之甚少,它對圈外人有些防範,」索厄斯如今這樣說。過去五年,他建立了更爲開放的情報局:舉措之一就是命令在軍情6處總部大樓裏設立開放式辦公區,軍情6處總部大樓位於沃克斯豪爾(Vauxhall)的泰晤士河畔,是一幢後現代主義風格、樂高樂園(Legoland)的綠色建築。他還繼續前任約翰•斯卡利特爵士(Sir John Scarlett)的政策————吸納非執行董事進入情報局。另外,最高法院兩位前任法官負責監督軍情6處、軍情5處(負責國內情報)以及英國絕密監聽機構政府通訊總局(GCHQ)。這些情報專員定期就偵聽、情報以及資料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並可隨意瀏覽所有檔案。
. . .
遵循全管理流程的索厄斯爵士幾乎沒動乾酪茄子,但當服務員打算端走時,索厄斯卻禮貌而堅決地回以「還沒喫完」。服務員端走了我的空湯碗(奶油色的湯乏善可陳)。我倆繼續問責制話題。斯諾登事件是否會在情報工作中引入逐項稽查而不是隨心所欲、搞得神祕兮兮?完全不會,他堅持道。「如果不按規矩做事,事後就會惹上麻煩,這樣做就會減少騰挪的空間。我認爲服從命令聽指揮是最基本的素質。」
他接著說,軍情6處如今能夠與軍情5處以及通訊總局實現「無縫對接」式的合作。軍情6處與軍情5處的特工都可在國內外執行任務,彼此間共享情報,儘管保護國家財產以及保密仍是天條。「兩大情報機構高層需要改變自己的文化定式與思維模式。」
但斯諾登的大曝光讓情報機構的日子雪上加霜。英國的恐怖主義威脅上升,而情報機構的「某些能力」卻下降了,原因是如今恐怖分子也對監測自己行蹤的手段更加了如指掌,他說。去年11月,索厄斯與軍情5處以及通訊總局的負責人同赴國會參加了首次公開聽證會,他說:「很顯然,我們的敵人正信心十足地摩拳擦掌,基地組織則正蠢蠢欲動。」
聽證會過了10個月後,讓他欣慰的是:比起美國民衆,英國公衆仍普遍支援情報機構的工作,美國民衆似乎對私隱受到侵犯更爲憂心忡忡。很顯然,詹姆斯•邦德與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間諜故事讓公衆浮想聯翩,而且英國的情報工作事實上相當出色,但爲何公衆仍有此擔憂呢?
他說:「您已陷入文化問題難以自拔了,但是……」
我趕忙說:您是有文化底蘊的人。他與自己的髮妻(結婚30多年)謝莉都是十足的戲劇迷。他們最近推崇的戲劇包括《深夜小狗神祕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狼廳》(Wolf Hall)以及《摩門經》(The Book of Mormon,該片褻瀆神明,但從頭到尾讓觀衆捧腹大笑)。稍遜一籌的作品包括理查德•比恩(Richard Bean)關於電話竊聽的作品《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這部作品有些草率,類似於現實生活中描寫普通人的漫畫。我不太喜歡那些純宣傳性質的作品。」
事實上,索厄斯爵士有點喜歡顯擺。儘管他喜歡情報機構的那種神祕莫測感,但也不乏調侃。去年耶誕節,他的親朋好友收到的卡片上有一排聖誕老人的圖片,其中一位是戴著黑眼鏡的「神祕聖誕老人」。卡片用綠墨水簽名,這是沿襲歷任局長的「C」字標誌性簽名,它最早可追溯至1909年成立祕密情報局的創辦人喬治•曼斯菲爾德•史密斯-卡明爵士(Captain Sir George Mansfield Smith-Cumming)。
服務員端來了我倆點的魚。在湯羹與肉菜之間,喫點魚恰到好處。索厄斯爵士的海鯛看上去很白嫩新鮮,讓人垂涎欲滴。我問索厄斯爵士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情報總管約翰•瑟洛(John Thurloe)的畫像是否就掛在他的辦公室裏。
「是有一幅他的畫像,事實上,我的前任斯卡利特爵士以前很推崇這幅畫。他的辦公室……掛滿了各式老藝術品以及各種信函,我則非常推崇現代風格的東西。我辦公室放的是現代傢俱,牆上掛的是現代藝術品,喜歡化繁爲簡至極致。
我趁機問他:就類似您昔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大使官邸那樣?我有意不提他牆上掛的那幅沃霍爾(Warhol)的女王版畫,那是他從外交部的藏品中借來的珍品。
「很不錯嘛!」爵士說,這是在恭維我的情報收集工作能力。
他說自己既是工黨老牌政治家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所謂「腹地」理論(「hinterland」)的突出代表,也是該理論的擁躉。家庭(他有兩子一女)、體育(他喜歡騎自行車,擁有兩輛Cannondale高檔自行車)以及看戲都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容。「生活中必須要有其它愛好,才能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工作。我每週工作65.7小時,過去20年始終如一(有時甚至工作更長時間)……你也可以每週工作90-100小時,但我覺得於公於私都不利。」
. . .
我倆轉而談論政治話題。祕密情報局的首腦有特定的人脈及自信心讓自己置身於政府重量級人物之列,這與美國的情況大同小異。他依靠成立不久的國安會發聲,併爲自己的預警能力深感自豪。2003年,就在美國領導的聯軍發動入侵伊拉克的戰爭後,索厄斯被借調至巴格達工作,他給倫敦發了封電報(內容後來遭洩),警告伊拉克正在快速陷入混亂。2003年底,在某私宴場合,他就英國政府同意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發出警告。2010年,他公然反對阿富汗中央政府發動所謂的反恐戰爭。他表示:即便美英繼續軍事清剿塔利班勢力,最終結果依然會南轅北轍。過了四年時間,他仍持同樣看法。「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葉門以及索馬利亞等國家(地區)迅速崛起,而國際社會對他們的重視程度遠不及阿富汗的塔利班恐怖分子。」
他說,他希望未來能在不放棄軍事打擊的前提下,軍情6處能更靈活應對地區恐怖威脅。過去10年的教訓(在阿富汗與伊拉克耗費了幾十億美元的軍事費用)就是:政府只需短短几個月就能推翻掉,但重建國家需花費長年累月的時間。然後歷史又一次次重演,「如果沒有重建打算(部分原因就是重建伊拉克遭受的創傷,如今的利比亞就是如此),那麼推翻該國政府後,到頭來一切就會亂套。如果不想進行軍事幹預,那麼最終的結果就是如今的敘利亞。真的是左右兩難、進退維谷。」
餐廳播放的音樂突然之間音量變大了。索厄斯叫來服務員,禮貌地要求能否降低音樂音量。餐廳方倒騰了大半天,仍沒多大改觀。難道真有人暗中想要攪黃我倆的談話?
索厄斯爵士曾在2001-2003年間擔任駐埃及大使,他說阿拉伯之春表明革命性變革難以掌控,最終往往會進一步損害西方的利益與價值觀。「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是如此,過去幾年中埃及發生的革命同樣如此。」
我倆都沒要甜點,最後我要了杯熱牛奶咖啡,而爵士要了杯薄荷茶。我問他職業生涯的最亮點是什麼。他認爲「傑作」當屬獲得中國與俄羅斯的支援,同意伊朗核計劃的聯合國制裁方案。他認爲制裁是伊朗改變政策的「功臣」。如今,國際社會有可能與伊朗政府達成「某種和解」,尤其因爲伊朗看到了鄰國伊拉克與敘利亞如今的亂局。
他指出中國人是傑出的外交官,他們清楚自己的長處與劣勢以及自己國家的實際需求。「中國外交部吸納的是才華橫溢的精英,再師之以絕頂技藝,他們是談判高手,知道何時達成協議……俄國外交官素質出衆,但缺點是對莫斯科惟命是從,有時還不得不爲自己形象欠佳的國家編造謊言。」
我問他是否也曾爲英國撒過謊。「並非有意爲之,」索厄斯爵士回答說,「本人從未撒過明目張膽的謊,但曾不得不爲之掩飾。」
今年底,索厄斯將辭去祕密情報局局長一職,「眼下」是他的最後一份公職。民營機構已向他伸出了橄欖枝。最後我倆結了帳————剛過60英鎊。我對他說,喫得完全物有所值。索厄斯爵士不禁笑了,並提出順路捎我至位於泰特博物館(Tate)的下一場採訪。
我倆步出餐廳,室外陽光明媚,一位彪形大漢引我上爵士的公務用車,沒想到這是一款外國車。車快速迂迴穿行於倫敦的大街小巷。沒過幾分鐘,車就抵達了博物館大門外。我下了車,掏出手機,並回頭探看,索厄斯早已不見蹤影。
萊昂內爾•巴貝爾是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
Gustoso餐廳位於倫敦威洛街(Willow place )35號,郵編區:SW1P 1JH
麪包:2.5英鎊
混合橄欖:2.7英鎊
幹嘛酪茄子:6.8英鎊
蒜蓉菠菜與小西紅柿燒海鯛:13英鎊
土豆湯與烤劍魚(套餐中選取):16英鎊
薄荷茶:3英鎊
牛奶熱咖啡:3英鎊
2份Virgin Mary雞尾酒:7英鎊
慈善捐款:1英鎊
總計(計小費):61.75英鎊。
譯者/常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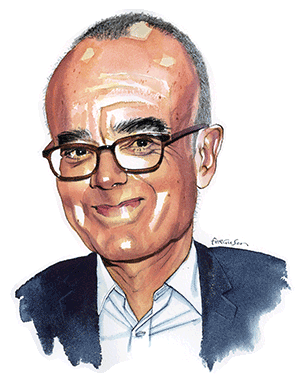
我及時趕到Brasserie Zédel酒館,約好與斯蒂芬•沃爾爵士(Sir Stephen Wall)在下午一點共進午餐,卻發現他早已坐在長條軟座上等候,餐館裏的餐桌擺放得滿滿當當。這位退休外交官握著我的手說:「感謝上帝,你今天沒系領帶。我也解了它,系它只是應酬您的午餐會。」說完,就趕忙解下自己的鮮紅色領帶,然後在我對面坐了下來。他今天內穿白襯衣,外穿藍色夾克。「系領帶感覺特不爽,是吧?」他說,然後我倆就聊起儘管難受之極、但男士仍堅持系它的原因。「我上班那陣子,要求穿制服,」他對我說。「所以我只得如此。」
脫掉壓抑的制服,可以說是斯蒂芬爵士一生的一個主題。縱觀他的職業生涯,多數時間是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外交官——外交生涯的頂峯是上世紀90年代擔任英國駐歐盟大使、而後又擔任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的歐洲事務首席顧問。2004年卸任公職後,成爲時任西敏寺大主教科爾馬克•墨菲-奧康納(Cormac Murphy-O'Connor)的高級政策顧問。但是,剛過花甲之年不久,他就決心不再篤信上帝。差不多同時,他告知自己妻兒自己是同性戀者。如今的他積極爲同性戀者的權利奔走疾呼。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真正恢復自我的天主教徒」。退休後,他又擯棄自己了的外交中立立場,積極主張英國應繼續留在歐盟內。
總而言之,所有這一切聽起來像是他正經歷嚴重的中年危機。但坐在我對面的這個人,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與我2000年在唐寧街首相府(Downing Street)初次結識的那位沉穩外交官並無二致。當時的他簡要給我介紹了歐盟尼斯(Nice)峯會前英國秉持的談判立場。如今的他已68歲,卻一點不顯老,留著平頭短白髮,依然戴著那副學者派頭的眼鏡,仍是昔日那位無可挑剔的政府官員——才思敏捷、剖析問題既迅速又全面,充滿了冷幽默。然而,除了公職領域之外,斯蒂芬•沃爾爵士遠比表象有內涵。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史蒂芬是優秀的職業外交官……但從深層次看,他情感豐富、觀點全面以及洞察力深邃。」
. . .
英國公務員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他們往往非常儉樸。史蒂芬選中的這家Brasserie Zédel餐館當然不會豪華,儘管它屬於歐式風格(很合適)。它離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 Circus)很近,開在地下室裏,店面很大,人頭攢動,採用19世紀末的裝飾風格(大理石柱子、大面鏡子以及大量使用鍍金料),裏面的餐桌擺得滿滿當當。所有的指示牌都用法語標示(如廁所門就標著「toilette」字樣),此舉稍顯做作,但聽到我們鄰桌的一對夫婦正用法語交談,這就增添了一絲真實感。
史蒂芬選了非常便宜的客飯(只有8.95英鎊),並一再向我保證這並非客氣——因爲它的模樣讓人垂涎欲滴。我也認可,於是我倆都先點了蘿蔔絲,主菜則點了牛肉餅與炸薯條。如今的倫敦,平時上班在外喫午餐,往往會喝點葡萄酒,當服務員問我們是否需要時,我倆都婉拒,並表示歉意,只是決定改點純淨水。剛點完菜,蘿蔔絲就端上了桌(快得出乎意料),但用純正檸檬汁調出的味道美味可口。
這次午餐會,我預料我們的談話將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國際事務,一是個人私隱。我倆先從國際事務聊起。史蒂芬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在歐盟努力實現英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英國似乎卻在脫離歐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問他是否憂心忡忡,他溫和地回答道的確如此。與諸多富有經驗的觀察人士一樣,他認爲英國現任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提出的要求近乎無理——尤其是要求歐盟就公民自由流動修改相關法律。
此類問題早有先例。上世紀90年代,史蒂芬效力的首相是約翰•梅傑(John Major),梅傑不斷受到自己所在保守黨的攻擊,指責其對歐洲不夠強硬——尤其指責他1992年簽訂了旨在實現歐盟貨幣一體化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史蒂芬爵士認爲卡梅倫目前陷入了尷尬境地。「他們那一代年輕人在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遇刺後,成爲其忠實門徒,並把全力反對馬約視作忠心不已的標誌——對撒切爾夫人死心塌地。但我認爲與歷任首相一樣,卡梅倫也清楚英國一旦脫離歐盟,就不再是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
當然,英國的歐洲懷疑情結由來已久。史蒂芬擔任英國駐歐盟大使時,曾一度接到指示,要求他否決每項歐盟決議——旨在報復1996年歐盟在英國爆發瘋牛病後禁止其牛肉出口的決定。史蒂芬儘管認爲該命令站不住腳,但仍忠實照辦。他深思後說道,這種務實做法導致「政客相當程度地蔑視公務員……因爲英國本質上是唯利是圖的國家。」
我問他作爲鐵桿挺歐派,是否對英國政府的恐歐論心灰意冷,是否曾考慮過辭職。這樣的事,他只能想到曾經發生過一回:就是在英國爆發瘋牛病期間,政府似乎考慮拒交應承擔的歐盟預算份額——這種做法肯定是不合法規。史蒂芬電告其上司,如果當局要求他公然違反歐盟法律,他只能選擇辭職。幾周後,英國政府告訴他已有了更妥善的解決辦法,儘管他一如既往謙稱自己很清楚政府的最終決定與自己的抗爭毫不相干。
我問他有過啥遺憾?與諸多感同身受的政客及官員一樣,史蒂芬爵士的思緒也轉向2003年美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我一直後悔自己沒有面諫布萊爾發動伊戰是個錯誤。我曾對別的官員說過,但我沒有就此事面諫他。並非我能未卜先知……而是我總認爲戰爭應是最後的不得已選擇……退一步說,發動伊戰的法律依據根本站不住腳。」
關於國際政治,我倆聊得既愜意、話題轉換又快——因爲我倆不時從歐盟轉向以色列、南非以及俄羅斯。「普丁無疑是在不斷突破界限,」他認真說道。「大家都覺得他不會傻到在波羅的海國家犯渾,但他或許真可能這麼做。」我倆都把牛肉餅喫到一半時,我適時問他私生活方面的巨大轉變。
. . .
在最近一期的澳洲同性戀雜誌《DNA》上,史蒂芬爵士談及自己的第一次同性戀經歷,當時他只有10歲,就讀於Douai天主教寄宿學校。事情敗露後成爲千夫所指(「本人成爲學校的棄兒」),自己也自覺羞愧難當,於是幾十年來一直深藏自己的性取向。直至他將近四十歲時(當時他已娶妻生子),才完全確認自己是同性戀者。20多年後,直到妻子凱瑟琳(Catharine)發現他偷藏有同性戀雜誌,他才最終向家人承認出櫃。
我問他:如果妻子沒有發現那些雜誌,這輩子是否會一直嚴守這個祕密?史蒂芬爵士搖搖頭,並說自己內心的煎熬與日俱增,不可能永遠祕而不宣。「我越發感覺痛苦,並非由於遭受性挫折感,而是感覺這是自己人生極其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我對此也無法再掩耳盜鈴……凱瑟琳事後對我說,『我一直覺得有些不對勁,因爲感覺你越來越悶悶不樂,但我搞不清楚你內心的糾結是什麼。』」我問:難道你妻子真一點都沒覺察出你是個同性戀者?他搖搖頭說:「沒有,我覺得她沒覺察。」
他說自己與妻子「都希望繼續維繫這段婚姻,但難度實在太大,因爲我想公開自己的性取向,很顯然,這是很痛苦的抉擇。」他倆目前正在辦理離婚手續。儘管如此,他仍堅稱自己公開這個祕密後感覺如釋重負(「平生第一次陶醉於自己的肉體,」他在《DNA》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最大的慰藉來自35歲兒子馬修的反應。「他完全支援我的決定……有趣的是,儘管他一想起我和他媽媽離婚很是難受,但我出櫃後,他顯得很泰然。」
過去的年輕人對此往往會耿耿於懷。英國法律早在1967年就實現了同性戀關係合法化,當時史蒂芬爵士已經20歲,「但如果公開出櫃,自己就不可能進外交部(Foreign Office)工作,」他這樣解釋道。「當初接受當面審查時,我曾被問及此問題:『有無同性戀經歷?』我回答道,『我10歲時發生過』,我是實話實說,但考官們微微一笑,說那不算什麼……最後在我臨近退休之際,我又被要求坦承自己的性取向後,對方只是說,『哦,同性戀不算啥問題。』」他皺著眉說道。「但也從沒人告訴過我:這真不是個問題的原因是本人並非同性戀、還是他們壓根就不在乎?」
但政府對同性戀的立場還未徹底轉過來。史蒂芬爵士認爲上世紀90年代中葉,自己要是公開出櫃,政府就不可能提名他出任英國駐歐盟大使,因爲當時政府對待同性戀者的態度改變不大。我問他如今是否已今非昔比。他點頭說:「我敢肯定情況已大不一樣。」他願意談論自己的同性戀經歷的一個原因是希望助推政府態度的轉變。他最後的工作(從2010年直至去年)是擔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校董會主席,讓他驚詫與感動的是:他公開出櫃後,很多同性戀學生對他感激涕零。
. . .
我曾以爲史蒂芬爵士放棄宗教信仰與其出櫃密不可分,但他一再向我強調事實並非如此。他說,自己放棄宗教信仰一事發生在前,「與出櫃毫不相干,但主因是自己不再篤信上帝。若真篤信上帝,則當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不容易,因爲得遵守太多清規戒律;但反之則更難。」我不知這是否屬玩笑之舉。
我問他爲何不再篤信上帝?
「我坦承,誘因是拜讀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大作《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並非他道出了我自己未曾想到的原由,而是因爲他說出了我自己不願思考的內容,千真萬確。我當時就想,『實際上就是這樣,說句真心話,自己已不信上帝。』」
但隨著我倆談話不斷深入,很顯然他對天主教的保留看法早已有之:「我五歲時就第一次坦承自己不信上帝……天主教如果希望教化信衆,就應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體系,但事實上它沒做到。這套體系並非建立於理性、成人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負罪感與寬恕的基礎上。這就好比崇尚強硬手段與懷柔警察之間的區別。」
我倆的談話因服務員的到來而暫時中斷。我問他要咖啡還是甜點?史蒂芬爵士堅持喫套餐包含的甜點,於是我給他點了鮮果撻。我自己則決定放縱一把(愧疚之至,敬請寬恕),於是在自選菜單中點了奶油布丁。
我倆每人要了一壺咖啡後,史蒂芬爵士又回到剛纔的話題。他回憶說自己兒子六歲時,「每週六送他上天主教的教義問答課,有一天他回來後,看見他筆記本里寫了這樣一段話(很顯然是老師的授意),『親愛的老爸,原諒我,因爲我罪孽深重。』讀到這,我就對凱瑟琳說(因爲她是不可知論者),『說句心裏話,我寧願兒子不信教,也不希望他再遭這份罪。』」但史蒂芬又補充道:但事後馬修告訴他想去參加King』s Canterbury(一家英國聖公會寄宿學校)的彌撒後,他又轉憂爲喜——因爲沒想到馬修這樣對他說:「老爸,我去過教會各種活動,而彌撒耗時最短。」
我納悶史蒂芬的天主教義是否參摻雜了他對待歐盟的態度,同時我又想驗證自己的觀點:即英國天主教徒通常更易於接受歐洲統一的理念,原因是他們的信仰生來更具國際視野。但史蒂芬爵士指出,英國國內包括保守黨議員比爾•凱希爵士(Sir Bill Cash)與伊恩•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在內的疑歐派重量級人物都是天主教徒,算是委婉地駁斥了我的上述觀點。但是,他的確認爲英國的疑歐論思想或許可以一直追溯至16-17世紀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時期。「科爾馬克•墨菲-奧康納大主教過去常調侃,『只要不把成立歐盟的條約稱爲《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情況可能會好得多(天主教教廷所在地梵蒂岡便位於羅馬——譯者注)』。我覺得疑歐論者的『徹底否定天主教會』的說法,言下之意是反對歐洲大陸對英國國家利益的侵犯,而宗教改革運動就是政治上的反制行爲……就這個意思。」
史蒂芬爵士因職業原因,對歐洲事務仍存有興趣。他正爲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撰寫英國參與歐盟的官方歷史,作爲去各個學校做報告的常客,他仍在測驗英國國民對待歐盟的態度。他的開場白通常是問濟濟一堂的優秀學生:「如果明天公投決定英國在歐盟的去留問題,那麼諸位會如何做?「多數學生表示將投票贊成英國留在歐盟內。」他認爲學生認同『自己對所謂歐洲有幫助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道義』的說法。」而後又補充說,「我認爲學生們並不憂慮所謂的英國主權削弱問題,而這正是挺歐派與疑歐派爭論的內容。」
我倆聊了差不多快2個小時。我支付少得可憐的餐費時,突然覺得他與平時不時哀嘆「現今年輕人」的那位退休要員大相徑庭。相反,在他關注的諸多大事(歐洲問題、宗教信仰以及同性戀者權利)上,史蒂芬爵士如今覺得,對他來說,年輕人沒有上述的「煩惱」,既是寬慰,也是激勵。
吉迪恩•拉赫曼是《金融時報》外交事務首席專欄作家
譯者/常和

少林寺方丈釋永信(Shi Yongxin)剛把iPod的耳塞放入耳朵,耳膜立刻被震耳欲聾的紐約武當派樂隊(Wu-Tang Clan)的音樂震得咚咚直響,但他神情依然坦然自若。
出於禮貌地聽了一會兒後,釋永信坦言:「我聽不懂。」他的普通話地方口音很重,饒舌組合武當派是上世紀90年代來自紐約斯塔騰區(Staten Island)的新潮樂隊,對上世紀70年代功夫電影推崇備至,自詡就來自「少林貧民窟」。
我們就坐於少林寺餐館內,少林寺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名下的世界遺產,坐落於中國中部河南省嵩山(Mount Song)鬱鬱蔥蔥的山谷中。這家規模不大、有1500年曆史的寺院是佛教禪宗(Zen Buddhism)的祖庭,也是中國功夫的精神家園。幾百年來,寺中的僧人在此研習武術,爲的就是匡扶社會正義,尋求悟道。外面,遊客正漫步於寺院,觀看名滿天下的武僧的定時表演,他們展示力量以及眼花繚亂的功夫。
少林寺這麼一個地方能與全球最知名、最鬧騰的饒舌組合聯繫在一起,確實難以想像。但我設法對釋永信說,即便他並不知道武當派饒舌組合,但上世紀90年代的很多西方成年人一開始知道少林寺源於聽《全球聞名的少林寺》(Shaolin Worldwide)這樣的歌,歌詞大致是這樣的:
絕地武士(Jedi),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什麼少林寺,別他媽地跟我扯淡!
饒舌樂隊靠沽名釣譽那就中招了。
「有關少林寺的不實之詞實在太多,」釋永信說,神態十分淡定,是多年修煉的結果。「這些人並不瞭解少林寺,也不代表真正的少林歷史、少林文化與少林精神的傳承。」
在武當派饒舌樂隊RZA、大佬鬼臉(Ghostface Killah) 、Ol』 Dirty Bastard 及其他成員看來天經地義,但在中國,這正是很多人口誅筆伐釋永信的把柄。46歲的釋永信爭議不斷,自他1999年升任該寺第30位方丈以來,就不斷飽受攻擊,指控他收受貴重禮品,把少林古寺商業化。中國網際網路上公然指責釋永信的那些人認爲,他的種種行爲反映了全社會赤裸裸的唯利主義,在過去幾十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分崩離析,全民追求財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與道德真空。
佛教是中國的主流宗教,全國信衆超過3億人。與其它佛教流派一樣,禪宗強調放棄世俗紛擾,透過修行與踐行佛教教義(包括禁止傷害任何的生靈),最終實現悟道。少林寺是很多武俠小說與電影主角的發生地,已經成爲中國通俗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事實上,它是中國走向世界最知名的金字招牌,對此釋永信方丈「居功至偉」,中國媒體給了他「和尚CEO」的綽號。
少林寺的經營包括出資建立全球功夫巡迴表演團,允許影視、卡通及舞臺劇冠名以及先期投資中藥系列產品。在北美、歐洲以及其它國家,它還派出僧人建立了40多個功夫及修行中心,但釋永信說這些中心以及其它「文化營運」勉強保本。相反,他說寺院每年幾百萬元贏餘中的大部都是來自每年約200萬遊客的門票收入,其中30%歸少林寺,70%上交地方政府。
少林寺在全球註冊了商標,以阻止他人盜用其名來推銷不合教規理念的東西。但它的主要戰場在中國,因爲中國保護智慧財產的意識薄弱,從生產軟飲料、筷子到電器與汽車的各色公司都盜用少林寺商標。甚至白酒與火腿腸的生產廠家也是如此,雖然禪宗嚴禁食肉與飲酒。
大量的侵權事件以及中國司法系統糟糕的智慧財產保護,意味著少林寺追究每位侵權者得不償失,但釋永信說最終一切都會向好的方向轉變,對此他持樂觀態度。「若付諸司法來保護我們的權益,就會花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結果卻不一定事逐人願,」他說。「中國人將來一旦與西方人一樣,有很強的法制觀念,侵權行爲自然就會停止。」讓我覺得驚訝的是,他的說辭與中國主政者如出一轍。
然而,他解釋說,成立於1988年的河南少林寺產業開發總公司(Henan Shaolin Temp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pany)是中國第一個實名註冊商標的宗教團體。「我們會應用法律與商業手段來保護自己的智慧財產與品牌,保護自己的文化傳承,」他說。
自公元5世紀建寺後,少林寺經歷了多次破壞與重建。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其周邊所有的農田都被充公,並重新分配給農民,使得寺裏僧人無法自食其力。十年文革浩劫中,留在寺裏的僧人遭到毒打與迫害,被迫解散。但十年浩劫結束後,有些僧人回到了寺裏,開始重振其傳統,包括恢復練功習武。
1981年,16歲的釋永信進入少林寺,從此以後,他一直立志要重整雄風。爲了保護及進一步傳承少林寺,我感覺他做了很多妥協。但是,釋永信說,梵蒂岡(Vatican)就有自己的銀行,就是一家跨國公司,而少林寺每年的收入甚至都無法入圍全中國100家最有錢的寺院。
「我們銀行存款不多,但庫裏的存糧很多,足夠喫上兩年,所以即便遭災,少林寺可保兩年衣食無憂,」他補充說。正是對中國傳統歷史的深刻理解,才造就了他與衆不同的商業技能。
午餐由寺院的老廚師親自安排,服務僧人端來第一道菜——烤麩、醃蘿蔔與豆腐乾做成的、被譽爲「三珍迎客」(three treasures to welcome guests)的精選素小喫——這時釋永信的手機響了,他從飄逸的深紅色袈裟中掏出嗡嗡作響的三星手機,並禮貌地掛斷了對方的電話。我這時注意到他的手指修剪得很整齊,耳垂也特別大,這樣的體徵在中國的文化裏表示能力出衆、財運亨通。
菜不斷地被端上來,方丈矜持地說自己喫飯一般很簡單。事實上,我被允許參加清晨的誦經課,並與衆僧一起喫了一頓豐盛早餐——大米粥、素菜以及熱饃,給我們端飯的小和尚年齡不超過10歲。釋永信與其他和尚一起坐在木凳子上一聲不吭地喫早餐,不到15分鐘,大家就風捲殘雲地喫完了。
看到他的手機後,我覺得正好可以問問他偏好小飾件與貴重禮品那些事,釋永信經常在公開場合乘坐大衆SUV車(Volkswagen SUV),堂而皇之使用iPad。「大衆車不到100萬元,是地方政府所送,因爲我們給他們帶來了不菲的收入,」他淡定的神情中,略顯不悅。「我們吸引了很多的遊客與學生,所以地方政府獎勵我一輛車,勉勵我要更好地工作。」
他說iPad與其它飾件都是信徒所贈,但都要用到無法再用才更換。「我所做的一切不爲別人,而是爲了整個社會與大衆;也不爲我個人及地方政府,如果社會或信衆有需要,我都會竭力爲之。」
接下來喫的這道菜由捲心菜與豆腐乾丁做成,它有個好聽的名字叫「飄香瓦罐」(floating fragrance in a Buddhist pot),但我注意到釋永信幾乎未動筷子。他提到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分成形象地說明了在中國,宗教團體與宣揚無神論的共產黨之間要處好關係是多麼不容易。中國政府只承認五大正式宗教團體——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以及新教——並要求他們組成受「愛委會」監管的機構,愛委會則由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與統戰部門(Communist party』s United Front department)所管轄。
北京政府並不承認其他世界性宗教,如東正教(Orthodox Christianity)、猶太教(Judaism)、摩門教(Mormonism)以及巴哈伊教(baha'i),也不承認很多天主教與新教的祕密家庭教會。但只要這些非官方活動屬於私下行爲,官方也能容忍,但任何顯示政治苗頭的組織都會遭到政府無情打壓。
釋永信則無需要擔心這些事。1998年以來,他一直是全國人大(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是擺設性議會)代表, 2002年以來,一直擔任官方的中國佛教協會(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副會長。通常說來,他與寺裏其他一些高僧就能決定誰能受戒當和尚,並隨後在省級宗教事務局登記備案。但方丈由宗教事務局直接任命,這些機構幾乎清一色都是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員。
我問他是如何被選中當方丈的,他的回答很簡單:「因爲我聽組織的話。我願意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傳統口號,是各級黨政機構的口頭禪。他解釋說:宗教服務於國家在中國由來已久,在其他許多國家也莫不如此。「縱觀歷史,概莫能外:宗教必須敬重帝王,敬重政府。如若不從,它就很難生存下來,」他說。「我們必須依靠政府來宣傳與發展。政府權力很大,若沒有它的支援,我們很難發展。」
他這時的說話口吻又儼然象一位跨國公司的CEO。
這時小和尚又端上一盤油炸茄子與豆腐做的菜,菜名就叫「悟道開顏」(blossoming smile of enlightenment),我問如何回應那些批評者,對方指責他癡迷於把神聖與世俗揉雜在一起。
「我們的目的旨在弘揚佛法,淨化衆生靈魂與心智,」釋永信說。「事實上,我們迄今爲止的商業運作很保守,因爲我們不想太多介入世俗事,也不想過度開發少林寺。」他提及2009年,正是自己與其他一些僧人的強烈反對,才使得當地政府讓少林寺到國內或國際上市的提議束之高閣。
方丈吩咐菜上慢點,多數菜他嚐了一下就被端走了。整頓午飯,似乎想讓我相信他並非如外界所傳那樣,是個貪圖享受的品行不端之輩。他也多次提到自己與手下的僧人生活簡樸,每天的生活費只有7元錢。
解釋自己承受社會壓力的那一套說辭,卻顯得很有說服力。「我們希望藉助少林寺的影響,能扭轉時下不良社會風氣;這幾年,我們親眼看到全民汙染地球,過度開發利用資源,物慾追求日盛一日,」他說。「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如僧侶一樣生活簡樸,不要象那些一夜暴富者那樣追求名牌與奢侈生活。」
最後端上來的一道菜是佛家版的「佛跳牆」(Buddha jumps over the wall),細細品味著這自相矛盾的菜名,釋永信不禁呵呵笑了起來,這道菜通常是用肉與海貨煨的高湯,味道鮮美得甚至能讓和尚違背清規戒律,翻牆而出。
「瞧瞧,這道菜可以讓你感知中國佛教的包容與慈悲,」他說。「在其它文化或宗教中,如果用了這樣褻瀆神靈的菜名,定會掀起軒然大波。」
起誓不傷害生靈的佛家弟子天天舞刀弄劍,練慣用鐵拳擊碎天靈蓋,同樣顯得很具說服力。對於釋永信來說,暫時的利益交換——包括商業運作——似乎僅僅只是悟道路上的必然分化而已。
譯者:常和
三味餐館(Samadhi restaurant)
地點:中國河南省少林寺
『三珍迎客』:烤麩、醃蘿蔔與豆腐乾丁
素魚翅湯:南瓜與豆麪
春捲:用瓜、蘿蔔與素雞做成
飄香砂鍋:捲心菜與豆腐丁
悟道開顏:油炸茄子,豆腐與素菜
佛跳牆:人蔘、菌類與雪果燉的濃湯
定價:每客約80美元
(相互搶著買單差不多折騰了快1個小時,最後還是由我買單,因爲這歷來是FT的規矩。但違背了中國人的禮儀,但這種所謂的不合規矩最終還算被接受了。)